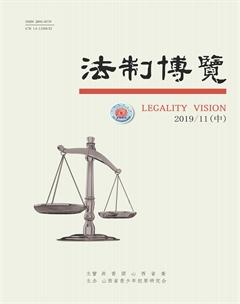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風險與對策
摘 要:認罪認罰從寬是指嫌犯、被告人已明晰認罪可能判處的刑罰,并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從而受到從寬處罰。由于現行法律法規的不完善,特別是在刑事偵查階段,存在虛假認罪認罰的風險。虛假認罪認罰包含三種類型。嫌犯頂替認罪的虛假認罪認罰、偵查機關主導的虛假從寬和偵查機關誘使無罪者的認罪認罰。虛假認罪認罰從寬案件對本國公正高效的司法運作環境、甚至人權保障造成了極大程度的破壞。為了有效解決虛假認罪認罰的問題,應當明確調查取證與認罪認罰的關系,并把偵查的重點放在調查取證上;強化律師的辯護;規范認罪協商的行為;人民檢察院強化審查。
關鍵詞:認罪認罰從寬;偵察階段;虛假從寬;類型;對策
中圖分類號:D925.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9)32-0093-02
作者簡介:王凱麗(1998-),女,漢族,浙江義烏人,嘉興學院,本科。
一、定義/現狀
自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提出之日起,便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和討論。若要探討虛假認罪認罰在刑事偵查階段的風險與對策,首先要明確該制度的內涵。
(一)關鍵詞的定義
“認罪”概念的認定與該制度的適用存在著很大的關系,關系在于前者決定了后者的適用階段。從改革的初衷來看,該制度不僅僅適用于審判程序,也適用審判前的程序中。雖然這兩種內涵可以是一致的,卻會導致在偵查階段不適用從寬制度的局面。因此,從這一角度看,應該從更廣泛的角度界定“認罪”一詞:認罪是嫌犯、被告人供述其主要的犯罪事實。基于此,對“認罰”的界定,要在“認罪”為基石的前提下,有所放寬①。因此,將“認罰”定義為嫌犯、被告人在明晰認罪可能受到判處的刑罰的前提下,接受該刑罰。
(二)適用認罪認罰的案件,大多存在于在刑事偵察階段
在刑事偵查的階段,進行認罪認罰的案件占大多數。根據相關的法律,只有“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的案件才能移送至檢察機關。而在移送至檢察機關的這類案件中,絕大多數的嫌犯都會選擇認罪,即通過嫌犯的口頭供述作為定罪證據。只有少數的案件,偵查機關提供出除了口頭供述之外的、充分的證據,并且證實了犯罪的客觀事實。由于罪與罰具有相關性,在一般情況下,嫌犯“認罪”必然導致“認罰”的發生②。根據推導,我們能得出結論:適用該制度的案件,大多存在于刑事偵查的階段。
二、偵察實踐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存在的風險
我國正在進行該制度的試點改革,但由于現行相關的法律法規尚不完善,虛假認罪認罰從寬案件必然會出現在司法實踐中。以案件主體作為分類標準,虛假認罪認罰可以被分為三種類型。
(一)虛假認罪認罰中,嫌犯自發地虛假供述
根據嫌犯虛假認罪認罰的主觀動機不同,我們可以將自發地虛假供述案件分為兩類:出于獲利替人頂罪、出于情感替人頂罪③。頂罪,是由頂罪人出于某種特殊目的,而承擔不屬于自己的責任。就出于獲利而替人頂罪者來說,如果利益足夠大,大到滿足了頂罪者的需求。定罪者愿意犧牲自己的自由,甚至愿意喪失自己的性命。此類行為顯然不利于社會的公平和穩定,更是在法治制度進行嚴重的破壞。就出于情感而替人頂罪者來說,往往主觀上是出于維護親情、友情和人情的目的。從傳統的道德倫理層面來說,中國人看重親情并無大過。但是,如果要從現代法治社會的層面來說,這是對犯罪的縱容,不利于達到刑法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目的,更是不尊重國家法律的公正、威嚴的體現。
(二)偵察機關主導的虛假從寬
偵察機關主導的虛假從寬,指在證據收集難度大或根據現有證據難以對嫌犯定罪的情況下,偵查機關向嫌犯作出虛假的許諾,從而換取嫌疑人的不真實的口供言論。顯然,偵察機關的此類行為,與自愿認罪的原則相抵觸。無罪之人也許就會因為害怕承擔重罪敗訴的風險,對偵察機關妥協。
(三)偵察機關誘使無罪之人的認罪認罰從寬
偵查機關誘導無罪之人的認罪認罰,是偵察人員利用自己的職權,通過威脅、誘導、甚至強迫等不合法的方式,促成無罪的嫌犯適用該制度。在實踐中,由于偵查人員容易在事實認定清楚之前就“先入為主”的認定嫌疑人有罪,即帶著有色眼鏡看嫌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通過不合法的方式,給嫌犯施加壓力,迫使嫌犯認罪認罰,作出有罪供述。更有甚者,會制造出虛假證據,來證實自己先前有罪推定的主觀判斷。在偵察人員多種手段的審訊下,無罪的嫌疑人往往背負了超常的壓力,從而不得不順著偵察人員的誘導,作出有罪供述,并從寬處理。這顯然違背了刑法中的“罪行責相適應”原則,更不利于達成刑法的目的。
三、如何保障偵察機關正確適用認罪認罰制度
為了保證在偵查階段,正確地適用該制度,必須采取運用事前防范、事中規制、事后救濟等多個方面的對策。
(一)事前防范:把偵查的重點放在調查取證上
認罪認罰要以偵察人員的調查取證為基礎,再進行政策攻心和認罪協商。依據相關的數據顯示,多數嫌疑犯往往不會主動認罪,而是進行反偵查行為。其原因并不難以猜測,人都有趨利避害的天性,也有逃避承擔責任的心態④。嫌犯作為人,自然也不例外,如果嫌犯如實說出自身的犯罪事實,那就有可能要承擔嚴重的刑事責任,最嚴重的會被剝奪自由和生命。出于這樣的天性和心理狀態,嫌犯往往會采取破壞現場、消滅證據等行為來躲避偵察。即使是在被歸案后,這樣的天性和心態也不會就此消失,除了少數人坦白外,往往會拒絕訊問。了解到這些,我們可以得出,出于嫌犯的天性和心理,如果過分的希望嫌犯主動的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顯示并不現實。因此,偵查人員要以充足的事實、證據為基礎,也要清楚地認識到認罪認罰和調查取證之間的相互聯系。把偵察的重點放在調查取證上。在有充足的證據的基礎上,再用該制度的寬大處理政策合理勸說,才能更正確地適用這項制度。
(二)強化律師辯護和法律幫助
在很大程度上,強化律師的辯護和法律幫助能夠促進該制度的正確適用。第一,要認真貫徹落實法律中有關對于辯護權的規定,特別是在刑事偵查的階段。具體來說,相關法律規定了偵察機關和檢查機關對律師權力的保障。即偵查機關要保證律師的會見權、通信權、提供法律幫助權等訴訟權利:對于律師提出的申訴、控告,檢查機關應該做到及時審查。第二,要落實《試點工作辦法》中專門為偵查階段的嫌犯與其律師新增的多項權利。其中一項新增的權利如下:在認罪認罰的案件中,嫌疑犯擁有獲得法律幫助的權利。對于該條文進行解析:如果意向認罪認罰從寬的嫌犯沒有為自己聘請辯護律師,有權提出有關機構為自己法律援助。該項新增權力的規定,直接地保障了嫌犯明晰法律后果,有利于嫌犯在此基礎上,自發地作出選擇。既維護了嫌犯的權力,又保障了該制度的有效實施。
(三)規范認罪協商行為
應規范認罪協商,做到應依法訊問。偵查機關不能通過威脅、誘導、甚至強迫的方式促進嫌犯認罪。認罪協商的過程⑤,通常也就是指偵查機關對嫌犯的詢問過程。在此過程中,也就是偵察機關對嫌犯進行思想上和政策上的教育過程,在這過程中,必須要做到規范認罪協商行為,堅持依法訊問。規范認罪協商的方式體現在嚴格執行《試點工作辦法》中的相關規定。即“偵查機關因該告知嫌犯其享有的法律上的權利,并且使嫌犯明白其行為所帶來的的法律后果。同時,也要聽取嫌犯的辯解和意見”。其次,規范的其他方式也體現在《刑事訴訟法》的第50條規定中。即“嚴禁采取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強迫、誘導、騙取嫌犯認罪認罰。”
(四)人民檢察院對于偵查階段認罪認罰的案件,應強化審查
為了保障該制度的正確適用,人民檢察院要履行權利告知義務,讓嫌犯清楚的認識到其法律上的權利⑥。其次,人民檢察院也要通過多方途徑,了解偵查機關在訊問的過程中,是否存在不正當方式獲取證據的行為。當發現偵查人員存在通過威脅、誘導等方式促進嫌犯認罪認罰的,要及時依法監督糾正。除此之外,還要明晰在認罪認罰之前,律師是否為嫌犯提供法律幫助。最后,公安部提起的,請求批準擬撤銷的相關案子,最高人民檢察院應當認真、從嚴審查。
[ 注 釋 ]
①王瑞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銜接問題探究——以偵查階段的認罪認罰從寬為視角[J].四川警察學院學報,2016(10):3-5.
②朱孝清.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幾個問題[J].法治研究,2016(5):35-44.
③陳歡,CHENHuan.自愿型虛假供述成因的多角度解讀[J].北京警察學院學報,2015(1):38-44.
④王恒認.反偵查行為表現及防范對策[J].安徽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13,12(2):69-71.
⑤李黎.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究[D].2017.
⑥李學軍.論偵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D].湘潭大學,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