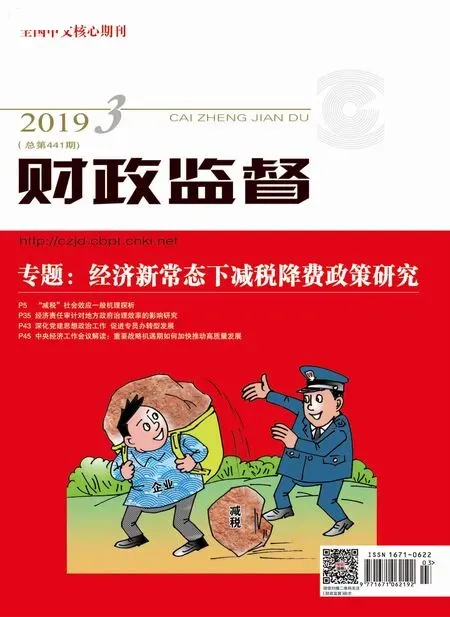“減稅”社會(huì)效應(yīng)一般機(jī)理探析
●姚軒鴿
要通過出臺(tái)一項(xiàng)有效的減稅政策,發(fā)揮其對(duì)某一國(guó)家或地區(qū)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積極效應(yīng),無疑既要弄清一項(xiàng)減稅政策的一般經(jīng)濟(jì)社會(huì)效應(yīng)機(jī)理,也要弄清在特定政治經(jīng)濟(jì)等歷史大背景下一項(xiàng)減稅政策的正負(fù)效應(yīng)。道理在于,“稅收是藝術(shù)、技術(shù),也是科學(xué),我們永遠(yuǎn)要限于特定的時(shí)空條件才能對(duì)其進(jìn)行評(píng)判。”邏輯上,必須注重“減稅”社會(huì)效應(yīng)一般機(jī)理研究,這是經(jīng)濟(jì)新常態(tài)下減稅政策制定和出臺(tái)的前提。
一、“減稅”“社會(huì)”的內(nèi)涵與本質(zhì)
要探討“減稅”社會(huì)效應(yīng)的一般機(jī)理,邏輯上,必須首先弄清“減稅”與“社會(huì)”的內(nèi)涵與本質(zhì)。
(一)“減稅”的內(nèi)涵與本質(zhì)
所謂“減稅”,就是稅收減征,意指“按照稅收法律、法規(guī)減除納稅義務(wù)人一部分應(yīng)納稅款。”對(duì)征稅者而言,一般情況下,“減稅”意味著國(guó)家財(cái)政收入的減少,即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減少,也就是政府為國(guó)民提供公共產(chǎn)品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資金總量的減少;對(duì)納稅者而言,“減稅”則意味著納稅者法定納稅義務(wù)的減少,自己可支配資金的增多。同時(shí)就稅收的本質(zhì)——國(guó)民與國(guó)家之間就公共產(chǎn)品交換價(jià)款締結(jié)、履行契約的活動(dòng)而言,也意味著納稅者或國(guó)民可享受公共產(chǎn)品與服務(wù)質(zhì)量與數(shù)量(性價(jià)比)的相應(yīng)降低。
就“減稅”的本質(zhì)是政府“減權(quán)”而言,一切“減稅”意味著政府財(cái)政可支配力量及其權(quán)威的減少。因此,根據(jù)權(quán)利與義務(wù)分配交換的公正原則可知,“減稅”意味著政府提供公共產(chǎn)品與服務(wù)之責(zé)任的降低,或者說,國(guó)民享有公共產(chǎn)品與服務(wù)之權(quán)利的減少。直言之,“減稅”意味著征納稅者之間權(quán)利與義務(wù)關(guān)系的重新調(diào)整。就是說,真正的“減稅”意味著征納稅者之間、納稅者之間、征稅者之間、國(guó)家之間、人與非人類存在物之間,以及代際之間等等涉稅主體之間權(quán)利與義務(wù)關(guān)系的重新調(diào)整,即稅收基本權(quán)利與義務(wù)、非基本權(quán)利與義務(wù)的重新調(diào)整。邏輯上,不同性質(zhì)和類型的“減稅”,其對(duì)稅收基本權(quán)利與義務(wù),以及稅收非基本權(quán)利與義務(wù)的影響效果是不一樣的,存在公正平等與否的問題。比如稅權(quán)的性質(zhì)不一(威權(quán)的或民主的),在同樣減稅額下的“減稅”,其社會(huì)效應(yīng)是有大小優(yōu)劣差別的。毋庸置疑,唯有有助于促進(jìn)上述六大基本稅收權(quán)利與義務(wù)關(guān)系之自由、公正、平等交換的“減稅”,才是善的、好的、優(yōu)良的,才是值得遵從和追求的“減稅”,因?yàn)檫@些減稅,將有助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實(shí)現(xiàn)。反之,一切無助于六大基本稅收權(quán)利與義務(wù)關(guān)系之自由、公正、平等交換的“減稅”方案,便都是惡的、壞的、落后的,不值得遵從和追求的“減稅”。因?yàn)檫@些減稅,將無助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實(shí)現(xiàn)。
可見,關(guān)鍵在于一種“減稅方案”,即稅收基本權(quán)利與義務(wù)的重新調(diào)整,是否更加趨于完全平等原則,非基本權(quán)利與義務(wù)的重新調(diào)整是否更加趨于比例平等原則?事實(shí)上,這才是“減稅”社會(huì)效應(yīng)必須關(guān)注的核心問題。由于“權(quán)利是一種具有重大的社會(huì)效用的必須且應(yīng)該的索取或要求;是一種具有重大的社會(huì)效用的必須且應(yīng)該得到的利益;是一種具有重大的社會(huì)效用的必當(dāng)?shù)玫降睦妫灰蚨簿褪菓?yīng)該受到社會(huì)管理者依靠權(quán)力加以保護(hù)的利益、索取或要求;說到底,也就是應(yīng)該受到政治和法律保障的利益、索取或要求。”因此,稅權(quán)越合法,稅收權(quán)利與義務(wù)分配越可能趨于公正平等,基本權(quán)利與義務(wù)的重新調(diào)整越趨于完全平等,非基本權(quán)利與義務(wù)的重新調(diào)整越趨于比例平等。反之,如果稅權(quán)合法性較小,稅收權(quán)利與義務(wù)分配則可能趨于不公正、不平等,基本權(quán)利與義務(wù)的重新調(diào)整越可能背離完全平等原則,非基本權(quán)利與義務(wù)的重新調(diào)整越趨于背離比例平等原則。
(二)“社會(huì)”的內(nèi)涵與本質(zhì)
關(guān)于“社會(huì)”的界定,古往今來,專家學(xué)者的觀點(diǎn)可謂汗牛充棟。馬克思認(rèn)為:“社會(huì)不是由個(gè)人構(gòu)成,而是表示這些個(gè)人彼此發(fā)生的那些聯(lián)系和關(guān)系的總和。”“社會(huì)——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dòng)的產(chǎn)物。”即社會(huì)是“人的真正的共同體”。當(dāng)代學(xué)者歐陽康先生則認(rèn)為:“社會(huì)是指一定空間意義上的歷史,歷史是運(yùn)動(dòng)著的社會(huì)。”
鑒于辨析“社會(huì)”概念不是本文的重點(diǎn),筆者采信王海明先生給“社會(huì)”下的定義,并作為后續(xù)“減稅”社會(huì)效應(yīng)分析的依據(jù)。“所謂社會(huì),動(dòng)態(tài)地看,亦即社會(huì)活動(dòng),無非是財(cái)富活動(dòng)與非財(cái)富活動(dòng)之和。財(cái)富活動(dòng)亦即創(chuàng)造財(cái)富的活動(dòng),又分為兩類:一是創(chuàng)造物質(zhì)財(cái)富的活動(dòng),即經(jīng)濟(jì);二是創(chuàng)造精神財(cái)富的活動(dòng),即文化產(chǎn)業(yè)。非財(cái)富活動(dòng)也分為兩類:一類是與財(cái)富沒有必然的、不可分離關(guān)系的活動(dòng),是完全不創(chuàng)造財(cái)富的活動(dòng),即人際交往活動(dòng);另一類則是與財(cái)富有必然的、不可分離關(guān)系的活動(dòng),是直接不創(chuàng)造財(cái)富而間接創(chuàng)造財(cái)富管理活動(dòng),說到底,也就是直接不創(chuàng)造財(cái)富的管理活動(dòng)。這種管理活動(dòng)又分為權(quán)力管理及其規(guī)范和非權(quán)力管理及其規(guī)范:前者即政治與法;后者即德治與道德。于是,社會(huì)就其動(dòng)態(tài)結(jié)構(gòu)來說,無非由經(jīng)濟(jì)、文化產(chǎn)業(yè)、人際交往、政治、德治、法和道德7類活動(dòng)構(gòu)成。”如果再加上“人類與非人類存在物的活動(dòng)”,社會(huì)便有8類活動(dòng)構(gòu)成。如此,“減稅”的社會(huì)效應(yīng)分析,便可簡(jiǎn)化為對(duì)財(cái)富活動(dòng)與非財(cái)富活動(dòng)之正負(fù)效應(yīng)的分析,或者說對(duì)財(cái)富活動(dòng)、完全不創(chuàng)獲財(cái)富活動(dòng)與直接不創(chuàng)獲財(cái)富活動(dòng)之正負(fù)效應(yīng)的分析,即“減稅”利害“經(jīng)濟(jì)、文化產(chǎn)業(yè)、人際交往、政治、德治、法和道德7類活動(dòng)”及“人類與非人類存在物的活動(dòng)”之正負(fù)效應(yīng)的分析。
二、“減稅”的途徑與方法
“減稅”雖然是指“按照稅收法律、法規(guī)減除納稅義務(wù)人一部分應(yīng)納稅款”,與社會(huì)效應(yīng)緊密相關(guān),但要全面進(jìn)行“減稅”社會(huì)效應(yīng)分析,“減稅”的途徑與方法同樣重要,同樣需要認(rèn)真梳理和明確,而且,其對(duì)“減稅”社會(huì)效應(yīng)的影響也不可忽視。
因?yàn)樵凇皽p稅”的概念下,至少有以下類型可作為選項(xiàng):第一,就減稅目的而言,有“卸責(zé)式”減稅與“不卸責(zé)式”減稅(減稅只是作為一種權(quán)宜的手段)。前者意味著政府少征稅也少擔(dān)責(zé),權(quán)責(zé)基本一致;后者則意味著“堤內(nèi)損失堤外補(bǔ)”,政府公共產(chǎn)品供給責(zé)任不減;第二,就“減稅計(jì)劃”之主導(dǎo)者而言,有征稅者主導(dǎo)之減稅與納稅者主導(dǎo)之減稅,即有多數(shù)或全體公民主導(dǎo)之減稅與少數(shù)公民主導(dǎo)之減稅,或者說有官員主導(dǎo)之減稅與民眾主導(dǎo)之減稅,等等;第三,就“減稅”的公正性而言,有公正減稅與不公正減稅,有助推稅收基本權(quán)利與義務(wù)趨于完全平等之減稅,也有助推稅收非基本權(quán)利與義務(wù)趨于比例平等之減稅,即有普惠式減稅與特定式減稅之別。前者是針對(duì)所有納稅人,是遵從完全平等原則之減稅(比如普遍降低稅率、提高免征額或起征點(diǎn)等);后者則針對(duì)特定納稅人,遵從比例平等原則之減稅(比如稅收優(yōu)惠政策等);第四,就稅種而言,有針對(duì)間接稅的減稅,也有針對(duì)直接稅的減稅,或者針對(duì)不同稅種之減稅;第五,就“減稅”的實(shí)際結(jié)果而言,有總體性總量減稅與總體總量不減稅之別。前者是指納稅人稅負(fù)普遍降低的減稅,后者是指對(duì)不同納稅者的納稅義務(wù)有減輕的減稅,即所謂的“有增有減”的“結(jié)構(gòu)性減稅”,等等;第六,就減稅之內(nèi)容與形式而言,也存在形式減稅與實(shí)質(zhì)減稅之別,即真減稅與假減稅之別;第七,就“減稅”的性質(zhì)而言,則有普遍性與特殊性減稅、絕對(duì)性與相對(duì)性減稅,以及主觀性與客觀性減稅之別。比如法定減稅、特定減稅和臨時(shí)減稅,等等;第八,就減稅的具體實(shí)施方式而言,有一次性減稅與多次漸進(jìn)式減稅,等等。
毋庸置疑,國(guó)情不同,國(guó)家治理面臨的緊迫問題不同,以及制度背景不同,不同國(guó)家將會(huì)選擇不同的減稅方式,其減稅的實(shí)際效果也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別。而唯一不變的是:評(píng)價(jià)一種“減稅計(jì)劃”得失成敗的終極標(biāo)準(zhǔn)是——哪種“減稅計(jì)劃”最有助于增進(jìn)全社會(huì)和每個(gè)國(guó)民的福祉總量,最能滿足人們不斷增長(zhǎng)的美好生活需求,同時(shí)又不傷害其他國(guó)家和國(guó)民的利益。
三、“減稅”社會(huì)效用之一般機(jī)理分析
“減稅”之社會(huì)效用機(jī)理分析,顯然受制于稅制優(yōu)劣之社會(huì)效應(yīng)與功能,即稅收在國(guó)家治理大系統(tǒng)中所處的地位與作用(見圖1)。

圖1 國(guó)家治理大系統(tǒng)圖示
首先,稅收治理作為國(guó)家治理系統(tǒng)和財(cái)政系統(tǒng)的一個(gè)子系統(tǒng),國(guó)家治理系統(tǒng)和財(cái)政系統(tǒng)運(yùn)轉(zhuǎn)之質(zhì)量和效果,總體上決定稅收治理的運(yùn)行效果。但稅收子系統(tǒng)的變化,比如“減稅計(jì)劃”等稅制改革舉措,也會(huì)反作用于國(guó)家治理系統(tǒng)和財(cái)政系統(tǒng),影響國(guó)家治理系統(tǒng)和財(cái)政系統(tǒng)運(yùn)轉(zhuǎn)的總體質(zhì)量。而且,由于稅收治理在國(guó)家治理系統(tǒng)和財(cái)政治理系統(tǒng)中所處的重要地位,稅收治理對(duì)國(guó)家治理系統(tǒng)和財(cái)政治理系統(tǒng)的反作用影響更需特別關(guān)注。就本質(zhì)而言,一個(gè)國(guó)家的最高權(quán)力,包括最高財(cái)權(quán)、稅權(quán)、預(yù)算權(quán)的合法性與民意基礎(chǔ),會(huì)從總體上決定這個(gè)國(guó)家治理、財(cái)政治理與稅收治理水平的高低。眾所周知,所謂稅權(quán)“合法性”是指納稅者或國(guó)民對(duì)稅權(quán)的認(rèn)可與同意。納稅者或國(guó)民對(duì)最高財(cái)權(quán)、稅權(quán)、預(yù)算權(quán)的認(rèn)可與同意越多,這個(gè)國(guó)家的財(cái)權(quán)、稅權(quán)、預(yù)算權(quán)便越合法。關(guān)于這個(gè)道理,莫里斯·迪韋爾熱明確指出:“權(quán)力的合法性只不過是由于本集體的成員或至少是多數(shù)成員承認(rèn)它為權(quán)力。如果在權(quán)力的合法性問題上出現(xiàn)共同同意的情況,那么這種權(quán)力就是合法的。不合法的權(quán)力則不再是一種權(quán)力,而只是一種力量。”在哈貝馬斯看來,“沒有大眾的忠誠(chéng),就沒有合法性。”
深究之,一個(gè)國(guó)家的政體類型:專制、寡頭或民主,會(huì)從總體上決定一個(gè)國(guó)家治理、財(cái)政治理與稅收治理水平的高低。專制政體下的國(guó)家、財(cái)政與稅收治理,其總體水平最低。這不僅是因?yàn)槠渥罡邫?quán)力,包括最高財(cái)權(quán)、稅權(quán)、預(yù)算權(quán)的合法性與民意基礎(chǔ)薄弱,也因?yàn)樵谶@種政體下,國(guó)家最高財(cái)權(quán)、稅權(quán)和預(yù)算權(quán)缺少“閉環(huán)式”監(jiān)督機(jī)制,權(quán)力的匪性與貪婪性容易發(fā)作,會(huì)造成大面積的權(quán)力濫用,背離國(guó)家、財(cái)政與稅收治理的終極目的。同時(shí)也因?yàn)樵谶@種政體下,稅收決策與執(zhí)行容易犯錯(cuò),等等。以此類推,寡頭制的國(guó)家、財(cái)政與稅收治理總體水平次之;民主制下的國(guó)家、財(cái)政與稅收治理總體水平相對(duì)較高,特別是完備民主制下的國(guó)家、財(cái)政與稅收治理總體水平更高。道理在于,民主制可相對(duì)有效地克服專制政體的一些固有弊端,比如大面積出現(xiàn)的腐敗問題,消減權(quán)力的濫用現(xiàn)象,有助于國(guó)家、財(cái)政與稅收治理終極目的的實(shí)現(xiàn)。坦率地說,不同政體背景下的稅制改革方案,包括“減稅計(jì)劃”,其對(duì)內(nèi)對(duì)外的社會(huì)效應(yīng)也不一樣,甚至大相徑庭。
其次,稅收是國(guó)家治理體系運(yùn)行的物質(zhì)基礎(chǔ),它通過為國(guó)家運(yùn)轉(zhuǎn)提供所需要的資金,保障政府職能的運(yùn)轉(zhuǎn)和發(fā)揮。常識(shí)是,國(guó)家如果沒有一定的財(cái)力,便無法生產(chǎn)和提供基本的公共產(chǎn)品與服務(wù),并保證其正常運(yùn)轉(zhuǎn)。這方面美國(guó)稅收政治學(xué)者瑪格麗特·利瓦伊有精辟的論述:“國(guó)家歲入生產(chǎn)的歷史即國(guó)家的演進(jìn)史。”因?yàn)椤敖y(tǒng)治的一個(gè)主要限制條件是歲入,即政府的收入。國(guó)家的歲入越多,統(tǒng)治就可能延伸得越廣。歲入增強(qiáng)了統(tǒng)治者的能力,使他們能夠精心建立國(guó)家機(jī)構(gòu),將更多的民眾納入這些機(jī)構(gòu)的治理范圍之內(nèi),并增加國(guó)家所提供的公共產(chǎn)品的種類和數(shù)量。”因此,稅收歷史學(xué)者查爾斯·亞當(dāng)斯認(rèn)為:“國(guó)家的繁榮與衰落經(jīng)常有稅收因素,這一點(diǎn)我們?cè)谡麄€(gè)歷史中可以經(jīng)常看到。”
最后,稅收通過籌集足量的公共產(chǎn)品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資金,提供高性價(jià)比的公共產(chǎn)品與服務(wù),從而影響一個(gè)社會(huì)的總體治理水平,即增進(jìn)或者消減全社會(huì)和每個(gè)國(guó)民的福祉總量。可見,納稅者如果不繳納一定的稅款,則無法獲得生存與發(fā)展所需要的公共產(chǎn)品與服務(wù),難以最大限度地實(shí)現(xiàn)人生價(jià)值、獲得足量的人生幸福、過上美好生活。公共產(chǎn)品的性價(jià)比高低與全社會(huì)和每個(gè)國(guó)民福祉總量之間的邏輯相關(guān)性不言自明。任何人要生存和發(fā)展,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公共產(chǎn)品與私人產(chǎn)品滿足自己的需求,只有這些不同層次的需求和欲望滿足了,方可談得上快樂與幸福。按照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人的需要從低級(jí)到高級(jí)依次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需要和愛的需要、自尊需要、認(rèn)識(shí)和理解的欲望、審美需要、自我實(shí)現(xiàn)需要。由于只有優(yōu)良稅制或者“減稅計(jì)劃”,才能有助于提供高性價(jià)比的公共產(chǎn)品,從而滿足全社會(huì)每個(gè)國(guó)民各個(gè)層次的需要,特別是滿足每個(gè)國(guó)民的人生重大需要、欲望和目的。因此,唯有優(yōu)良稅制和科學(xué)完備的“減稅計(jì)劃”才是可欲的、有價(jià)值的、值得追求的。
換句話說,稅制或者“減稅計(jì)劃”越優(yōu)良、越先進(jìn)、越完備,則每個(gè)國(guó)民的人生重大需要、欲望和目的越容易得到滿足,其生存與發(fā)展越容易實(shí)現(xiàn)某種完滿。相反,“稅痛”越大,就越不幸。同樣,稅制或者“減稅計(jì)劃”越惡劣、越落后、越不完備,則每個(gè)國(guó)民越容易陷入人生重大的痛苦,“稅痛”也就越大。每個(gè)國(guó)民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的肯定方面就越不容易得到實(shí)現(xiàn),其否定方面也就越難以避免。即每個(gè)國(guó)民的生存和發(fā)展也就越容易達(dá)不到某種完滿,也就越容易遭受嚴(yán)重的損害。簡(jiǎn)言之,稅收治理體系或者“減稅計(jì)劃”越優(yōu)良意味著,國(guó)家治理與財(cái)政治理越優(yōu)良,越有助于實(shí)現(xiàn)滿足人類美好生活需求的終極目的——增進(jìn)全社會(huì)和每個(gè)國(guó)民的福祉總量。正因如此,才有財(cái)稅治理是“國(guó)家治理的基礎(chǔ)和重要支柱”的論斷,才備受世界各個(gè)國(guó)家的關(guān)注與重視。
概而言之,圖1具體啟示我們,“減稅”社會(huì)效應(yīng)一般機(jī)理如下:
第一,從“減稅”等于減少當(dāng)下政府公共產(chǎn)品資金分析,一般而言,“減稅”意味著一個(gè)國(guó)家公共產(chǎn)品供給能力的下降,意味著國(guó)家與國(guó)民之間稅收權(quán)利與義務(wù)關(guān)系的重新調(diào)整,即國(guó)家與國(guó)民之間稅收基本權(quán)利與義務(wù)關(guān)系、非基本權(quán)利與義務(wù)關(guān)系的調(diào)整。“減稅”意味著國(guó)家基本權(quán)利與義務(wù)的降低,因?yàn)檎皽p權(quán)”即應(yīng)減責(zé),或者降低公共產(chǎn)品的性價(jià)比。
當(dāng)然,核心在于國(guó)民愿意不愿意。在完備民主制度下,“減稅”將成為政治博弈的主要領(lǐng)域,最終可通過民主機(jī)制中的相互妥協(xié)與博弈平臺(tái),求得一個(gè)“最大公約數(shù)”。因此,一切看上去很美好的“減稅計(jì)劃”,或因?yàn)槎喾讲┺模罱K達(dá)成一個(gè)“變形”的“減稅計(jì)劃”,從而對(duì)本國(guó)及世界各國(guó)產(chǎn)生一定的正負(fù)效應(yīng)。但在不完備民主制度下,由于國(guó)民與國(guó)家之間博弈地位的不平等,“減稅”或成為政府繼續(xù)降低國(guó)民用稅權(quán)利之契機(jī)與借口。即“減稅”會(huì)以降低公共產(chǎn)品的性價(jià)比為代價(jià),加劇國(guó)民與國(guó)家之間稅收權(quán)利與義務(wù)分配關(guān)系的不公正與不平等,致使稅收基本權(quán)利與義務(wù)分配背離完全平等原則,稅收非基本權(quán)利與義務(wù)分配背離比例平等原則,結(jié)果擴(kuò)大國(guó)民與國(guó)家之間稅收權(quán)利與義務(wù)分配關(guān)系的結(jié)構(gòu)性不公正與不平等。進(jìn)而加劇納稅者之間、征稅者之間、國(guó)家之間、人與非人類存在物之間,以及代際之間權(quán)利與義務(wù)關(guān)系的不公正與不平等,松動(dòng)稅收治理的主體基礎(chǔ),甚至引發(fā)系統(tǒng)性的社會(huì)風(fēng)險(xiǎn),背離“減稅”的終極目的,消減而不是增進(jìn)全社會(huì)和每個(gè)國(guó)民的福祉質(zhì)量。
進(jìn)一步說,“減稅”雖然有助于納稅者可支配財(cái)富的增加,有助于社會(huì)生產(chǎn)總過程中生產(chǎn)、分配、交換、消費(fèi)關(guān)系的重新理順,有助于投資、消費(fèi)、出口“三駕馬車”的啟動(dòng),即對(duì)一切創(chuàng)獲財(cái)富的活動(dòng),都有積極正面的影響。同時(shí)對(duì)與財(cái)富沒有必然、不可分離關(guān)系的活動(dòng),也有積極正面的影響,有助于人際關(guān)系的自由安全與健康和諧。但對(duì)于那些直接不創(chuàng)造財(cái)富的管理活動(dòng),即對(duì)政治與法、德治與道德活動(dòng)之影響,其結(jié)果則可能比較復(fù)雜,完全取決于“減稅計(jì)劃”本身性質(zhì)之優(yōu)劣,及其具體實(shí)現(xiàn)途徑與方法之科學(xué)性。
第二,就“減稅”意味著政府“減權(quán)”而言,“減稅”對(duì)不同政體社會(huì)的影響也是不同的。對(duì)完備民主政體社會(huì)而言,由于“減稅”的民意基礎(chǔ)相對(duì)堅(jiān)實(shí),因此而聯(lián)動(dòng)的政府“降責(zé)”舉措,國(guó)民認(rèn)同與理解度會(huì)相對(duì)較高,引發(fā)系統(tǒng)性社會(huì)風(fēng)險(xiǎn)的概率較小。而且,看似“減稅”的“減權(quán)”,也會(huì)因?yàn)榧{稅者可自主財(cái)富的增加,促進(jìn)經(jīng)濟(jì)、文化產(chǎn)業(yè)的繁榮與發(fā)達(dá),收到實(shí)際“增稅”“擴(kuò)權(quán)”的隱形效果,有助于政府更加有效地提供高性價(jià)比的公共產(chǎn)品。事實(shí)上,只有在完備民主制度下的社會(huì)里,公民才會(huì)因“減稅”而調(diào)低的“用稅”期望,更容易獲得較多的滿意和認(rèn)可,消減普遍的焦慮與不安,促進(jìn)全社會(huì)各種關(guān)系的和諧與安全,降低系統(tǒng)性社會(huì)風(fēng)險(xiǎn)爆發(fā)的概率。
但對(duì)于不完備民主社會(huì),卻可能因?yàn)椤皽p稅”的民意基礎(chǔ)相對(duì)薄弱,缺乏制度性的緩沖與調(diào)適機(jī)制,加劇因“減稅”而引發(fā)的民眾福利減少之負(fù)面效應(yīng),引發(fā)系統(tǒng)性社會(huì)風(fēng)險(xiǎn)。或者說,在不完備民主社會(huì)里,盡管“減稅”的經(jīng)濟(jì)效應(yīng)(創(chuàng)獲物質(zhì)財(cái)富與精神財(cái)富的活動(dòng))較為積極,至少利大于弊,但“減稅”對(duì)于那些完全不創(chuàng)造財(cái)富的活動(dòng),比如人際交往活動(dòng),以及不直接創(chuàng)造財(cái)富活動(dòng),諸如政治法律和德治道德等活動(dòng),卻不敢輕言影響的利弊。因?yàn)椤皽p稅”對(duì)不完備民主社會(huì)政治法律和德治道德的挑戰(zhàn)與壓力比較大。這不僅是因?yàn)椤皽p稅”效應(yīng)的影響因素是多元復(fù)雜的,充滿不確定性與歧義性,而且是因?yàn)椋皽p稅”關(guān)系政府與國(guó)民之間權(quán)利與義務(wù)關(guān)系的重新調(diào)整。因此,對(duì)處于全球化和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的國(guó)家,對(duì)“減稅”效應(yīng)更應(yīng)作出理性的判斷。既不能因噎廢食,也不能粗心大意。
第三,就“減稅計(jì)劃”的具體方案而言,其效應(yīng)不僅與方案本身的優(yōu)劣有關(guān),也與不同國(guó)家選擇之“減稅”應(yīng)對(duì)舉措本身之優(yōu)劣以及具體實(shí)現(xiàn)途徑與方法之科學(xué)性有關(guān)。換句話說,如果一種“減稅計(jì)劃”的目的是增進(jìn)全社會(huì)和每個(gè)國(guó)民的福祉總量,且是敬畏人道自由、公正平等原則,其實(shí)施途徑是法治、限度、民主的,同時(shí)又是真實(shí)的、非形式的,或者說是納稅者主導(dǎo)的,是普惠的、總量的,是客觀的;等等,而且應(yīng)對(duì)這種“減稅計(jì)劃”的對(duì)策及其具體策略方法也是遵從上述原則,是科學(xué)的,那么,“減稅”的社會(huì)效應(yīng)將趨向積極、正向,“減稅”便有助于增進(jìn)全社會(huì)和每個(gè)國(guó)民的福祉總量。相反,如果一種“減稅計(jì)劃”本身就有悖增進(jìn)全社會(huì)和每個(gè)國(guó)民福祉總量之終極目的,且背離人道自由、公正平等精神,其實(shí)施途徑又偏于人治、無限度、非民主,缺少科學(xué)性,且屬于“偽減稅”、形式減稅;或者說是征稅者、少數(shù)人主導(dǎo)的,是充滿特殊性的、有增有減的,是主觀的;等等,同時(shí)應(yīng)對(duì)這種“減稅計(jì)劃”之對(duì)策及其具體策略方法又不當(dāng),那這種“減稅計(jì)劃”實(shí)施后之社會(huì)效應(yīng)將趨于消極、負(fù)向,這種“減稅”只會(huì)消減全社會(huì)和每個(gè)國(guó)民之福祉總量,遠(yuǎn)離美好生活的實(shí)現(xiàn),自然必須拒絕和否決。
當(dāng)然,如果一種“減稅計(jì)劃”是優(yōu)良的,“減稅”的途徑與方法也是科學(xué)的,但某個(gè)國(guó)家的應(yīng)對(duì)策略卻是拙劣的,或者說這種“減稅計(jì)劃”雖有瑕疵、不完美,但其他國(guó)家的應(yīng)對(duì)策略卻是科學(xué)的、符合實(shí)際的,而且應(yīng)對(duì)策略是充滿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性的,那這種“減稅計(jì)劃”的社會(huì)效應(yīng)或是喜憂參半。即對(duì)“減稅”的社會(huì)效應(yīng),必須作具體分析,不能“一刀切”,即對(duì)“經(jīng)濟(jì)、文化產(chǎn)業(yè)、人際交往、政治、德治、法和道德7類活動(dòng)”以及與非人類活動(dòng)的正負(fù)影響,必須作全面、歷史、動(dòng)態(tài)的深度分析,切不可輕率地下結(jié)論。
第四,就一項(xiàng)國(guó)外發(fā)達(dá)國(guó)家“減稅計(jì)劃”的提出、立法通過及其實(shí)施過程而言,本身也是一種稅收治理的示范活動(dòng),會(huì)產(chǎn)生一定的正負(fù)效應(yīng)。因?yàn)橐豁?xiàng)科學(xué)、文明、優(yōu)良“減稅計(jì)劃”的提出、立法論證與實(shí)施過程,對(duì)于民主政體相對(duì)不完備國(guó)家和經(jīng)濟(jì)欠發(fā)達(dá)的國(guó)家而言,其稅收治理的積極示范效應(yīng)不容忽視,而且是有助于提升全球財(cái)稅總體治理水平,增進(jìn)每一個(gè)人類同胞福祉總量的。退一步講,如果一個(gè)國(guó)家固守落后狹隘的社會(huì)治理理念,拒絕科學(xué)、文明、優(yōu)良的“減稅計(jì)劃”示范與倒逼,那就很難說此項(xiàng)“減稅計(jì)劃”效應(yīng)的積極性了。
總之,“減稅”社會(huì)效應(yīng)是指一項(xiàng)“減稅計(jì)劃”對(duì)財(cái)富創(chuàng)獲活動(dòng)、完全不創(chuàng)獲財(cái)富活動(dòng)與直接不創(chuàng)獲財(cái)富活動(dòng)之正負(fù)效應(yīng),即“減稅”利害經(jīng)濟(jì)、文化產(chǎn)業(yè)、人際交往、政治、德治、法和道德,以及與非人類存在物活動(dòng)之正負(fù)效應(yīng)。根本說來,內(nèi)外“減稅計(jì)劃”之社會(huì)效應(yīng),既取決于一個(gè)國(guó)家最高財(cái)權(quán)、稅權(quán)和預(yù)算權(quán)的民意基礎(chǔ)是否堅(jiān)實(shí),也取決于稅權(quán)監(jiān)督制衡是否擁有“閉環(huán)式”制約機(jī)制。同時(shí),也取決于該項(xiàng)“減稅計(jì)劃”本身之優(yōu)劣及其實(shí)現(xiàn)途徑與方法的科學(xué)性與人道性等要素。■
- 財(cái)政監(jiān)督的其它文章
- 本月財(cái)經(jīng)法規(guī)制度(上)本月財(cái)經(jīng)法規(guī)制度(上)
- 大型企業(yè)財(cái)務(wù)共享服務(wù)中心的建設(shè)與啟示
——以中鐵大橋局的實(shí)踐為例 - 鼓勵(lì)創(chuàng)新相關(guān)稅收優(yōu)惠政策的思考與改進(jìn)
- 加強(qiáng)鄉(xiāng)鎮(zhèn)財(cái)政履職能力建設(shè)的思考與對(duì)策
- 我國(guó)經(jīng)濟(jì)業(yè)務(wù)部門引入非現(xiàn)場(chǎng)審計(jì)制度路徑探索
- 公共政策審計(jì)相關(guān)問題探討及改進(jìn)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