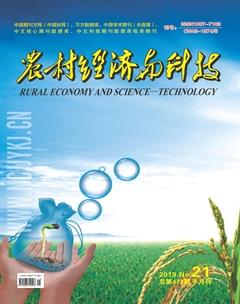社會資本在自助組織中的溢出作用
翁玉華
[摘要]采用參與式觀察和無結構訪談法,以A村自助組織為研究對象。圍繞社會網絡、互惠規范、信任關系與自助組織之間的作用關系,分析社會資本與自助組織的互動機制。繼而呈現社會資本通過自助組織在社區層面的溢出作用:提升村落共同體意識、激活社區參與能力、豐富社區照顧服務、傳承村落文化。基于此,得出結論:社會資本是自助組織生存發展的先行條件,然而自助組織“消耗”社會資本而產生的“能量”不止于個人和群體的雙重性作用,組織所在村莊是其潛在受益者。
[關鍵詞]社會資本;自助組織;溢出作用
[中圖分類號]G302[文獻標識碼]A
1概念界定
根據學者Kate的定義,自助組織是指:為了滿足共同需要,克服共同面對的困難和問題,尋求個人和社會改變的一群人自發形成的組織。學界對社會資本的定義莫衷一是,可以被廣泛接受的是普特南(2000)給出的定義:它是一種重要的私人和公共利益,包括社會網絡、互惠規范和信任關系。社會資本是研究自助組織的重要視角,國內外學者大量研究了社會資本在個人和群體層面的雙重性作用,但目前仍較少有研究關注社會資本在自助組織之外的益處。
2案例簡介
A村地處廣州市從化區北部山區,面積約18km2,下轄6個經濟社,在籍人口745人,常住人口僅212人;村民以種植高山番薯、毛竹及砂糖桔為業;因地處深山,交通不便;又因該村屬于水源保護區,不宜發展工業及家畜養殖業,因此經濟較不發達,青壯年多外出務工,留守村莊的多為老年人及婦女兒童。為提升該村的福祉,回應村民的生計需求,在廣東省婦聯和區民政局的支持下,廣東省L社會工作發展中心進駐A村開展“婦女之家”項目服務,L機構以 “城鄉合作、公平貿易、共創生態文明與可持續生活”為愿景,關注婦女創業、社區互助、社區教育,探索鄉村可持續生活方式,陸續培育了生態種植與青梅加工小組、開心娛樂廣場舞隊、竹編小組、腐竹小組等娛樂性自助組織以及經濟生產自助組織。
3 文獻回顧
在分別梳理自助組織”、“社會資本”以及關鍵字同時包含二者的相關文獻中發現,社會資本是倡導自助組織和社區發展計劃的重要基礎,學者們十分關注社會資本和自助組織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為清晰呈現二者關系,將文獻梳理如下:
3.1 社會資本是自助組織發展的必要基礎
社會網絡、信任關系、互惠規范作為社會資本的基本構成內容是自助組織成立及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學者熊躍根、何欣(2005)以病殘青年俱樂部為例,在闡述自助組織和自助組織成員社會資本兩重性變化的過程中提到:成員參與群體的時候,會將他在其他網絡中的社會資本帶到這個剛參加的群體中來,成員所攜帶的社會資本為俱樂部的整體發展提供了便利。同理,缺少社會資本的自助組織則難以建立和持續發展。正如Thorp等人(2005)所指出的那樣,長期貧困人群處在組織形成的不利地位中,因為他們缺少權利和資源,Kuntala等人(2006)則使用行動研究方法證實:過分強調貧困婦女自助組織的成立而未考慮到這些邊緣化群體所遭遇的社會資本不足,諸如文化水平低、健康狀況差、社會網絡窄的實際限制,導致印度東部Burdwan地區自助組織的成功率低于發起者的期待。
3.2 自助組織是社會資本積累的重要平臺
當代研究表明,組織成員的定期社會互動,有助于成員個人及組織社會資本的發展,社會資本是一種可在組織中培育的資源(Putnam&Campbell,2010)。例如,學者Al Mamun(2014)對馬來西亞半島集團提供的低收入婦女小額信貸互助組織項目作用進行實證調查表明:自助組織為她們提供了投資人際關系的支持性環境,這顯著提高了受訪者之間的互動、信任和合作,最終提高她們建立資本的能力。治療性自助組織則為遭受社會排斥的成員提供一個與他人建立關系的機會、成員在互助的過程中獲得心理的重構,由此,他們積累了對社會關系的普遍信任感,這為他們建立穩定的關系網絡做好了準備。以意大利酒精依賴自助組織為例,Folgheraiter測量了組員的社會資本指標,結果顯示:成員的社會資本指數與參與時間呈正相關,擁有長期參與酒精相關自助組織經驗的人與年輕的參與者在社會資本總量存在顯著差異;該發現進一步證實,自助組織的關鍵特征是雙向的幫助、相信聯合行動,這些特征回應了社會資本所包含的基本內容:網絡、信任和互惠性規范。
3.3文獻述評
綜上所述,自助組織消耗社會資本,繼而再造社會資本。自助組織需要成員的原始社會資本才得以建立并解決共同問題,在集體行動的過程中進一步產生了個人和群體的社會資本。同時,可以發現,在二者關系的探究中,學者們十分關注社會資本在個人和組織發展兩個維度所發揮的基礎性作用及其積累過程。目前還較少有研究關注自助組織在成員和組織之外所積累的社會資本(Knowles 201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自助組織和社會資本的作用結果不僅停留在個人和參與群體的兩重性變化,有效的自助組織將無形的增加社區的社會資本總量。學者Knowles和Saha均選取印度小額信貸項目下的自助組織為研究對象,分別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探究了自助組織為社區層面的社會資本所做的貢獻。學者們在這方面的有益嘗試,為本文探究社會資本在自助組織中的溢出作用起到啟發作用。
4社會資本和自助組織的互動機制
4.1 社會網絡是自助組織的支點
社會學家布迪厄、林南和科爾曼都認可社會網絡的工具性功能,他們都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個人通過自身所擁有的社會網絡關系而獲得的資源。也就是說,個人可以在網絡中獲得實質性的幫助和信息,從而實現個人和組織的活動目標。過去,A村村民與親房共同住在傳統建筑“圍屋”中,婚喪嫁娶都由親房共同操辦。近十年來,隨著政府給予每戶村民的建房補助政策落實以及村民對城市生活的想象,A村幾乎家家都拆了圍屋建小洋房,獨戶獨院的生活方式擠壓了公共空間也疏遠了鄰里親房關系。正如村民所言:“白天開工,休息也不回到一處去,少去(親房家里)喝茶了,以前聚在圍屋大廳包糍粑,現在沒有了。”(ST大叔)
“婦女之家”項目開展初期,為重新粘接村民的社會網絡,社會工作者從最容易吸引人群的娛樂活動入手,鼓勵婦女們共同學習舞蹈并組建廣場舞隊。為培養村民自助互助的能力,社會工作者引導隊員從村民和廣場隊都需要舒適穩定的的公共活動空間這一迫切需求入手,鼓勵隊員整理裝飾舊村委樓,將之改造為全村聚會的重要場所。A村廣場舞隊婦女還積極主動的擴展網絡,授予鄰村婦女組建廣場舞隊的經驗,并陸續組織了三村聯合新春聯會、六村廣場舞大賽等活動。值得一提的是,活動經費的申請亦是得益于婦女的人際網絡,廣場隊某一隊員的丈夫在村委會工作,因而她了解到村委會有一定預算可以投入到社區活動當中,獲取該信息后,婦女們與村書記商量并順利爭取了村委會的贊助。活用社會網絡,使得A村廣場舞隊從單純的文娛小組成長到可以自主開展活動并回應村民文娛需求的自助組織。
4.2 互惠規范是自助組織的保障
A村生產性自助組織的初衷是團結小農智慧來應對市場化的共同困難,生產生態產品吸引城市用戶以獲得收益,采用無化肥生產保護鄉村生態。顯然,相較前文的娛樂性自助組織,生產性自助組織存在更復雜的利益交匯,集體行動面臨更大的挑戰。因此,自助組織不能僅是人的集合,要順利的開展互助自助行動,還需要集合制度規范,規范是自助組織發展的要素之一,也是社會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普特南所認為的那樣,互惠規范有助于解決集體行動中的困境。因為規范督促人們在互動的博弈中認識到:實現個人利益的同時也需兼顧他人的利益。
A村腐竹小組的成功正得益于此,該小組的規章制度由全體成員共同決策而得,小組成員定期舉行會議探討組織工作。在小組成立之初,組員就達成了“共同責任、按勞分配”的基本共識,團體的每位成員共同出資,共同生產,生產的人工成本按照工時計算成本,收益共享,并抽取收益的固定比例投入到本村公益服務。而A村生態種植小組解散的導火索也正是規范的不成熟,該小組是A村第一個生產性自助組織,可借鑒的實踐經驗不足。生態小組在規范尚不明確的情況下開展集體行動,因而在生產行動中,陸續出現成員出勤率低、積極性不強、收益分配矛盾等問題并最終導致小組解散。對比可見,規范是成員對期望行為和風險規避的共識,有利于自助組織在互動中降低交往的成本達成一致行動,是社會資本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
4.3 信任關系是自助組織的核心
意大利學者Folgheraiter(2009)研究發現:信任,這一社會資本的重要方面,隨著參與自助組織而增長。該發現與普特南對信任的解釋契合,他認為:信任是一種期待,人們期待被幫助人未來會給予回報,這種期待被多數人認可時,信任就在群體中產生了,同時這種信任促進了成員對互惠規范的遵守,對規范的遵守又進一步增強了信任。科爾曼則認為,信任的產生與權威的形成類似,都是從人們轉讓某種資源開始的,二者的區別在于:信任強調行動者在關系中考慮風險因素,權威關系則更強調控制權。
自助組織的信任涉及人們產生的對組織和對成員的感受,自助組織的社會網絡為成員增加了自尊和聯系,因而產生信任,對規范的共同遵守又鞏固了成員互信。A村自助組織的形成仍是基于村民間的普遍信任,成員在村莊的口碑和信用對其是否能夠順利加入組織發揮著影響作用,管理者則通過正式程序由組員選拔而產生,她們有明顯的特征,諸如: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可熟練使用漢語對外溝通、更懂得使用媒介平臺。管理者的存在意味著組員讓渡了部分決策權,具有能力優勢的管理者如何保持被信任而不是權力的壓迫得益于平等的交流和信息公開。A村自助組織的生產計劃、社區服務方案等行動內容均在例會中由成員共同商討產生,管理者在例會中則扮演引導者角色并在活動階段即時公開財務信息。基于此,成員間互信與對規范的遵守在自助組織網絡中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5社會資本在社區層面的溢出作用
Knowles等人研究發現:透過集體行動,社會資本可以投資于更廣泛的社區。社會資本的發展不限于自助組織及其成員,而是通過個體參與集體行動對社區產生實質性的影響。為調查A村自助組織對社區的潛在益處,筆者駐村實習,調查訪問了該村村委、社會工作者、鄰村村民、自助組織成員以及社區中的非自助組織成員。調查結果顯示:村民參與A村自助組織發起的集體行動,有助于增加有形社區資源,也有助于無形社區資本的生成。社會資本經由自助組織發酵后,在社區層面的溢出作用主要有以下幾個表現:
5.1 提升村落共同體意識
田胡杰(2018)認為,“合村并組”的推行打破了傳統村落的邊界,加劇熟人社會的瓦解,進而使村民對新社區產生一定的抵觸情緒,減少了村民們對村莊的認同感。村落共同體意識提升主要是指村民對村莊的情感從低情感認同到有一定程度的歸屬感再到采取行動守護村落。A村自助組織的存在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激活村落認同感的作用。以公共空間改造為例,廣場舞隊隊員首先裝飾了舊村委大禮堂,而后社工協助該村自助組織向“招商局幸福家園項目”申請了空間改造資金,自助組織成員們則號召村民共同參與空間的修繕,完成了禮堂改造、兒童樂園和婦女之家的設計布置,使其成為全村老少可以娛樂聚會的共同場所。此類自助組織帶動村民共建美好家園的活動喚起了彼此對村莊的情感認同,村民的社會生活不僅限于對自身益處的考量。正如生態種植給村莊帶來的“健康生活、守護村莊生態系統”等理念,成員Y姐說到:以前我想小孩吃的健康,就不用化肥種菜,現在我也會想為了保護我們村莊的土壤,所以帶動大家少用化肥、不用化肥。即使該生態小組最終解散,但該村的大部分村民都在種植中減少了對化肥的使用,還激發了村莊其他婦女開始以種植生態蓮藕為實踐的個體創業。
5.2 激活村莊參與能力
社工在培育A村自助組織的過程中,始終堅持以村民為主體,注重村民參與策劃,培養村民骨干。隨著該村自助實踐經驗的傳播,不少公益人士被吸引來參觀學習,村民骨干們則擔任“社區講師”,從主體視角總結歷程、分享經驗,這打破了傳統農村社會工作中的客體視角,村民在其中得到參與能力的提升和自信,這促使部分村民成為A村的村莊精英并在村落中產生了權威和號召力。在“城鄉匯”、“食物工作坊”、“腐竹制作體驗”、“自然教育”活動中,這些村莊精英又帶動村民參與城鄉交流活動,在此過程中加強了村民自我認同感和村莊婦女參與處理村莊事物的能力。在最近一屆的村委換屆選舉中,不少曾經“參與冷漠癥”的村民都突破自我設限,積極參與了村委和監委會委員的競選。
5.3 豐富村莊照顧服務
該村青壯年多外出務工,留守村莊的多是老年人和婦女兒童,自助組織成立后,開展了多項面向該群體的照顧活動。組織成員義務為長者理發、教授老人保健操、節假日組織村民們制作各類糕點美食贈與老人;策劃并開展兒童夏令營、繪畫比賽、親子活動等各類文娛活動豐富兒童的生活。
5.4 傳承村莊文化
為了更好的向城市居民和參訪者介紹村落,組織成員常家訪做長者口述歷史,向老年人了解本村歷史、村落風俗、圍屋建造技巧、記錄歌仔(當地特殊的歌曲形式)。生產性自助組織力圖生產與工業化不同的鄉村原味產品,在此過程中組織成員常主動的向老年人學習傳統工藝,如:茶油蜂蠟唇膏、編織、腐竹以及生態種植技巧。此類行動一方面激發了老年人的生命價值感,另一方面鼓勵當地青年兒童了解并參與保育村落文化。在駐村基金會工作者的幫助下,村民還與美術家共同選取了一座圍屋作為鄉村美術館,陳列能體現村落文化的系列作品。
6結語
對于自助組織生長中促成社區資本溢出的關鍵要素,筆者尚未著墨,對此有以下幾點思考:定期會議和活動的必要性,如Polson(2013)指出的那樣,當人們定期互相交流并建立信任關系時,他們更有可能共同努力實現共同目標并解決社區問題;社工的支持引導,在該村自助組織培育過程中社工所實施的社區教育是促成社區意識形成的重要一環,是社會資本得以溢出的關鍵點之一;開放性和封閉性:組織的發展階段對于群體的密度有不同的要求,組織需要調整方能維持和再生社會資本。
對本論文,筆者亦有如下幾點反思:與其他社區和村落相比,該案例村莊所存在的資源具有不可復制性,因而選擇該村自助組織作為個案在解釋性上存在局限性;本文主要描述了社會資本的積極作用,暫未呈現它潛在的消極功能,例如將社會資本作為自助組織發展的先決條件,實踐中可能已經排除了缺乏或缺少社會資本的村民參加自助組織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 何欣,王曉慧.關于自助組織的研究發展及主要視角[J].社會學評論, 2013(5):61-69.
[2] Knowles G,Luke B,Barraket J.Investing and reinvesting in social capital: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in self-help group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13,25(3).
[3] 熊躍根,何欣.我國城市弱勢群體自助組織的社會資本的建構與發展——北京市病殘青年俱樂部的個案研究[J].中國社會工作研究,2005.
[4] Thorp R,Stewart F,Heyer A.When and how far is group formation a route out of chronic poverty?[J]. World Development,2005,33(6):907-920.
[5] KUNTALA LAHIRI‐DUTT,Samanta G.Constructing Social Capital: Self‐Help Groups and Rural Womens Development in India[J].Geographical Research,2006,44(3):285-295.
[6] Al Mamun,A.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Group-based Microcredit Programme in Peninsular Malaysia[J].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Economics,2014,26(1-2),33-59.
[7] Folgheraiter F,Pasini A.Self‐help Groups and Social Capital:New Directions in Welfare Policies?[J].Social Work Education,2009,28(3):253-267.
[8] Saha S,Annear P L,Pathak S.The effect of Self-Help Groups on access to maternal health services:evidence from rural India[J].Int J Equity Health,2013,12(1):36-36.
[9] 文博華.公租房社區社會資本培育研究[D].上海:華東理工大學,2018.
[10] 田胡杰.有序參與、社區認同與村莊共同體再造[J].社會治理,2018, 28(08):2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