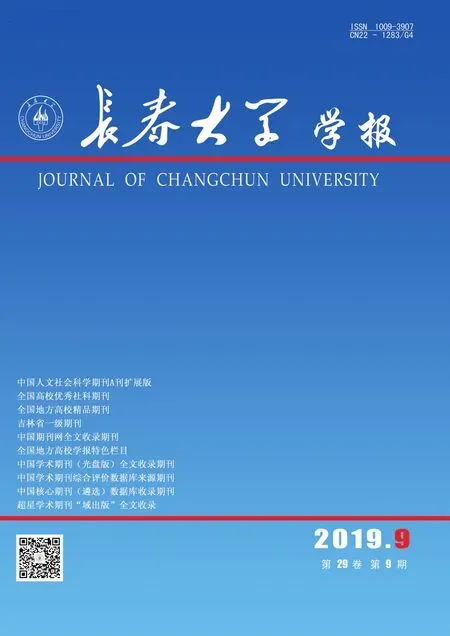文學翻譯:還“陌生”以“陌生”?
劉為潔
(廈門理工學院 外國語學院,福建 廈門 361024)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是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什克羅夫斯基(Shklovskij)在《藝術作為手法》一文中對語言進行變形之后所具有的文學性作出的非常著名的解釋。它的要義在于,文學文本要在語言和情節設計上“陌生化”于慣常做法,“使事物變得陌生,使形式變得困難”[1]。這里的“形式”不是與“內容”相對的,不是通常所認為的“思想的外殼”,而是指藝術作品的創造方式。這種創作方式往往直接體現作者的陌生化意圖。陌生化的翻譯過程因“異”而起,無“異”則無“譯”;此處的“異”不僅體現在陌生化語言形式上的偏離,還體現于文化意義上的偏離。因此,陌生化可謂是作者在形式層面對相關常規語言有動因的偏離的一種邏輯活動。而由于翻譯與譯者的文化熏染息息相關,那么陌生化翻譯作為文化問題便是對譯者的一大考驗,即對“異”的處理方法如何。
本文結合陌生化翻譯的具體實例分析,試以類比的翻譯策略從實現層、形式層和語義層三方面來探討陌生化語言在跨文化語境下實現文學性對等的根本路徑。
1 陌生化語言的英漢偏離形式
就文學性而言,陌生化最鮮明的特征就是挑戰常規,但并非指晦澀難懂,而是讓原來熟悉的事物變得新奇,是一種去除熟悉感、打破認知慣性的藝術手法。也就是說,陌生化是對常規的一種偏離。陌生化語言的關鍵在于常規語言和偏離語言所構成的互文張力。互文源自以往常規搭配所提供的關聯性,張力來源于常規與偏離之間在當下所構成的不連貫性,因此,常規和偏離之間的張力是一種特殊的平衡關系。
實現這種關系的平衡需要譯者尋求形意關系的最佳平衡點,否則就會稀釋陌生化的作用力,危及譯語文本的詩學價值和連貫性。譯者想要再現陌生化意圖,就必須在譯語文本中生成偏離式語言以仿造互文張力,這就是為什么有些學者主張還“陌生”以“陌生”的原因所在。然而,譯語文本的偏離雖從文化意義上可呈現多樣性,但在具體實現中又離不開現實特殊的語言形式,可以說,偏離的具體方式取決于語言形式的具體特點。
語言形式是制約譯者再現陌生化意圖的因素之一。進而言之,陌生化語言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文本系統的一部分,構成文本連貫的一環,只不過它所構成的連貫是特殊的連貫,或者說“有標記連貫”。有標記連貫的標記性源自偏離,而偏離以常規為背景,常規語言就是屬于文本系統中的“無標記連貫”,沒有常規就沒有偏離之說。因此,按照常規的語言特征劃分,英語可用于創造偏離的方法大致可分為五類:語音書寫層面的韻律、諧音、疊詞、擬聲詞等;詞匯層面的同音異形詞、雙關語、字謎、仿擬等;語義層面的非常規搭配等;句法層面的倒裝結構、違反語法常規的句法、排比重復等;篇章層面的回文、嵌字句、歇后語等。
本文將以上五類劃分歸納為實現語言偏離形式的三個層面:實現層、形式層、語義層。其中,實現層包括語音偏離和書寫偏離;形式層包括詞匯偏離和語法偏離;語義層包括語義偏離。譯者翻譯陌生化語言時,首先就需要參照三個層面的語言特征對陌生化語言的偏離方式有所把握,然后在此基礎上解讀其文化意義,實現跨文化交流。
回顧陌生化的翻譯研究,文學翻譯中的陌生化形式、意義及其翻譯策略引起許多研究者的關注。學者們討論文學性的對等時主要關注的往往是文學語言的“形式”。然而,翻譯范疇中的陌生化概念遠比形式主義學派的復雜,具有雙重文本性和跨文化性[2]。因此,不少翻譯學者認為陌生化語言是不可譯的。就文本類型而言,文學性越高的文本就越具有更高的抗譯性,難以用另一種語言完全再現;就翻譯主體而言,由于受其文體和詩學意識的限制,譯者難以充分表現源語的陌生化手法。陌生化語言的可譯性歸根結底都歸因于語言的不完備性[3]79。而語言的不完備性決定了語言的意義潛勢這一命題,所以文本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是開放性的,這才給讀者提供了“見仁見智”的思考空間。
其實,不管文本和文化語境如何多變,語言自身就有一個不斷豐富更新的過程,唯有如此,它才能推動不斷涌現的“異質”的表達形式和滿足人們的審美需求;不管語際之間的語言差異有多大,任何一種語言系統都是自足的、具有表征性的,譯語和源語之間雖然不可能“完全對等”,卻可以最大程度地向“對等”趨同;譯者不能保證將源語中所有的偏離形式加以體現,卻可以恰當的翻譯補償策略最大化地再現源語的陌生化手法。換句話說,語言符號是有限的,但語言符號的組合可以表達無限的意義,在語言的轉換過程中造成的意義上的偏離都能在另一語言系統中得到補償[3]104。
2 陌生化翻譯的類比策略
上述的分類對研究文學作品語言形式及其中所展現的陌生化特征具有重要的參考作用。那么,在翻譯過程中,漢語是否有與英語相對應的偏離方法呢?如果沒有,漢語是否為譯者提供其他方法作為補償?以往研究者在研究陌生化翻譯時提出的策略不是異化就是歸化。然而,理想的譯文應該是歸化、異化適度,歸化和異化并不截然對立,乃至譯語讀者既看不出“歸”也看不出“異”來,悄然入于錢鐘書先生所說的“化境”。因此,具有敏銳詩學意識的譯者往往需要在“同”和“異”之間把握尺度,方能在二者之間游刃穿梭,把握互文張力的最佳平衡點。
過分歸化,將掩蓋源語語篇所蘊含的異域性特征,導致文學性的流失;過分異化,陌生化往往被陌生性所覆蓋,而陌生性可能觸發讀者對他者的排斥,壓縮讀者的闡釋空間和減少閱讀的趣味。無論何種形式,都將導致詩學價值的不連貫,難以讓譯語讀者產生相應的文化聯想。因而,以類比的翻譯策略恰恰是遇到文學性較強的文學文本時在特殊語境中所采用的動態、辯證的處理方法,不能把它簡單地歸結為歸化或異化。
從性質上來說,類比就是根據兩種語言在形式或功能上的相似以一種語言的表現手段表征或象征另一種語言的表現手段。它是基于兩種語篇的形式對應而不是語義等值[3]223。從具體操作上來說,類比就是譯者選用譯語本土語言文化材料在譯語文本中仿造陌生化形式的翻譯策略,通過以“相似”為向度的類比法可以消除微觀層面“遣詞造句”等方面的“不可譯”,彰顯源語的“形”、“意”特色,使陌生化手法“現形”,通過手法的靈活調變尋求陌生化意圖的“不變”。
下文旨在弄清在跨語言文化轉換的過程中,譯者能否在實現層、形式層和語義層三個層面以類比的翻譯策略在譯語文本中生成偏離、仿造陌生化形式的同時,將作者的陌生化意圖明確傳達給譯語讀者。這些問題對于想仿造陌生化形式的譯者和研究者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1 實現層的類比
實現層的陌生化包括語音和書寫偏離。當然,語音偏離與書寫偏離經常有重疊之處。語音偏離指文本中某個或某些詞語的發音違反語言系統的發音規則。現實生活中,由于情緒、受教育背景、方言背景或者仿諷他人等原因,人們在發音上有時會表現出與規范發音相距甚遠的個人色彩。但譯者仍舊可以利用錯音字來進行類比翻譯。錯音字即用近似音來標示“不標準”的普通話讀音,如我們網絡用語中就常用“趕腳”表示“感覺”,“醬紫”表示“這樣子”等。在文學作品的翻譯中,譯者在翻譯AdventuresofHuckleberryFinn時就使用了這種方法突顯老黑奴吉姆的種族和方言背景,如用“陀舊”代替“多久”,“史什摸人”替代“是什么人”。各地方言不同,因而在聲母、韻母、聲調等方面各有各的“不標準”,因此,聲母、韻母、聲調等都可用于變形,聲母如“f-h”“r-l”“z-zh”“c-ch” “s-sh”“n-l”“d-t”“j-z”,韻母如前后鼻音之分,聲調如一個調到尾。
書寫偏離指的是對書寫規范的違反,這種違反既可以在字/詞之內表現為誤拼誤寫某個或某些字/詞,也可以在字/詞之間則表現為違反正常的排列規范,文學創作者便泛化這些形式規則,把原來不組合在一起的語素組合起來,構成新詞。這些新詞作為對現有詞匯的擴展,形式上的張力非常引人注目,而漢譯也同樣可以類比的方式讓讀者耳目一新。如SnowWhite中的一例:
原文:I am tired of being just ahorsewife.[4]
譯1:我厭倦了僅僅做一個家庭主駙。[5]
譯2:只當個家庭煮婦我已經感到厭煩。[6]
小說中,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同住,組合成一個現代“家庭”,她日復一日地為他們做家務,成了他們的家庭“煮”婦,她厭煩了自己的家庭角色,對歧視女性的社會忿忿不滿,希望改變現狀從平庸中得到解脫。不難看出,原文horsewife是housewife在形、音上的變異。在文學創作中,作者有時候會對某個符號進行變異,使它在形或聲上臨摹符號所描寫對象的某種特征。這些形/聲偏離符號原本并無擬聲/擬像理據,但是特殊語境和作者的陌生化意圖賦予了它們臨時理據。在這里,作者就凸顯詞的理據,表達了她的言外之力。從符號上看,horsewife是一個偏離符號,能指是其音響形式或書寫形式,所指是家庭主婦。當相關的horse及其引申義被激活時,這一能指就派生出另一能指,即“做牛做馬”的主婦。在特殊的語境下,當雙關語指向后一種能指所表達的意義時,用字面直譯成“家庭主婦”的常規譯法會使譯語和源語發生沖突,不能再現作者的陌生化動因,此時,譯者就應該用新的表征方法將其透明的文化意義陌生化,突顯動因。
譯1中,“家庭主駙”的譯法雖然在“音”的偏離形式上看似保留了,盡管譯者在語音層面下了功夫,但沒處理好譯語的形和義傳遞的最佳語境關聯信息,普通讀者不可能在horsewife和“主駙”之間找到關聯。也就是,源語是雙關語而譯語不是,沒有讓譯語最大限度地折射出說話人的陌生化意圖。如果譯語讀者不能辨別譯者的陌生化形式仿造的意圖,那么這種形式的仿造就是失敗的。譯2的“家庭煮婦”雖與“馬”不對應,但“煮婦”和“主婦”音似,在形式上相關,且在語義上暗涉“女人只限于廚房‘做煮(主)’”,將“主婦”概念陌生化了,可類比horsewife蘊含的“做牛做馬”之義,與“主駙”相比,文化批判意味更加明顯。horsewife之于housewife自然不同于“家庭煮婦”之于“家庭主駙”,正因其間既存在相似性又有相異性,我們才稱作類比。所描寫對象的相關文化特點是譯語讀者所熟悉的,讀者可以把陌生化語言中的偏離特征和被描寫對象聯系起來,從而把握兩者之間的臨時像似性。英漢兩套語音和書寫特征都是在各自文化里才能表達它的本土文化意義的。因此,即使譯者以譯語本土的語音、書寫偏離去對應源語文本的語音、書寫偏離,它引起的是本土聯想,而非源語的文化意義,所以譯者只能訴諸于類比在本土文化語境中構建臨時像似性。但這種像似性應為譯語讀者所識解,如“家庭煮婦”;而不能讓偏離形式成為一種陌生性,如“家庭主駙”。
2.2 形式層的類比
形式層包括詞匯偏離和語法偏離。詞匯是作者或譯者通過靈活運用現有構詞規則,創造出現有詞匯中不存在的詞語。不過,新詞雖新,卻是依據原有規則創造出來的,或者至少與現有詞匯存在某種聯想關系,讀者結合上下文語境基本可以理解這些新詞。在新詞創造方面,不僅“詞”在英語和漢語中的地位不同,而且兩種語言造新詞的方法也不同,因而兩種語言的新詞表現出來的張力在程度和方式上有所區別。如:
原文:He went to India with his capital, and there, according to a wild legend in our family, he was once seen riding on an elephant, in company with aBaboon;but I think it must have been aBaboo——or aBegum.[7]
譯1:他帶著我姨婆給他的這筆錢,到印度去了。據我們家里一種荒乎其唐的傳聞,說在印度,有一次有人看見他和一個馬猴,一塊兒騎在大象身上。不過,據我想,和他一塊兒騎在大象身上的,決不會是馬猴,而一定是公侯之類,再不就是母后什么的。[8]
譯2:他拿著錢到印度去了。我們在家里聽到的傳說簡直神了,說有人在印度看見他和一只狒狒騎在大象身上,不過我想那一定不是狒狒,而是位紳士,或者公主。[9]
《大衛·科波菲爾》本就是一部兒童文學名著,狄更斯在此精心挑選了3個博得孩子一笑的俏皮詞匯,Baboon、Baboo和Bagum。它們在詞匯形式的創作上不僅形式相近,而且音韻相似,整個句子因為詞匯的偏離盡顯童趣。譯1為了傳達這種俏皮的韻味,也用了3個發音相近的漢語詞,但語義卻與原文發生了偏離。原文中的Baboon指的是狒狒,這里卻譯為“馬猴”,語義上雖有出入,譯者的陌生化意圖卻不難被讀者識解;而“公侯”“母后”的詞匯偏離形式看似“無稽之談”,卻和“馬猴”在音、形、義的創造上產生了語用關聯的連續性,在字面意義上雖談不上等值,但類比的語用效果卻是對等的,源語的趣味性及形意之間的張力完全可以讓讀者“心領神會”。譯2將這幾個詞直譯為“狒狒”“紳士”“公主”,語義雖然準確無誤地譯出了,但讀者很難在詞匯的音、形、義上找出其間的關聯性。其實,英語中并沒有Baboo和Bagum,但前文提及“拿錢去了印度”,所以這兩詞應是仿造印度語發音的英語仿擬詞,作者獨具匠心,將兩種語言和文化雜合以創造語篇的陌生化效果,實乃文豪手筆。在印度語中,Baboo指的是印度穆斯林土邦的公主,Bagum則是印度人對尊貴人士的稱呼。如果譯者沒有從上下文識別出作者的陌生化意圖,就不可能仿造偏離,那么源語幽默的陌生化意趣蕩然無存,更談不上文學性的對等;而如果譯者采用譯語詞匯偏離去對應源語詞匯偏離,首先就必須將語義邏輯本土化,即替換源語文本的語義內容,譯語讀者才能辨識和把握形式上的偏離意圖。
語法偏離是指對語法規則的違反和擾亂,以致在詞句組合上顯得不合語法。“漢語的語法不像英語那樣有顯露的外在形式,……它不是通過形式(form)或形態(morphology)來表示語言成分之間的關系,而是讓語義本身來體現這種關系的”[10]。英語語法的“剛柔并濟”恰恰為偏離提供了條件和參照,使偏離的語言形式獲得明顯的對比張力。相比之下,隱性且彈性的漢語語法則無硬性語法形式要求,所以作者或譯者難以用它來塑造形式上的對比和張力。一般情況下,英語語法形式只是語言使用的基本規則,文體價值不大,譯者無須過多理會。但有時候,作者會違反語法規則,在形式上與上下文形成對比、聯動和互動,表達特殊含義,此時扭曲的語法形式成為臨時的新符號,參與文本主題意義的表達,對譯者構成挑戰。如:
原文:Next came an angry voice——the Rabbit’s——“Pat! Pat! Where are you?” And then a voice she had never heard before, “Sure then I’m here!Digging for apples,yerhonour!”
譯1:再一會兒,就聽見很發怒的聲音——那兔子的聲音——“八升!八升!你在哪里?”她聽見一個先前沒有聽見的口音問道:“我在這兒,老爺您哪!我在這兒地底下掘蘋果,老爺您哪!”[11]36
譯2:接著傳來的是一陣生氣的叫聲,那是兔子的聲音:“派德!派德!你在哪里?”接著是一個她從沒聽過的聲音:“是啊,我在這里!在挖蘋的果,老的爺!”[12]93
每種語言都有獨特的擇句選詞、修辭、話語標記等語言形式,其自身的形式特點從根本上限定偏離的可能方式。而上文中的Digging for apples是典型的語法偏離,dig和apple這兩詞完全搭配不當,這樣源語的陌生化手法給讀者就注入了新鮮、意外的感受。語言形式承載意義,甚至是文化意義,讀者完全可以從上下文找出一些線索,還原作者的陌生化意圖。Digging for apples的前面出現了一個人名Pat,相信源語讀者肯定能辨識Pat是典型的愛爾蘭名字。所以,Pat提到的yerhonour是your honour的語音書寫偏離形式,同時雜糅了英語和愛爾蘭語言的文化。而Pat口中的apples實際上是指“愛爾蘭蘋果”(Irish apple),意為“馬鈴薯”。擅長語言邏輯游戲的卡羅爾故意為之,以dig搭配apples。譯1把Pat翻譯成“八升”,“升”是中國式的計量單位,這種過度的歸化翻譯鈍化了讀者對源語中蘊含的異域文化的認知,更難以聯想到“八升”與“掘蘋果”之間有何關聯性,偏離形式的仿造沒有深化文本主題意義,也未能讓讀者產生相應的文化聯想,因此就難以收獲與源語讀者類似的陌生化效果。譯2中“蘋的果”、“老的爺”是對語法偏離形式的翻譯的一種創新性挑戰,屬于類比式的仿擬,體現于“蘋的果”與“蘋果”的差異,“蘋的果”與“愛爾蘭蘋果”的共現。盡管“在挖蘋的果”與“digging for apples”,“老的爺”與“yerhonour”在語法、語義上都不能對等,但陌生化的語用效果是等值的,讀者能體會到譯者仿造語言游戲的樂趣。可見,抽象的、主觀的動因都可以落實和體現為具體的、客觀的上下文符號關系。可以說,上下文符號介于偏離式語言和作者的動因之間,既是作者或譯者向讀者傳達意圖的橋梁,也是讀者用于闡釋偏離式語言為何被設計成如其所是的線索和依據。因此,譯語既要體現偏離形式,又要體現作者的偏離動因,這就決定了以“相似”為向度的類比法的“呼之欲出”,因為類比既依賴于本土常規,同時又要打破本土常規的慣性,這無疑構成對譯者的一種挑戰。
2.3 語義層的類比
語義偏離是詞語的基本義與當下意義的類比關系。語義類比屬于語義相似性。常規語言和陌生化語言的區別就在于,常規語言或者是無此相似性,或者是有,但該相似性已被熟知而石化,在閱讀過程中成為認知背景;而陌生化語言的語義相似性則是獨特新穎的,其相似關系由文本語境臨時獲得,具有突出的陌生化效果。請看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第11章的1例:
原文:“——and the twinkling of the tea——”
“The twinkling ofwhat?”said the King.
“Itbeganwiththe tea,” the Hatter replied.
“Of coursetwinklingbeginswith a T!...”
譯1:“……而且那個茶又要查夜——”那皇帝道:“什么東西查夜?”
那帽匠道:“查夜先從茶起頭。”
那皇帝厲聲道:“自然茶葉是茶字起頭!……”[11]128
譯2:“……還有一閃一閃的茶……”
國王問:“什么東西一閃一閃?”
帽匠回答:“我說從一開始——”
那國王厲聲說道:“‘一閃一閃’當然是
從‘一’開始!……”[12]235
雙關語屬于特殊的陌生化語言,在這本兒童名著里占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如果雙關語按字面翻譯,作者的陌生化意圖就會在跨文化語境中立刻被阻斷,獲得的陌生化效果與常規翻譯無異。原文“Of course twinkling begins with a T!”中的twinkle的第一個字母是t,又和前文的tea(茶)同音,成為一個糾纏不清的雙關語。譯1和譯2都沒有按照字面直譯,都用了類比的方法。譯1從一開始就沒有把“twinkling”譯成“一閃一閃”,而譯成“那個茶又要查夜——”,讀者不管從前文還是后文,除了“茶”和“查”是同音字,難以聯想到“查夜”與“茶”之間到底有何關聯,可以看出譯者并沒有識別出作者的陌生化意圖,以致譯者仿造陌生化手法的動因難以被讀者所識別,偏離便難以獲得陌生化效果,也稀釋了陌生化語言的幽默感。實際上,源語中看似“滿紙荒唐言”的陌生化語言的背后蘊含著卡羅爾嚴密的思維邏輯,都是有著很強的互文張力和關聯的“邏輯游戲”。在這里,帽匠想到的是在第7章瘋茶會中提到的歌“一閃一閃傻乎乎……好像茶盤飛四處”。所以,帽匠未說完的句子,可能是“……還有一閃一閃的茶盤”。因此,這種互文關聯讓譯2的譯者領會了作者的陌生化意圖,從而在twinkling上下足了功夫,譯者使用“‘一閃一閃’當然是從‘一’開始”的譯法類比于“twinkling begins with a T”。“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這首童謠對中國讀者并不陌生,讀者應該容易識別譯者翻譯成“一閃一閃”的動因。這樣一來,加上譯者靈活利用tea和T的諧音特點,巧妙地在twinkling和tea之間建立起關聯性。因此,語篇翻譯的質量歸根到底取決于源語與譯語之間最佳的語言和文化的關聯度。當譯文難以直接傳達語篇在音、形、義、修辭等方面的特質時,譯者需要有敏銳的文體和詩學意識,體現源語的常規和偏離之間的張力連貫,有效地傳達作者的陌生化意圖或意蘊。類比式的仿擬可以有效地保持文體連貫性,其語義雖然不能夠等值,卻同樣能達到“妙趣橫生”的奇特效果。總之,陌生化的翻譯屬于文學性較強的翻譯,因此在語際轉換時,首先應對源語的文體偏離作出積極的詩學反應,然后訴諸于超越語言單位但保留陌生化意圖的類比策略,這種意圖無形中打上了譯者作為文化“擺渡人”的烙印。
3 結語
如果說,實現文學性翻譯的途徑是還“陌生”以“陌生”的形式仿造,那這種觀點只探討了偏離形式本身,忽視了偏離形式的文本語境和文化語境,更忽視了翻譯具有轉化詩學價值和構建翻譯文學性的施為力量。因此,決定陌生化“文學翻譯”的關鍵要素不在于陌生化形式本身,“文學翻譯”的實現途徑也不在于陌生化形式仿造,“文學翻譯”行為的決定性要素在于:譯者需要在譯語文本“異質文化形式”與譯語文化本土文學形式之間突出相似性還是相異性。因此,陌生化翻譯的悖論屬性決定了譯者進行還“陌生”以“陌生”仿造形式的同時,還需要譯者具備敏銳的文體和詩學意識,在陌生化語言的三個層面——實現層、詞匯層和語義層上以類比的翻譯策略在跨文化語境下轉移詩學價值并構建其翻譯文學性。類比的翻譯策略是具有動態屬性、辯證的翻譯藝術的處理手段,又是翻譯認識論的科學方法[13],同時也是實現文學性對等的根本途徑。類比的翻譯策略可以讓譯者站在譯語文化的角度,向讀者呈現其觀察源語文化的視角,將“異質”文化轉化為“本土”文化的邏輯,在特殊文本語境中構建臨時像似性,引發譯語讀者對源語文學文化的聯想。當世界進入全球和本土相雜合的時代,我們以陌生化語言的翻譯為旨來思考譯者如何對待“異質”的問題就顯得非常重要和必要,它不單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陌生化語言的翻譯方法,而且有助于進一步認識文化審美活動的需求,并借此重審我們對文學性對等的既有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