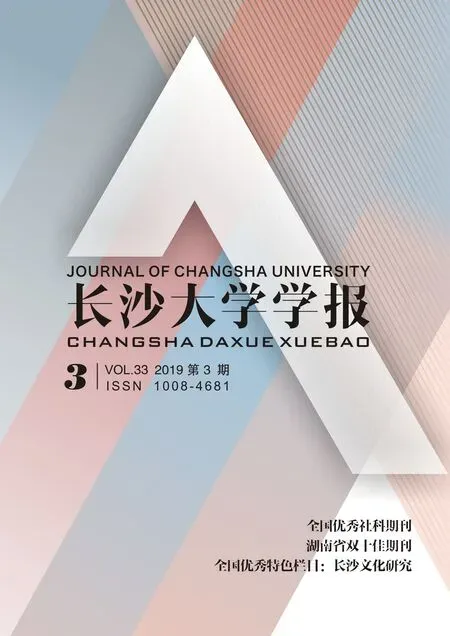《浮世畫家》主人公小野的日本身份認同
王 飛
(長沙學院外國語學院,湖南 長沙 410022)
心理學家埃里克森(Eric Ericson)指出,面對時空變遷,認同主體的身份認同有“更新”和“守舊”兩種傾向,對于認同主體來說,“不僅存在重構適應性身份認同的心理機制,而且還有保護和提升已有身份認同的傾向,(因為)個人有一種保護和防衛自身身份的內驅力”[1]P37。國族身份認同具有典型的本質主義傾向的“身份內驅力”。在遭遇身份危機和焦慮時,認同主體就會選擇努力重構國族身份認同。國族身份認同是“原初身份”(primary identity)的一種,對個人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根據社會學家詹金斯(Richard Jenkins)的定義,“原初身份”是人生早期建立的身份認同,由于其更加有活力和復原能力,所以與其他身份認同相比,原初身份在人生以后的階段更難改變[2]P41。社會學家史密斯(Anthony Smith)在《國族身份》(NationalIdentity)一書中指出,“國族身份認同,通過國族的集體人格與獨特文化,為個人在世界中的定義和定位提供了強有力的途徑”,“與一個國族認同,并非僅指與一個事業或集體的認同,而是通過國族的重生,獲得個人的更新與尊嚴”[3]P17,161。面對身份焦慮,石黑一雄的許多小說人物都通過回憶往事,努力“保護和防衛”作為原初身份的國族身份認同。在石黑一雄的身份書寫中,國族身份認同構成人物身份認同的重要一維。
在《浮世畫家》中,軍國主義畫家小野產生身份焦慮的重要原因,便是面對戰后日本時代的變遷、社會價值的巨變,他卻仍舊堅守個人的記憶和國家的歷史,選擇認同那個已然逝去的軍國主義、封建主義時代的價值觀[4]P27。正是這種沖突讓他產生了嚴重的身份焦慮。在社會價值觀方面,小野沒有能夠與時俱進,而是一直堅守個人的和國家的輝煌過去,試圖為自己重建國族身份認同。正如社會學家所言,對某一國族的“忠誠和貢獻”是國族身份認同極為重要的“標志和原則”。麥克隆(David McCrone)和比籌佛(Frank Bechhofer)將國族身份認同的“標志和原則”定義為,人們在“聲明國族身份、評判他人有關國族身份的聲明”時所使用的標準,這些標準包括“出生地、口音、祖先、膚色、居住地以及對國族的忠誠與貢獻”等[5]P29,99,103。對于一直強調通過職業成就貢獻國家的小野來說,職業身份認同與國族身份認同密切相連。在戰前日本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盛行的背景下,小野的畫家職業生涯將其從功利主義、唯美主義一步步引至通往愛國主義、軍國主義的路上。這四個“主義”,分別以四個導師為代表,其實正是小野畫家職業生涯發展和日本國族身份認同建構的一個路線圖。
一 依托職業身份的國族身份認同
事實上,整部《浮世畫家》就是以敘述者兼主人公小野的身份焦慮與身份認同的沖突為中心而展開敘述的。其中,最核心的沖突就在于,由于世易時移,持有不同價值觀的他人與小野產生沖突而引起他的身份焦慮,以及這與他通過回憶“復活從前的自我”[6]P43而建構和鞏固職業身份認同、國族身份認同之間的張力。小野以日記形式記述的回憶是“一種回顧式的回憶形式,這種形式與講述相似……講述是在沖突、分裂和異化之后所進行的戰勝過去的努力以及共同的分享”[7]P91。正是他對記憶的講述,抵抗了身份焦慮所帶來的“沖突、分裂和異化”,從而建構起以自身職業身份為依托的日本國族身份認同。
正如評論家指出的,在其敘述進程中,小野總“喜歡以其(職業)成就感為中心進行迂回”[8]P49,“他在記憶中來回穿梭,(實際上是在)試圖呈現一個尚可接受的身份和過去”[9]P44。與《遠山淡影》中的緒方以及《長日留痕》中的史蒂文斯相似,小野建構其身份是通過回顧自己的輝煌過去,尤其是自己在過去的社會地位,而這種地位則是通過其在職業當中所取得的成就而實現的。當然,他們的職業又都與各自的民族和時代背景緊密相連。小野關于自己地位的思考貫穿于整部《浮世畫家》。實際上,整本小說大致講了這樣兩個故事:一是在軍國主義盛行的過去,小野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其職業上的成功;二是在世易時移的現在,周圍的人又是如何看待小野的。社會現實引起小野的身份焦慮,他只有通過回憶輝煌的過去、建構自豪的職業身份,才能抵抗這種焦慮。當然,他的職業身份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與日本社會及日本民族緊密聯系在了一起。不妨先來集中關注小野關于自己社會地位的思考。
小說以小野對其“豪宅”的描述開篇,從而引出豪宅的來歷。這棟房子其實是十五年前從杉村家買來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前任房主杉村明的女兒關于房屋買主所做的“信譽調查”。在眾多的“候選人”當中,他們最終選擇了小野,據小野自己的回憶,是因為“他的道德操守和成就”[10]P5。小野在回憶時說,當時“內心深處曾感到多么滿足”,因為這是他當時社會地位和職業成就的最好證明。他的職業身份與社會地位密切相連。小野正是通過向后看,而重新召回了自己的驕傲和尊嚴。小野雖然聲稱“把名聲地位之類的東西看得很淡,本能地對此不感興趣”,也“從來沒有對自己的社會地位有很清楚的認識”[10]P17,卻在小說中通篇回顧自己過去的成就與地位。他擅于用一種委婉曲折、甚至不可靠的敘述方式,從他的豪宅、得到豪宅的經過以及他人對他的評價中,展現自己的地位以及對自己地位的自豪,以此來建構自己的職業身份。另一段來自小野得意門生黑田的評價將小野的社會地位推至頂峰:“如今他的名望已經超出了藝術圈,擴展到生活的各個領域……我個人毫不懷疑,先生的名望還會與日俱增,在未來的日子里,我們最大的驕傲就是告訴別人,我們曾經是小野增二的弟子”[10]P25。
小野關于自身地位的敘述不僅停留在過去,偶爾還會擴展到現實當中。比如與紳太郎在川上夫人的酒館里喝酒這一場景。當川上夫人說起自己一個親戚找不到稱心如意的工作時,紳太郎說:“像先生這樣地位的人推薦一下,不管是誰都會買賬的。”[10]P18關于紳太郎的提議,小野是這樣想的:“其實我心里也知道,紳太郎的斷言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我愿意去試一試,說不定又會為我的影響力之大而感到驚訝。就像我說的,我對自己的地位從來沒有清醒的認識。”[10]P20小野潛意識里將過去的地位與現在的地位相混淆,說明他是想要通過回憶過去進而抵抗現實中的地位落差與身份焦慮。而后來,紳太郎為了在東町中學謀一個教職而來找小野的那一幕,對于小野的身份卻構成了一個巨大的反諷:紳太郎來找小野,要的不是推薦信,而是想求他寫一封信,以聲明紳太郎曾反對過他所提倡的軍國主義觀點。
二 從愛國主義到軍國主義的身份認同
值得注意的是,小野在回憶過去的社會地位時,總是將自己的地位與所謂的“日本的新精神”相聯系。比如,他回憶由于自己的努力而促使左右宮開業時說:“這又一次說明,人有時候會突然發現他的地位遠比他自己以為的要高。我從來不把地位放在心上,所以帶給我這么大成就感的并不是左右宮的開業,而是我很驕傲地看到我一段時間以來堅持的觀點得到了支持——也就是說,日本的新精神與自我享受并不矛盾。”[10]P78把這段話與小野在小說后面回憶自己在左右宮對學生說的話相聯系,便能看出小野作為畫家的社會地位與他所說的日本“新精神”的內在聯系了。他對學生說自己一直以來努力在做的就是“超越我們周圍那些低級和頹廢的影響”,發揚與傳承“我們民族的精魂”。下面就是小野關于日本“新精神”的一段“宣言”:“如今,日本終于出現了一種更為陽剛的精神,而你們都是其中的一分子。實際上,我希望你們會成為新精神的先鋒而得到承認……我們大家聚集的這個酒館,就是這種新精神的見證,我們在座的各位都有權利感到自豪”。正是日本的這種“更為陽剛的精神”將經常光顧那里的人“團結在一起”[10]P90-91。小野將宣言的聽眾從桌旁的人擴展到周圍的所有聽眾,將他對自身職業地位的自豪提升至對日本“新精神”的認同與自豪,從而使得他的職業身份認同最終與國族身份認同合二為一。
這種“新精神”其實就是愛國精神,正如接下來小野提到的自己得意門生黑田的一幅名為《愛國精神》的畫作。那一時期黑田的創作反映了小野自身的觀點,黑田成為小野的一個“影子人物”(double)。關于這幅畫小野說:“看到這樣的標題,你大概以為畫面上是行進的士兵或諸如此類的東西。其實,黑田的觀點是:愛國精神植根于很深的地方,在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取決于我們在哪里喝酒、跟什么人交往。”[10]P91得意門生的觀點也就是小野自己的觀點。實際上直到戰后,小野還依然十分認同這樣的“愛國精神”,正如他所說:“今天,每當我看到這幅畫,仍然會感到一種滿足感”。小野的滿足感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自己的社會地位——“我在這個城里的一點威望”,一是愛國精神——“為這樣一個(滋生和促進愛國精神的)地方的開張做了我一點小小的貢獻”[10]P92。我們又一次看到,小野將自己的職業身份認同與國族身份認同聯系了起來。
小野的愛國主義認同在戰前日本的社會背景下逐漸發展成為軍國主義認同。日本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其實早在明治維新之后就開始發酵。流行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一首日本民謠很好地說明了日本當時逐漸抬頭的軍國主義:“很顯然,有一種‘民族法則’/然而一旦時機成熟,定要記得,/就會出現弱肉強食”(There is a Law of Nations, it is true,/ but when the moment comes, remember,/ the Strong eat up the Weak)。這一趨勢發展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全國上下都彌漫著一種創建“大日本帝國”和“大東亞共榮圈”的熱情,詩人、牧師以及宣傳家都極力鼓吹“大和民族”的優越性以及“帝國之路”的崇高性[11]P19-22。整個國家的愛國主義逐漸發展成為軍國主義思潮,這正構成了小野畫家職業生涯發生轉變的時代誘因。若將小野自己的畫作《放眼地平線》與黑田的《愛國精神》對比一下,便可看出這種轉變。《愛國精神》中日常生活的隱性愛國主義變成了《放眼地平線》中士兵們明目張膽的軍國主義。小野這樣描寫他的《放眼地平線》:“畫面下部是一組占主導地位的形象……三個……神色堅定的戰士。其中兩人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中間站著一位軍官,舉著長劍指向前方——西邊的亞洲。他們身后……是一片太陽軍旗……左下角寫著:‘沒有時間怯懦地閑聊。日本必須前進。’”[10]P211《愛國精神》中的喝酒、“閑聊”,此處卻被認為是“怯懦”。小野的愛國主義逐漸過渡到軍國主義。由是,他的日本身份認同也走上了極端的民族中心主義身份認同之路。
三 “影子人物”映射的國族身份認同
致使小野向軍國主義國族身份認同轉變的關鍵人物是他的老同事松田智眾。正如小野自己在這段敘述中將《放眼地平線》與松田直接并置時所說:“我想說明跟松田的相識對我后來事業的影響。”[10]P212由于小野總是透過松田的眼睛來看待自己,而且關于松田的回憶貫穿小說始終,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松田便是小野的另一個 “影子人物”。通過細致分析小說中小野與松田在過去(戰前)和現在(戰后)交往的幾個片段,可以考察小野與職業身份認同交織在一起的國族身份認同。這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小野對自己“影子人物”松田的認同。回憶他倆的初識時,小野第一句就說:“他的思想吸引著我。”[10]P212那么,松田有著怎樣的思想呢?來看下面兩段引文:
“天皇是我們當然的領袖,然而實際上是怎樣的呢?他的權利都被那些商人和他們的政客奪走了。聽我說,小野,日本不再是落后的農業國家。我們現在是個強大的民族,能跟任何西方國家抗衡。在亞洲半球,日本像一個巨人,屹立在侏儒和殘廢中間。可是我們卻眼睜睜地看著我們的人民越來越水深火熱,我們的孩子死于營養不良。與此同時,商人越來越富,政客永遠在那里找借口、扯閑話。你能想象任何一個西方國家允許這樣的局面存在嗎?他們肯定早就采取行動了。”
……
“現在我們應該打造一個像英國和法國那樣強大而富有的帝國。我們必須利用我們的力量向外擴張。時機已到,日本應該在世界列強中占領它應得的位置。相信我吧,小野,我們有辦法做到這點,但還沒有找到決心。而且我們必須擺脫那些商人和政客。然后,軍隊就會只聽從天皇陛下的召喚。”[10]P217-218
此處的引文便是小野通過其“影子人物”松田之口說出的“軍國主義”宣言。小野后來那副代表作《放眼地平線》也正是松田軍國主義思想的形象表達。松田接下來的一句“我們這樣的人,小野,關心的只是藝術”更為明顯地從反面提醒了讀者:小野和松田一樣,都將政治與藝術混為一談,都將職業身份認同逐漸等同于國族身份認同。此外,說松田是小野的“影子人物”還有另一個原因:即使在戰后日本的今天,小野依然選擇認同松田的觀點。可以通過松田去世前小野去拜訪他的那一段敘述看出來:“他當然更沒有理由在幻滅中死去。也許,他回顧自己的一生時確實看到某些瑕疵,但他也肯定認識到,他能夠引以自豪的正是這些方面。正如他自己指出的,他和我這樣的人,我們欣慰地知道,當年我們不管做了什么,都是憑著一腔熱血去做的……當一個人從內心深處產生信念時,一定也會這樣想的。”[10]P252-253小野的這段內心獨白表面上是在評價松田,實際上卻是對他自己一生的反觀和總結。雖然自己的人生有“某些瑕疵”(誰的人生沒有瑕疵呢),但他“能夠引以自豪的(卻)正是這些方面”,也就是他的畫家職業、社會地位以及他“一腔熱血”投入的“軍國主義”事業。
鑒于小野是通過回憶過去從而建構職業身份認同和國族身份認同的,可以說,小野其實一直活在過去,正如小說中的傻子平山小子——小野的另一個“影子人物”一樣。關于平山小子,小野這樣描述道,“在戰爭前和戰爭中,他唱戰歌、模仿政治演說,成為‘逍遙地’著名的街頭一景”[10]P73,得到人們的夸贊。但在戰后,因為不能“與時俱進”[8]P46而變得人人喊打,最終被打得殘廢,送進醫院。反諷的是,小野自己其實就是另一個平山小子,過去的價值觀在他腦海里扎下根來,所以整本小說都充斥著小野的“懷舊”情緒。在對過去的回顧中,他為自己建構了職業與國族合二為一的身份認同,正如小說結尾處他說的那樣:“我經常想起一個特定的時刻——是一九三八年的五月,就在我獲得重田基金獎后不久。事業發展到那個時候,我已經獲得過各種獎項和榮譽,但重田基金獎在大部分人心目中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而且我記得,我們就在那個星期完成了我們的新日本運動,并取得巨大成功。”[10]P253而小野內心充滿了“成就感和滿足感”就不僅僅是針對其畫家職業和社會地位了,更是由于“新日本運動”的巨大成功。小野說:“那是一種內心深處的喜悅,堅信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公正的承認。我付出的艱辛,我戰勝的疑慮,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取得了真正有價值的卓越成就。”[10]P256這正是評論家所說的石黑一雄“每部小說結尾處,主人公那種略帶奇怪的自我滿足的時刻”[6]P25。說其“奇怪”是因為,一方面小說主人公內心充滿了沖突和焦慮,另一方面,作為讀者卻能發現隱含作者加在主人公身上的那種善意的反諷。主人公小野認同的范圍,逐漸從個人、職業、社會擴展至國族層面。通過回憶逐漸找回自己的職業尊嚴,建構起自己的日本國族身份認同,這才是小野在小說結尾處體驗到一種“略帶奇怪的自我滿足”的真正原因。
戰后美國占領下的日本,新舊、東西文化相互沖突,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期。《浮世畫家》主人公小野面對時移世易的日本,為了抵制社會轉型帶來的身份焦慮,選擇退回到原初性的日本身份認同,通過回溯戰前的職業成就與社會地位重建了自己的國族身份認同。透過“影子人物”黑田、松田、平山小子等的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認同,小野逐漸追回了自己與職業身份認同相互交織的日本身份認同。現實當中小野替松田的辯白,也成了他為自己錯誤往事的辯護,顯示了他對戰前日本價值觀的認同。石黑一雄通過將主人公置于戰前日本的歷史背景下,對小野日本身份認同建構的過程進行細致講述,對愛國主義的正反兩面做了全面考察,給全球化時代讀者以深刻的啟示:溫和的愛國主義國族身份認同理應得到大力提倡,但極端的愛國主義,如民族中心主義和軍國主義則需要極力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