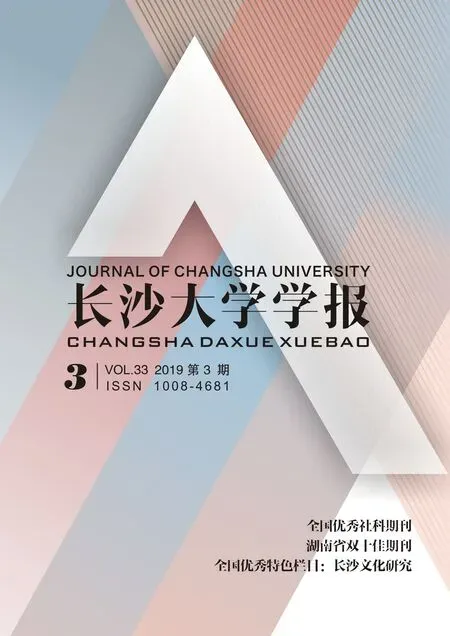名實之爭:論中國古代童話的自發性
范 麗
(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湖南 長沙 410016)
中國古代雖沒有童話之名,卻有童話之實。在中國古代存在眾多的童話作品。不過,事實上,要從眾多古代文學作品中無一遺漏地、輕松地將童話作品辨別、挑揀出來,卻非易事。而且,以前我國學術界一直存在著中國古代有無童話之爭,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中國古代童話具有自發性的特點,中國古代是童話的自發時代。因此,本文在試著說明中國古代存在大量童話的基礎上,進一步探析中國古代童話的自發性。
一 童話及童話的特征
何謂童話?在探析古代童話的自發性之前,我們需要對童話的概念有個清晰的認識。早期學者對童話的認識還比較籠統。比如孫毓修創辦《童話》刊物時就認為童話是除教科書外的兒童讀物,主要供兒童課外閱讀,內容包括文學讀物、知識讀物、歷史讀物、科學讀物等諸多內容。五四時期,周作人認為“童話最簡明的界說是‘原始社會的文學’”,并將童話分為“純正童話”(源于傳說,分為根據想象來解釋自然和解釋人事為主的兩種形式)和“游戲童話”(非源于童話而具有娛樂功用的,分為動物談、笑話和復迭故事三類)。
這些對童話的認識都不夠清晰,比較籠統。而事實上,時至今日,對童話的看法依然既具有不清晰性,又具有確定性。不清晰性表現在不同的書、不同的學者專家對童話的概念有不同的表述和界定。比如:
在《辭海》中,“童話”一詞是被這樣定義的:
“兒童文學的一種。通過豐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張來塑造藝術形象,反映生活,增進兒童思想性格的成長。一般故事情節神奇曲折,內容和表現形式淺顯生動,對自然物的描寫常用擬人化手法,能適應兒童的接受能力。”[1]
在《現代漢語詞典》中,對“童話”一詞是這樣解釋的:
“兒童文學的一種體裁,通過豐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張來編寫的適合于兒童欣賞的故事。”[2]
蔣風在其著作《兒童文學概論》中說:
“童話是兒童文學中的一種重要的樣式,也是文學中的一種特殊的樣式。它是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上,用符合兒童的想象力的奇特的情節編織成的一種富于幻想色彩的故事。”[3]
而韋葦在《韋葦與兒童文學》一書中,對童話作了如下一系列界定:
“童話是以口頭形式和書面形式存在的荒誕性與真實性和諧統一的奇妙故事,是特別容易被兒童接受的,具有歷史和人類共享性的文學樣式之一。
童話是以‘幻象’為一岸,以‘真實’為另一岸,期間流淌著對孩子充滿誘惑力的奇妙故事。
童話是一種以幻想為特征的荒誕故事來引起兒童共鳴的藝術假定。
童話是符合兒童想象方式的,富于幻想色彩的奇妙故事。
童話是以幻想滋養人類精神的故事家園。
童話是被故事邏輯所規范的童夢世界。”[4]
由吳其南主編的《兒童文學》一書,對“童話”的界定為:
“童話是一種以非生活本身形式塑造藝術形象并適合少年兒童閱讀的文學作品,其主要特點是文學性、虛擬性、兒童性。”[5]
黃云生在其主編的《兒童文學教程》一書中則指出:
“童話,是一種古老的文學樣式,也是兒童文學最基本最重要的體裁之一,它是具有濃厚幻想色彩的虛構故事。”[6]
陳蒲清在其著作《中國古代童話小史》中給童話的定義是:
“童話,是一種適合兒童心理特點的幻想性強的故事。這個定義揭示了童話有三個特性:一是故事性,二是幻想性,三是適合兒童心理特點。”[7]
這些對童話的解釋和界定已經有很多了,但還不是全部,這足以說明童話這一概念的不清晰。有些概念一開始就將童話劃定為兒童文學的一種體裁。這種概念不能說是錯,卻是面向現代童話的,是在有了兒童文學這一概念和學科劃分后,對兒童本位有著清醒認識后才有的概念。因此,這樣劃定童話,童話這個概念就只能面向現代童話了。也因為在童話的概念上存在著這些不清晰性,從而也導致很多人無法從定義下手,去尋找中國古代童話,從而得出中國古代并無童話的結論。
當然,這些對童話的解釋和界定,相對于孫毓修、周作人等早期學者對童話概念的模糊認定又是很清晰的,而且在不斷接近本真了。事實上,透過這些不同的表述方式,我們可以看到眾多定義中清晰的內涵,那就是童話概念中最實質性的東西,通過這些實質性的東西,我們完全可以很好地去界定、尋找、欣賞和評判古今童話。那么,什么又是童話最實質性的東西呢。童話是要以兒童為受眾的故事,而且這種故事是不同于現實生活中真實發生的故事。從這一點就可以確定童話必須是能易于被兒童接受的,適合兒童的、具有幻想性的故事。這就確定了童話需要具備的三個實質性的特點:故事性、幻想性和適合兒童心理性。這樣來看,前面所提到的諸多定義中,大都切中了童話的這三個實質性的特點。不過有些表述比較詩意,比如韋葦教授的;有些表述比較繁復細致,如《辭海》;有些定義則比較通俗、簡單,比如陳蒲清教授的。
二 中國古代的童話形式
中國古代有沒有童話?答案是肯定的。雖說中國古代沒有童話這一說,但童話卻實實在在地存在著,只不過這些童話在當時并不以童話的名目出現,而是混雜在各種民間故事、傳奇、志怪、志人小說當中。像《搜神記》《搜神后記》《異苑》《列異傳》《神仙傳》《齊諧記》《續齊諧記》《幽明錄》《酉陽雜俎》《夷堅志》《聊齋志異》等這些書籍中,就有很多童話。陳蒲清教授早在1993年出版的《歷代童話精選》一書中,就從中國古代的62種典籍中選出了120篇優秀童話。這些童話都具備童話的三大實質性特點,它們本質上就是中國古代的童話。以《葉限》為例,它其實就是中國版的《灰姑娘》故事。
《灰姑娘》先由貝洛收錄進《貝洛童話》,后格林兄弟又將它收入《格林童話》中。它是一篇家喻戶曉,經久不衰的經典童話。而事實上,早在我國古代的秦漢之前,就有一個與之相似的童話在民間廣為流傳,到唐朝的時候,段成式把這篇童話收錄進了《酉陽雜俎》一書中,它就是《葉限》:
南人相傳,秦漢前有洞主吳氏,土人呼為“吳洞”。娶兩妻,一妻卒,有女名葉限,少慧,善淘金,父愛之。末歲,父卒,為后母所苦,常令樵險汲深。時嘗得一鱗,二寸余,赪鰭金目,遂潛養于盆水。日日長,易數器,大不能受,乃投于后池中。女所得余食,輒沉以食之。女至池,魚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復出。
其母知之,每伺之,魚未嘗見也。因詐女曰:“爾無勞乎?吾為爾新其襦。”乃易其敝衣,后令汲于他泉,計里數百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行向池呼魚,魚即出首,因斫殺之。魚已長丈余,膳其肉,味倍常魚,藏其骨于郁棲之下。逾日,女至向池,不復見魚矣,乃哭于野。忽有人發粗衣,自天而降,慰女曰:“爾無哭,爾母殺爾魚矣!骨在糞下。爾歸,可取魚骨藏于室。所須第祈之,當隨爾也。”女用其言,金璣玉食,隨欲而具。
及洞節,母往,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行遠,亦往,衣翠紡上衣,躡金履。母所生女認之,謂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覺,遽反,遂遺一只履,為洞人所得。母歸,但見女抱庭樹眠,亦不之慮。
其洞鄰海島,島中有國名陀汗,兵強,王數十島,水界數千里。洞人遂貨其履于陀汗國。國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竟無一稱者。其輕如毛,履石無聲。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錮而拷掠之,竟不知所從來。乃以履棄之于道旁,即遍歷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葉限,令履之而信。葉限固以翠紡,躡履而進,色若天人也。始具事于王,載魚骨,與葉限俱還國。其母及女,為飛石擊死。洞人哀之,埋于石坑,命曰“懊女冢”。洞人以為媒祀,求女必應。陀汗王至國,以葉限為上婦。
一年,王貪求,祈于魚骨,寶玉無限。逾年,不復應。王乃葬魚骨于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為際。至征卒叛時,將發以贍軍。一夕,為海潮所淪。
成式舊家人李士元所說。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記得南中怪事。
這篇《葉限》故事性很強,想象奇特豐富,在主題、人物、情節安排,甚至細節處理和最后的結局等方面,都與《灰姑娘》相類似,況且,它最早記錄在我國唐代的《酉陽雜俎》一書中,比最早記錄在《貝洛童話》中的《灰姑娘》早了八百多年。從表1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二者的異同。

表1 《灰姑娘》與《葉限》比較
如果我們能承認《灰姑娘》是一篇不折不扣的經典童話,那《葉限》肯定也是。不只有《灰姑娘》和《葉限》相類似,清代黃之雋根據民間流傳的故事而記錄的《虎媼傳》也與《小紅帽》這個童話故事非常類似,是典型的“獸外婆”型童話故事。事實上,在中國古代還存在眾多膾炙人口的童話故事,比如《白水素女》《陽羨書生》《李寄斬蛇》《千日酒》《扶余王》等,它們與《灰姑娘》相比,與歐洲的其他童話相比,毫不遜色。只是在我們古代,沒有人把這些童話單獨列出來,進行系統地研究和整理,也沒把它們叫作童話罷了,這也導致了一些人誤認為中國古代沒有童話。
也許有人說:“中國古代童話缺乏兒童本位觀念,算不得是真正的童話。”但正如王泉根在《中國兒童文學現象研究》一書中所說:“從世界文學史的范圍看,真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只是在近代社會里才誕生的。”[8]西方也是在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之后,才有了兒童本位觀念的童話。《灰姑娘》這樣的經典童話也是在有兒童本位觀念之前就出現了的。所以,我們不能因為沒有兒童本位觀念,就否認《葉限》是童話,更不能因此就否定中國古代有童話作品。
三 中國古代童話的自發性
中國古代的童話還處在童話的初級階段,是完全自發的,它與完全自覺的現當代童話有著明顯的差異。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沒有專為兒童創作的、以兒童為本位的作家作品
從目前我們搜集到的古代童話作品來看,大都混雜在一些民間文學作品中,以及志怪、志人小說和傳奇故事中。這些民間文學作品、志怪、志人小說和傳奇故事等,它們都是專屬于成人文學領域的,是提供給成人閱讀的作品,而不是專門為兒童創作的。因而作者在創作這些古代童話作品時,也不可能考慮到兒童的需求和接受心理,做到以兒童為本位,專門為兒童去創作這些作品。但因為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有意無意地滲入了一些適合兒童心理特點、易于被兒童接受和喜歡的因素,使這些作品具備了童話的特點,成了兒童喜歡的童話作品。
不過,在前面已提到,沒有兒童本位觀,這并不是中國古代童話的專利,事實上,歐洲也是在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之后,才有兒童本位觀的。但正如不能因為沒有兒童本位觀,就否認歐洲古代沒有童話一樣,我們也不能否認中國古代沒有童話。
(二)中國古代沒有專門為兒童創作童話的作家
在我國漫長的古代文學長河中,一個個名垂千古、為人稱道的大作家,成就了先秦散文、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的輝煌。但是,眾多的作家當中,我們卻找不到一個專門為兒童創作童話的作家。
從古代作家的創作動機來看,中國古代的文人進行創作,無外乎以下幾點動機:第一,抒情言志,表達自己的內心意愿和情感,為自己立言等。第二,給領導階層進言、獻策,并給自己謀求仕進的機會,或為統治者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或對當局進行諷刺,表達自己的不滿和失望。第三,懷才不遇,轉而移情山水,寄寓鬼神等。總之,古代作家們進行創作,都是從自身出發,從成人的角度和目的需求去進行創作,而不是從照顧孩子的童心出發,去專門為孩子們寫作的。偶爾有家訓、家書之類的作品出現,也是本著教育后代、培養封建接班人和光耀門楣的想法和目的去寫作的。帶著這樣的目的和想法所創作的家書、家訓自然不可能成為童話。雖說偶爾有些作家從成人的角度和目的出發,寫出了孩子們喜愛的童話,但那都是不自覺創作的。而且這些童話,也基本上只是作家眾多作品中的一兩篇而已。所以,在中國古代,是沒有專門為兒童創作童話作品的作家的。
(三)沒有專門針對童話創作和批評的理論著作
中國古代有眾多的文學批評理論及著作,在郭紹虞的《中國歷代文論選》中選入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論文(含論詩詩)就有55種,其中先秦5種,兩漢4種,魏晉南北朝5種,唐8種,宋10種,金1種,元2種,明9種,清11種。比如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鐘嶸的《詩品》、劉勰的《文心雕龍》、嚴羽的《滄浪詩話》、葉燮的《原詩》、劉熙載的《藝概》……這些文學批評理論著作對中國古代出現的各種詩、文、賦等文學體裁及各種文學現象以及文學批評本身都有批評。然而,相比之下,中國古代的童話理論批評卻久久未能真正地生長發育起來。雖歷史上有過關于童謠來源的“熒惑星說”,有李贄的關于創作的“童心說”,但這些都不是從兒童的角度出發去進行思考和批評的,更不是針對童話創作去進行批評的。在我國古代,找不到專門針對童話創作和批評的理論著作。
(四)作品的呈現形式不利于兒童閱讀
文言文是我國古代特有的寫作方式,它作為古代文學流傳的主導方式,也就決定了那些接受教育很少,理解能力和知識水平有限的兒童群體是不可能讀懂或完全讀懂那些文言作品的了。雖然古代也有一些“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作品,但相對于兒童那有限的知識水平和欣賞層次,這樣的作品也大都只能束之高閣,拱手讓給成人去品味了。事實上,在我國古代,在漫長的封建社會,絕大部分兒童是文盲,他們根本無法接受學校教育和基本的文字教育,這樣,他們根本不可能看懂那些文言文作品了。因而這些作品也沒法廣泛地被兒童接受并在兒童群體中大量流傳。聽成人講故事是兒童知曉并接受它們的主要方式。夜間,圍爐夜坐或在星空下納涼,或大人忙活的間隙,聽大人“講古”是兒童接受這些作品教育的最常見的場景。古書中也有不少有關這種場景的記載。這種傳授方式一方面受限于大人所知曉的故事的多寡,同時也受制于他們的說話水平和思想觀念。因而能傳授的故事是相當有限的,而兒童能從中聽到的真正的童話故事就更不多了。
(五)沒有讓作家自覺創作童話的時代土壤
我國古代,處于漫長的封建社會,在封建社會里,封建倫理教育是建立在忠孝仁義的基礎上的,是必須絕對服從“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綱常倫理的。這種封建教育,一方面是父輩的無上權威,以致“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另一方面,這種教育也絕不可能以理解、尊重兒童的心理特點、精神個性和獨立人格為出發點,恰恰相反,是以損壞兒童的獨立人格為代價的。在“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桎梏下,兒童是只可能處在被漠視、被支配、被要求絕對服從權威的地位的。而對他們的教育,更是把他們當作“小大人”來看,用成人的方法和知識來對他們進行灌輸,從而培養出他們心目中所期待的“順民或忠臣孝子”。在這種封建教育大背景下,兒童的精神特點和獨立人格是完全不被尊重和理解更談不上重視的。當然,在這種封建土壤中,也不可能有作家作品是在以兒童為本位的前提下去專為兒童創作的。這種封建的時代土壤,一方面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童話自發性的一個特征和表現,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它是導致中國古代童話一直處于自發階段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古代童話的這些自發性特征,也導致古代童話中夾雜著一些不利于兒童閱讀的因素,比如大多數童話故事中的主人公是讓孩子感到比較害怕的精怪和鬼魅,一些故事情節也比較血腥、恐怖,在一些故事中還宣揚了因果報應、成仙得道、門第尊卑觀念等眾多封建思想。這些都是創作者從成人的角度出發創作并受自身思想的局限性影響的結果。不過,雖說夾雜了這些不利于兒童閱讀的因素,整體來說,中國古代的童話,童話的特征還是比較明顯,根據童話的本質特征,我們去檢視、去整理那些古代文學作品,便能從各個時期的作品中挑出大量童話來。
總之,正因為中國古代童話的創作有以上諸多自發性特點,因而可以斷定中國古代處于童話創作的初級階段,童話的自發性特征相當明顯。也正因為中國古代童話具有這么明顯的自發性特征,從而導致眾多童話作品沒有得到流傳和好好保存。這些古代童話與現當代處于自覺時代的童話創作有著明顯的區別,因而在很長時間內,現當代的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沒有童話,當然也就很少有當代學者對中國古代童話去進行研究和評判了。
事實上,中國古代的童話,猶如一座尚未被完全發現并開發利用的童話寶庫,它期待著我們去關注它、研究它、開發它、利用它。我國當代早期的童話作家,有過從我國古代童話中吸取營養的經驗,像張天翼的《寶葫蘆的秘密》、葛翠琳的《野葡萄》、洪汛濤的《神筆馬良》都是脫胎于中國古代童話的優秀之作。而從2003年底開始兒童文學創作的湯湯,則以一系列帶有濃郁古代童話氣息的鬼童話,讓兒童文學界驚艷。還有兒童文學作家湯素蘭,她的新作《南村傳奇》更是融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童話故事于一爐,通過舍身石、少年和蟒蛇、狐貍女婿及花神丁婆婆的美麗幻想故事,描繪了一個桃花源式的美好家園。相信,在這些作品的帶動下,在不斷發現并挖掘中國古代童話寶庫的形勢下,這樣充分從中國古代童話甚至整個古典文學的寶庫中吸取營養的上乘之作,將會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