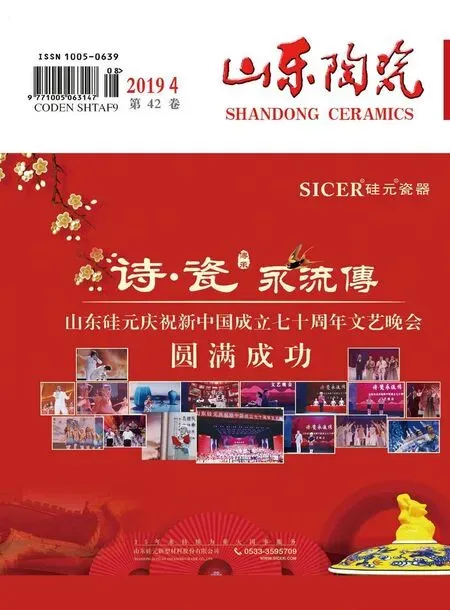瓷路之歌
2019-02-16 16:42:13高云華
山東陶瓷 2019年4期
高云華
有一片陶,薄如蟬翼。有一種瓷,潤如青玉。有一抹白與藍,猶如星光美鉆般夢幻。
后李的陶釜,龍山的陶鬶,北朝的青瓷蓮花尊,唐宋的金星雨點釉,泥土與水火淬煉出的陶音瓷韻,聲聲不絕,在世人驚艷的目光里曼舞輕揚。
還記得四千年前齊魯史冊上的優美歌謠嗎?“黑如漆、明如鏡、薄如紙”
還記得淄博陶瓷人百年來譜寫的華麗樂章嗎?“青瓷如玉,彩釉生香”
哦,還有一幅倍感親切的畫面,“牛拉碾、驢打場、三間半草房”,那是祖祖輩輩的制瓷景象
一條北方的陶瓷之路,打家門前經過,沿淄水博山一路向西,隨南來的花瓣雨飄洋而去。
從周村去張掖、雁門關,從博山過運河、波斯灣,每一輛顛簸的小車上,都有陶瓷碰擊出的鼓點,每一艘裝滿中國物產的大船里,都有陶瓷壓艙 鼓蕩風帆
那是一條多么崎嶇的路,
砂巖赤裸,長山嵯峨。
如果不是150年前一個異鄉人的到來,也許不會有人把它和絲綢之路緊連。
那一天的風格外大,他的藍眼睛不得不瞇起,怕被迎面的塵土染黃,第三次來華遠征考察,李希霍芬從木輪車上跌下,匍匐在孝婦河谷,一片古老瓷都的沃土上。
眼前的煙火景象讓他驚訝,一車一車的琉璃,一車一車的陶瓷,川流不息,成排成行,一條繁忙的陶瓷之路,隱沒在蒼茫的山梁。
它隱藏在樵嶺的脊背上,被野花簇擁著。
它隱藏在淄水的臂彎里,被清流滋養著。
齊魯大地的圓月,撫慰著它的孤獨。
博山漢子吼出的鷓鴣調,比一條條陶瓷之路更久遠、更綿長。
總有古老的歌要開花結果,總有一顆心要向天空眺望。
一輩輩陶瓷人,傳承、奉獻、創新、摸索,一件件國之器,登堂、入室、流芳、傳揚。
今日古老瓷都的新詩行,在命運一體的藍圖里更加豐滿。
今日陶瓷人探索的足音,在一帶一路的遼闊里鏗鏘回響。
而此刻,我心中的歌啊,正在一抹藍白的釉色里,靜靜地流淌,流向一首詩和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