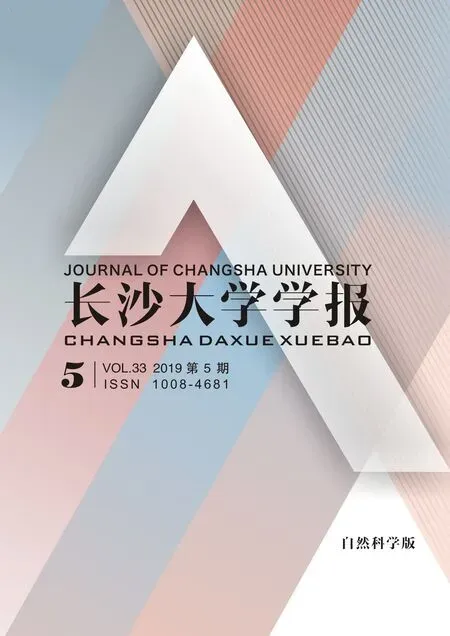城鎮化過程中的不平等效應分析與社會融合問題研究
寧 鴻
(大連財經學院基礎教育學院,遼寧 大連 116600)
現階段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已經處于最后的收尾階段,而截止到2020年中國城鎮化60%的發展目標也會提前實現.但在我國整體社會結構穩步調整的同時,還應看到中國新型城鎮化水平較低、質量不高,且城鎮化產生一系列城鄉不平等、農業戶籍人口難以融入城市社會的問題.這種過于傳統與粗放式的城鎮化發展,使得農業人口群體、城市群體之間存在天然間隔,在經濟收入、社會保障、身份與心理認同等方面,農業戶籍人口仍然面臨著生存困境與身份轉化障礙.本文針對農業人口轉移所出現的“半城市化”情況,分析城鎮化發展進程中“人口遷移”的趨勢,從而給出農業群體融入城市社會的解決方案.
1 城鎮化過程中農業戶籍人口向城市轉移的現狀分析
2015年我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通知與印發有關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綜合試點方案,將江蘇、安徽、寧波等城市列為城鎮化試點.這一城鎮化發展舉措的實施,對城市中大量的農業轉移人口進行合理分配,標志著多元化、可持續化、更高質量城鎮化建設的開始.
國內學者在有關農業戶籍人口進入城市社會的融合分析中,也有著不同的思維角度與見解.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培林針對農業人口進城務工的經濟、心理等狀態,對不同年齡段、不同受教育程度農業人口的社會融入狀況進行分析.在多種有關城市新移民的研究中,大多數學者往往集中于農業戶籍人口的整體探究,并未對不同農業人口、不同層級要素進行分類研究,也沒有將農業戶籍人口、城市人口放在同一緯度進行比較.在農業戶籍人口向城市轉移的現狀分析中,本文主要從農業人口進城后的就業、經濟狀況、居住與生活條件、社會交往等方面,探討城鄉二元對立環境下農業戶籍人口在城市社會中的生存現狀.
首先,農業戶籍人口在城市社會中的地位低于城市人口,特別是在購物商場、公共汽車或居民家庭等公共場所,農業人口會感受到來自城市人語言或行為上的輕視.其次,從農業戶籍人口就業的工資待遇來看,城市新遷入的農業人口,其在收入方面明顯低于城市人口.農村人口在進入城鎮勞動力市場后,會與城鎮勞動力產生競爭關系,在低端勞動力方面農業人口的價格優勢更明顯,其會通過降低工資來增強其本身的勞動競爭力,這加劇了城鎮、農業人口的收入不平等效應.另一方面,城市企業在招聘員工過程中,會優先為城市人口提供相應就業機會,農村流動人口只能從事技術含量低、勞動密集的工作,且并沒有完善的養老保險、工傷保險與社會保險等保障.同時由于農業戶籍人口的戶籍限制,其很難分享到城鎮化發展所帶來的紅利,因此農業遷入人口、城市人口之間的不平等待遇一直存在,并造成農業戶籍人口在城市社會中的融入困難.
根據《2018年農業進城務工人口監測調查報告》,2018年我國農業進城務工人口總量為28836萬人,比上年增加184萬人(增長率0.6%).在農業人口進城務工方式的分類中,在本地區城市就業的農業戶籍人口達11570萬人,比上年增加103萬人(增長率0.9%);在外地就業的農業戶籍人口17266萬人,比上年增加81萬人(增長率0.5%).之后從性別比例方面分析,全部農業進城務工人口中男性占65.2%、女性占34.8%,女性占比提升0.4個百分點.而從農業人口進城務工的年齡層級來看,其中40歲及以下青壯年占比52.1%、50歲以上中老年占比22.4%,平均年齡為40.2歲,比上年提高0.5歲.最后,在全部進城務工的農業人口中,小學文化程度占15.5%,初中文化程度占55.8%,高中文化程度占16.6%,大專及以上占10.9%.而2018年農業部最新數據表明,我國農業人口外出務工的平均月收入為3721元,比上年增加236元(增長率6.8%)[1].
現階段農業人口的居住與生活條件,基本維持在溫飽與勉強生存的境地.通常農業外出務工人口都會選擇城鄉結合部,作為外出工作的居住地,或者住在工地的大通鋪.這些地區的房租價格、交通成本較低,但所具有的居住條件也較差.而農業戶籍人口的飲食生活方面,大多數農業務工人口都會挑選便宜飯菜,用以維持日常的基本生活.最后,農業外出務工人口所具有的社會交往,主要依靠存在地緣或血緣的親屬,作為自身在城市謀生的資本.除此之外,大多數農業務工人口,并不能在城市中建立起可靠的關系網,這也是農業人口存在身份認同障礙的主要原因.
2 城鎮化背景下農業遷入人口不平等效應與社會融合問題的影響要素
自我國推行改革開放的城市化發展方向以來,城鎮化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推進:舊城改造、城鄉結合部開發、新城與商務區建設、制造與密集型產業轉移.在運用以上幾種方式來施行城鎮化建設的情況下,會促使農業戶籍人口向城市地區轉移.盡管當前國內學者在研究城市不平等效應時,并沒有與農業戶籍人口進行準確關聯,但從相關數據可以發現:農業勞動力對中國城鎮化建設的作用,遠遠大于城市人口對城鎮化建設的推動力.當下農業遷入人口不平等效應與社會融合問題的影響要素,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內容.
第一,城市對農業遷入人口的社會接納度,是決定農業務工人口是否能融入社會的重要因素.當下雖然我國政府頒布《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綜合試點方案》,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擔機制,以及對現行城鎮行政管理機制進行改革創新,以提供農業群體工作與落戶的便民條件.但在城市就業、城市市民資格的辦理方面,大多數企事業單位對城市人口、農業遷入人口,仍然采用區別對待的方式進行處理.相對而言,農業戶籍人口所從事的工作,主要為收入低、危險系數較高的行業.
第二,農業遷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較低,也是不平等效應與社會融合問題產生的原因之一.根據近年來《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的數據得出,新生代農民工小學文化程度占15.5%,初中文化程度占55.8%,高中文化程度占16.6%,大專及以上占10.9%[2].雖然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農民工的數量正在逐漸增加,但大多數農業務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仍舊較低,而且大部分農業人口未接受任何職業技能培訓.而缺乏知識與職業技能的謀生手段,以及城市企業所需要的高學歷,使得農民工在就業、社會交流過程中受到極大限制,由此會加深農業人口對不平等社會待遇的認知,甚至會造成農民工回流農村的現象.
第三,農業務工人口自身行為習慣、身份心理的固化,也會加深農業人口對不平等社會現狀的認知,影響其在城市社會中的融入狀況.根據相關調查表明,我國農民工在進入城市生活后,其本身能夠清楚感受到城市群體對其所存在的歧視或偏見.而這一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源于城市人口、農業戶籍人口之間的天然隔離;而另一方面,則由于農業務工群體自身的行為習慣,存在較多不檢點、不衛生之處,以及農業務工人員本身身份與心理的固化.大多數農業務工群體在工作業余,主要以電子游戲、棋牌游戲作為社會交往的手段,這與城市居民多樣化的業余生活存在較大差異.另外農業務工群體作為城市的外來者,其會主動將自身與城市進行分離,認為自身在城市中的主要價值為謀生,而最終還要回到農村.這種過于固化、絕對化的身份與心理認同,會降低農業人口與城市人口之間的交流意愿,從而導致農業戶籍人口在城市社會、城市生活中的不平等效應與融入問題[3].
最后,農業人口在遷入城市過程中缺乏社會保障,也是影響其不平等認知、城市社會融入的主要因素.從農業務工人口的公共權益來看,大多數企業或雇主并沒有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協議,或者在勞動協議中存在損害農民工利益的條款.而另一方面,企業或雇主在薪資、工傷等方面的商議中,不能與農業務工群體達成合理協定,常常會出現拖欠工資、工傷無人負責的狀況.此外,農業務工人員在子女入學、房屋購置及其他社會保障方面,也與城市人口存在較大差距.綜上所述,在社會城鎮化發展的過程中,農業戶籍人口由于自身發展狀況,或城市外在條件、國家政策的限制,其很難與城市社會進行融合,也無法消除農業戶籍人口、城市人口之間存在的不平等效應.
3 城鎮化過程中農業遷入人口不平等效應與社會融合問題的解決策略
在我國城鎮化迅速發展的形勢下,需要從多種社會制度、政府政策、就業崗位與培訓、社會保障、社會關系網絡等方面著手,進行農業人口勞動力就業、轉移就業的環境建構,以幫助農業人口群體消除不平等的心理認知,并推動農業戶籍人口融入到城市社會的生活中.這就要在城鎮化的建設過程中,以農業轉移人口作為社會資源、社會發展紅利分配的主體,減少城鄉二元對立,并逐步放寬戶籍制度、教育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的限制,才能保證農業遷入人口在城鎮化建設中的合理性流動.
3.1 加強與完善農業遷入人口政策、社會保障制度的制定
農業人口在進入城市就業的過程中,由于城市中缺乏農業務工人口發展的保障制度,這使得農業人口、城市人口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生存矛盾.因此政府針對農業務工人口生存的特殊情況,提出有關戶籍制度的利益改革,剝離出附加在人口戶籍上的教育、就業等優惠條件.而在農業戶籍人口就業制度的完善方面,我國也已經構建起城鄉統籌的一體化就業模式,各個省市有著不同的農民工就業優惠政策.特別是在我國落戶政策實施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開始設置合理的人員落戶門檻,對符合要求的農業人口辦理落戶手續,以使其獲得應有的市民待遇[4].之后在農業務工人口用人制度、勞動協議等方面,不同省市根據本地區的勞動就業狀況,對存在的拖欠工資、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等問題進行解決,從而消除企事業單位中的勞動歧視.由于農業遷入人口的數目較為龐大,只有逐步解決存在的政治與公民權利問題,才能使農業人口真正融入到城市社會中.
3.2 構建農業遷入人口的轉移就業協作機制以保障就業
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推動著國內各個行業產業結構的改革與升級.而當前農業進城務工人口的勞動能力較強,缺乏工業化生產的職業技能,這是導致農業遷入人口收入低的主要原因.在我國城鎮化發展的進程中,只有從轉移就業、職業技能培訓兩方面著手,才能改變農業人口的不平等認知與社會融合問題.在農民工轉移就業方面,我國各個省市已經形成廣泛的聯合.河北、甘肅、青海、河南、山東、黑龍江等省市,已經構建起完善的勞動力輸入輸出合作機制,并通過網絡對農業人口進行統籌管理,實現農業人口在城市建設中的合理有序流動[5].
3.3 大力開展農業遷入人口的教育與職業技能培訓
農業遷入人口受教育程度低、職業技能缺乏等因素,是其在城市社會中融入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在農業人口的教育與職業技能培訓方面,應根據城市建設、行業發展的具體需要,制定合理的教育與技能培訓方案,以滿足勞動力市場與經濟發展的需求.現階段我國政府正與互聯網信息企業進行聯合,試圖通過網絡構建起農業人口教育培訓的服務基地,“圓夢行動”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農民工教育培訓方式.“圓夢行動”立足于當下農業務工人員的發展現實,通過網絡進行各行業的資源整合與共享,并具有完善的政府調控、市場調節的管理機制,以保障農業遷入人口的職業技能培養[6].通過實施符合農業遷入人口的教育與職業技能培訓方案,可以從根本上增加農業戶籍人口的就業機會,并盡可能保證農業務工人口在就業中的平等待遇,以幫助其融入到城市社會的生存中.
3.4 施行符合農業遷入人口發展的社會關系與保障制度
城市生活的基本單位為社區或居民樓,農業遷入人口在進入城市就業時,也往往會選擇這些生活環境或工棚進行居住.這種城市人口、農業進城務工人口混合居住的模式,也增強雙方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在農業遷入人口的社會關系構建中,城市政府部門要針對流動人口的居住需求,推出配套的社區服務項目、人口管理措施等,以搭建符合農業戶籍人口需要的社會關系網絡.基層社區也應根據自身的人口密度,制定有利于農業遷入人口全面發展的方案,推動農業流動人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另一方面,城市相關部門應考慮到農業戶籍人口的經濟狀況,盡可能落實農業人口的戶籍落戶、子女入學、社會保險等制度,并在農業戶籍人口社會救助、創業就業等方面,對其給予多種政策性支持.
4 結語
在我國城鎮化不斷發展與演變的過程中,農村地區、城市地區之間的二元結構始終存在.這些進入到城市的農業人口,大多為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或個體商販,其在城市社會中的存在狀態為“半城市化”.雖然進入城市的農業戶籍人口,也作為城市一部分產生相應的社會價值,但在社會生存、身份認同、心理感知等方面,進城農民工與城市人口之間仍存在較大差距.因此在農業務工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的過程中,政府與社會中各機構應按照國家政策的規定,為農業戶籍人口提供就業創業、技能培訓、社會關系、社會保障等層面的幫助,以消除存在于農業戶籍人口、城市人口之間的不平等效應,使農業人口群體融入到城市社會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