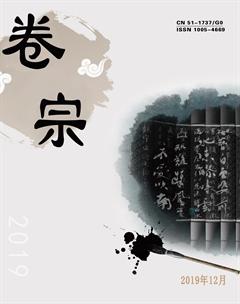侯氏長鏡緣起緣落
楊一葦
摘 要:長鏡頭在侯孝閑電影中有著獨特的運用,長期以來,自成一派,成為一種風格。當今,在國外大片沖擊國內市場的同時,經典好萊塢的敘事模式也劇烈地吸引著廣大年輕人的眼球。對與經典好萊塢風格截然不同的侯氏長鏡風格進行探析,并且進一步從創作環境和美學追求兩方面對其形成原因進行分析。作為一種電影現象,沒有強大的票房號召力,也沒有超人氣的明星效應,“侯氏長鏡”在電影歷史的長河中又耀眼醒目。
關鍵詞:侯孝閑;長鏡頭;臺灣新電影;情緒;東方人文
1 風格印象
靜觀長鏡頭作為侯孝賢鏡語結構中最突出的特點,多采用景深構圖來擴大時空容量。畫面構圖是開放性的,利用復雜的場面調度來表明畫外空間的存在,打破畫框。如《悲情城市》中第83場賭場過道搏殺的一場戲,比利和金泉從屋里出來,和妾兄發生口角后撕打起來,情急之下,比利朝妾兄開了槍,大哥聽到槍聲沖了進來,痛打比利,一時大亂,阿山、老表等人紛紛從各自房間沖出,又是一場混戰,妾兄、金泉、大哥流血倒地,人們在遠處默默看著。在這里,侯孝閑觀照的不是個體生命在這一時刻的存亡,而是這個社會群體的生命流程以及這一生命流程中顯示的對生命的歷史性內省。同時,侯孝賢還喜歡在長鏡頭的前景安排事物,借此拉開與主要被攝對象的距離,造成間離效果,不做主觀的介入,而是像個旁觀者一樣觀察著整個景象。如《悲情城市》中,大哥為老父籌備生日大壽,老父端坐在中全景中心位置,大哥入畫請安,兒媳進畫請示,女傭們從前或從旁入畫出畫地忙于備壽,雖然人物進出離鏡頭很近,但鏡頭與鏡頭內人物的活動始終有一種間離。這種風格再次突顯了侯孝閑長鏡頭中的人文關照,他總是以歷史的俯視角度,遠距離的觀照,鳥瞰世間萬事萬物,以一種寧靜致遠的態度敘事,仿佛再多的滿目創痍,鏡頭一轉便是青山綠水。
“沒有現在、過去、將來的清楚界限。你所看到的東西也許都是現在,但這個‘現在里包含了過去與未來,我們的觀念是把時空全部模糊掉了,因它的‘情緒而去轉換。侯孝閑的長鏡頭是為情緒服務,常常以轉場伴以時空大幅度跳躍,予大開大合中,抒發一種蒼涼的歷史詠嘆,給觀眾思緒的回味。感悟侯孝賢的電影空間就仿佛置身夢境,時空完全模糊了,視點也不清楚。例如在《戀戀風塵》中的閃回,各鏡之間空間彼此交錯,無垠流變——阿遠在軍中收到弟弟的來信,得知阿云已婚,畫面閃回為一組零散的鏡頭:1)仰拍家鄉天空下被電線纏繞的電線桿;2)家中外公與弟弟妹妹坐在家門口臺階上;3)阿遠的母親在阿云家門口勸慰生氣的阿云母親;4)阿云和郵差尷尬地站著。不知道一切是弟弟信中的描述還是阿遠的想象,亦或是現實的生活。空間的變化無法理清,只有淺淺的意緒穿梭在畫面。可謂,年輕不覺隱隱痛,戀戀風塵天知曉。這是侯孝閑長鏡頭鏡頭結構中時空節奏的設置,鏡頭內的時空被虛化了,但他有意重塑了一個非物質化的東方文化時空,抹平了歷史時空的深度,讓歷史僅僅是一個畫面,而畫面背后更多的卻是一份淡淡的揮之不去的心緒,一種詩畫交融的天人境界,一個藝術家有禮有節恬淡克制的觀照世界的方式。
侯孝賢在電影作品里恣意地讓長鏡頭作為主要的鏡頭方式,形成了超乎平常的侯氏長鏡頭風格。《戲夢人生》三個小時只有一百多個鏡頭。一路走來,我們看到的是輕濤拍岸,和風相送的海邊小屋,聽見阿清和朋友的對話,盡管難辨說話的是誰,但感受到的卻是無盡的寧靜和溫馨;看到的是老祖母在地鋪上悄然離世,四兄弟仿佛長達一個世紀的凝視。生命的凋謝如此突然卻又自然,風云散盡,憂愁卻留在了歲月里;看到的是《悲情城市》伴著風琴聲和小孩的歌聲,搖入的風琴前彈唱的靜子,搖入的靠在風琴邊凝視著靜子的寬榮,搖入的青山綠樹,搖入的犁田農人……侯孝賢的長鏡頭是東方的,它一笑一顰展現的是東方人文精神,神似中國的卷軸古畫:猶如卷軸徐徐展開,畫意一一流露的那分曼妙,所有的情緒在侯氏長鏡頭里也如此展現在觀眾眼前,由始至終,漸如佳境。在侯孝賢的長鏡頭里是對自然、生命深切體驗之后的熱愛、尊重、理解與寬容;是一種冷靜、莊嚴的全視點。這是東方超然物外的生命哲學,是歷盡人世滄桑后的頓悟。那些一鏡之間大幅度跳躍和被模糊的時空,通通化作侯氏長鏡中浴水而出的氣韻:歷史的距離感,寧靜內省的生命頓悟,大智若愚的審美氣度。
2 風格成因
侯孝閑的長鏡頭已經成為一種風格,中遠景的運用,定機位的拍攝,靜觀的,情緒的,這所有的風格特征全因為侯氏長鏡是東方的。在侯孝賢的作品中呈現的敘事觀念和影像風格都很大程度地體現了東方文化的內在精神,浸潤了東方傳統理論的氣質和詩意化的旨意。在他的長鏡頭中,總是以詩化的電影語言為自己的作品創造一種中國詩歌的意境:“靜”、“遠”、“空”。與其說他是一個敘事者,不如說他是一位抒情詩人。侯孝閑的長鏡頭是情緒的,是詩化的,在冥冥之中,侯孝賢的長鏡頭風格與東方傳統文化就有了一種契合。中國古典詩的方式,不以沖突,而以反映與參差對照;不以救贖化解,而是終生無止的綿綿詠嘆,沉思與默念。而侯氏長鏡正是淡化了故事情節,以詩意的布光,以及“氣韻剪輯法”為導演的情緒宣泄創建了一個個清幽淡遠的意境。而侯孝賢長鏡頭的詩意呈現的是另外一種恬淡的意境,注重人在自然環境中的和諧方式,更貼和中國古典詩歌的氣韻以及對情景交融的講究。《童年往事》中仰拍的在微風中搖動的樹木;《風柜來的人》中夕陽下,大海上在藍色沙灘跳舞的四少年。人與自然融合了,畫面以景抒情,以情描景。
在《悲情城市》中,大量的長鏡頭,侯孝賢更是讓詩意化的敘事和詩句的造型直接出現,以完成其對美學的追求。光影,聲效等電影語言通通成為導演的抒情手段,宛若詩詞歌賦里飄飄揚揚的柳絮,隨處可見,待到伸手欲捧時卻只是化作少女般羞澀的一簾幽夢。詩化的鏡頭語言好比一團一團的光暈,透過那些迷朦的色調,我們看到的是寬美帶林老師等人在文清處高談闊論,文清靜靜地坐在一旁,為眾人打開唱機。
侯孝賢的個性和氣質使他選擇詩并且是中國古典詩歌作為其長鏡頭風格營造的原動力,執著地追求“東方情調”。與西方的文學傳統不同,中國文學具有抒情傳統。侯孝賢正是用中國詩的意境把那些梢縱即逝的情緒留在鏡間。當別人稱他為一位抒情詩人時,他正站在某處,眼里永遠是那淡淡的回憶式的憂愁,時作時休,時吟時罷,平靜的用他的長鏡頭展開充滿著中國山水畫留白的無盡畫面。
用東方的方式把握東方的侯孝閑,我以為只有從最原始的東方傳統文化著手,才能最切實地分析侯孝閑的長鏡頭風格。侯氏長鏡風格是有技巧的,它物化情緒的技巧,復合敘事的技巧,心理張力的技巧;然而侯氏長鏡風格更是其來自有的,它透露出創作者的思維方式,是因緣際會的才情悟性,是欲罷不能的天性流露,是通過人力能達到的萬物萬化的胸襟境界和美學追求。因為有了這樣的追求,侯氏長鏡才是風格化的。從最初由于環境因素的不自覺創作,到風格的形成,再到自覺地對風格的延承,侯氏長鏡一番緣起緣落,終成正果。
參考文獻
[1]何冠平.20世紀的電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2]李.R.波布克.電影的元素.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4.
[3]吳念真,朱天文.戀戀風塵:劇本及一部電影的開始到完成[M].臺北:三三書坊,1987.
——以《山河故人》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