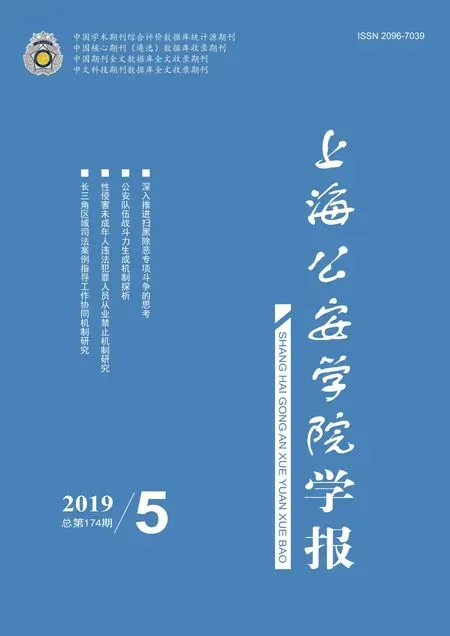防衛準備的認可:實踐探索與理論依據
劉嘉錚
(東北財經大學,遼寧 大連 116025)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1997年刑法對正當防衛制度進行了重大修改,這次修改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對正當防衛所保護的法益的范圍進行了擴張,明確規定除了保護人身權利以外,為了保護本人或他人的財產權利也可以進行正當防衛;第二,對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進行了松綁,明確規定防衛行為明顯超出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者,才應當承擔刑事責任,同時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第三,增加了特殊規定,明確規定對于正在進行行兇、殺人、強奸、搶劫、綁架等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殺傷不法侵害人的方式進行防衛,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者,不屬于防衛過當。
由此可見,我國1997年刑法對正當防衛制度進行重大修改的初衷是為了放寬正當防衛的成立條件,遏制部分司法機關動輒將原本屬于正當防衛的行為錯誤認定為防衛過當的趨勢,鼓勵我國公民積極行使防衛權利同不法侵害作斗爭,在公安司法機關無法及時救濟被侵害人權利的情況下對被侵害者的法益進行保護。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立法的這種修改并沒有得到良好的貫徹。1997年刑法頒布實施后,司法實務工作中動輒將正當防衛認定為防衛過當的現象仍然是主要趨勢,這種現象宛如一輛失靈的重型卡車,無論立法這個司機如何踩剎車,都阻止不了它向前沖撞的慣性,導致了刑法的明文規定與司法實務操作產生不一致,經過了1997年刑法修改后的正當防衛制度,除了極少數案件以外,并沒有完全發揮出其應當發揮的作用,逐漸淪為刑法中的“僵尸條款”。勞東燕教授甚至一針見血地指出:“具體就正當防衛的條款而言,它在我國實務中的適用情況,已經十足地表明,聲稱其為僵尸條款根本還是抬舉了它。嚴格說來,這個立法條款已然喪失作為法律規范的地位。”[1]
但是近來,這種令人憂心的現象出現了一絲轉機,為我國刑法扭轉實務工作中將正當防衛認定為防衛過當的錯誤傾向鑿開了一個突破口。這個轉機就是2019年轟動全國的河北淶源反殺案。在本案中,最重要最可喜的突破,就是河北省淶源縣司法機關并沒有將被侵害女生王某某一家人在自己家中預先進行的防衛準備認定為防衛過當,從整體上將被侵害女生一家人的行為認定為正當防衛。該案的正確處理為司法機關將防衛準備認定為正當防衛提供了強有力的現實依據。
二、突破口的出現:淶源反殺案的正確處理
(一)淶源反殺案的案情與處理結果
本案當事人王某某拒絕了其母親趙印芝的同事王磊的多次求愛后被王磊不斷騷擾和威脅,王磊給王某某發送了帶有死亡威脅的短信。王某某的家人被迫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予以防范,包括多次報警通過公安機關對王磊進行訓誡,借來兩條狗護院,在院中安裝了監控設備,在臥室里放置了鐵鍬、菜刀、木棍等,并讓王某某不定期更換臥室。
2018年7月11日23時許,王磊攜帶兩把水果刀、甩棍翻墻進入王某某家院中意圖實施犯罪時被發現,與王某某一家人發生激烈搏斗,在搏斗過程中王磊被王某某及其家人打翻在地,兩次試圖起身,王某某父母擔心其起身后繼續實施侵害,就連續先后用菜刀、木棍擊打王磊,造成王磊顱腦損傷合并失血性休克死亡。王新元、趙印芝和王某某也不同程度地受傷。
對于該案,淶源縣公安機關以王某某行為屬于正當防衛為由,對其終止偵查,解除取保候審;淶源縣人民檢察院依據《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認定王新元、趙印芝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決定對王新元、趙印芝不起訴。
(二)淶源縣人民檢察院對案件的處理所傳遞的信號
在本案中,王某某一家人的行為完全符合正當防衛的前四個成立條件(防衛起因、防衛意圖、防衛時間、防衛對象),唯一存有爭議的是王某某及其家人的事前進行了防衛準備的行為是否明顯超過必要限度。
根據我國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的規定,防衛人的行為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才構成防衛過當:其一,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其二,造成重大損害。因此,只發生了重大損害結果(造成不法侵害人重傷或死亡)但行為沒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或者行為雖然明顯超過必要限度但并沒有造成重大損害結果的都不屬于防衛過當。在本案中,雖然王某某及其家人的反擊行為最終造成了不法侵害人王磊被反擊致死這一重大損害,但是,應當認為盡管在事前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防衛準備,三人的行為并沒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結合本案案情可以發現,當事女生王某某一家人針對不法侵害人王磊的死亡威脅確實進行了一定的預先準備,包括借來兩只看家護院的狗,在房間里放置防身用的鐵鍬、木棍、菜刀,安裝監控設備,并且這些防衛準備在王某某一家人對抗不法侵害人王磊所實施的不法侵害(殺害、傷害)的過程中也都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王家人的事前防衛準備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做出的。本案中,不法侵害人王磊在向王某某求愛被拒絕后,實施了一系列讓王某某及其家人感到強烈不安和恐懼的行為,并且行為的危險性越來越大。王磊先是不斷糾纏王某某不讓其回家,然后攜帶管制刀具上門滋事,以自殺相威脅,隨后更是變本加厲,先后六次到王某某家中、學校等地對王某某及其家人不斷騷擾和威脅,王某某就讀的學校甚至專門制定了應急預案防范王磊。此后王磊又向王某某發送帶有死亡威脅的短信,并揚言要殺害王某某兄妹,最終攜帶刀具和棍棒沖入王某某家中實施殺人行為。而在王磊的犯意外化為實行行為的整個過程中,王某某一家人對不法侵害人王磊進行了最大程度的退讓。在王磊實施不法侵害之前,王家人一直采取的都是退避措施,先是拒絕王磊的見面要求,然后是采取了向公安機關報案這個最為理性的方式,甚至躲到了賓館和親戚家居住,在公安機關多次出警均對制止王磊的騷擾威脅行為無效以后,王家人才采取了更加進一步的防護措施:借狗護院,安裝監控,在屋子里放置防衛工具,讓王某某定期換臥室住。但是,王家人進行的這些防衛準備的作用是如果王磊真的像死亡威脅短信中所說的那樣,闖入王宅實施殺人行為時,王家人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知曉并手握一定的工具進行自我保護,不至于在身強力壯的王磊實施不法侵害時束手無策,并且王家人并沒有將王磊反擊致死的目的,做這些防衛準備僅僅是尋求一些心理安慰,讓一家人尤其是王某某的基本睡眠不受到太大的影響,保證其最基本的身體健康。與此同時,王某某一家人的防衛準備客觀上也并沒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借狗護院,在屋中放置防衛工具、安裝監控的行為僅僅是一系列被動的防衛準備,而不是主動的加害準備,既沒有采取極端防衛手段危害周邊不特定多數人的公共安全(如架設高壓電網),也不會起到積極加害不法侵害人王磊的作用。因此,王某某一家人雖然針對不法侵害進行了事前防衛準備,但是他們的行為并沒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
淶源縣人民檢察院也持同樣的觀點,并沒有將被侵害女生王家人的防衛準備行為認定為明顯超過防衛限度造成重大損害而構成防衛過當,而是直接依據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將一家人的行為認定為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淶源縣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在讓國民歡呼雀躍的同時,也傳遞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信息:針對不法侵害人事前發出的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威脅進行了防衛準備,并憑借這些防衛準備在不法侵害現實發生時進行了防衛,造成不法侵害人重傷或死亡的,同樣符合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的規定,不能將防衛準備行為認定為防衛過當。
三、正當防衛不排斥防衛準備的理論依據
淶源反殺案為將防衛準備認定為正當防衛打開了突破口,與此同時,在司法實務中將防衛準備認定為并沒有明顯超出必要限度,仍然成立正當防衛的理論依據同樣充分。
(一)防衛準備契合國民的規范意識
刑罰雖然由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制定通過并由具備專業知識的司法工作人員進行適用,但是本質上依然是國民規范意識的體現。司法機關在適用刑法處理案件的過程中對案件所做出的處理決定不能偏離國民對案件處理結果的合理期待,如果過分偏離國民規范意識,會導致國民減少甚至喪失對刑罰法規的應有作用的信心,動搖國民對于社會公平、正義的信念,正如前田雅英教授所言,“如果作為社會制度的‘法’,‘法理論’不匹配現在的‘國民的意識’,就不能發揮其作用”。[2]國民規范意識具有這樣的一種作用:它能夠適當調整司法工作人員在長期的辦案過程中所形成的思維定式,提升法院裁判的可接受性,將司法工作人員的專業優勢和國民思維相互結合,“通過國民的視角、感覺以及與法律人士的專業性之間的經常性交流,加深相互的理解,發揮各自所長”。[3]而正當防衛制度作為刑法中極其重要的制度,在落實的過程中同樣不能偏離國民規范意識,立法對正當防衛的規定和司法實務工作,對正當防衛規定的適用都應當符合國民規范意識對何種行為屬于正當防衛、何種行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構成防衛過當的正當的、合乎邏輯的期待。以淶源反殺案為例,在一般國民看來,任何具備完全行為能力的公民在受到明示的死亡威脅的情況下,都會進行一定的防衛準備,比如隨身攜帶防身工具。如果一個女生收到長期對自己進行騷擾威脅的人的“我要到你家里去殺你全家”的死亡威脅短信,那么該女生及其近親屬肯定會在不危害公共安全的前提之下(如不私自架設高壓電網)在家中做好必要的防衛準備,安裝監控,在家里放置棍棒等防身工具,以防止發出威脅的人真的到自己家中實施殺人行為時措手不及,這些都符合國民對完全行為能力人在面臨死亡威脅時會如何處理的合理預測,而并沒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也同樣不屬于事前防衛。因此,面對已經表露于外的殺人、行兇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威脅,防衛人或者被威脅者事前進行一定的防衛準備,然后在上述不法侵害真的發生時,借助這些防衛準備實施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只要防衛準備沒有危害公共安全,就仍然符合我國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的規定,沒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如果符合成立正當防衛的其他四個條件,就應當成立正當防衛,而不屬于防衛過當。而這里的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不能進行限制解釋,不能認為必須要現實地造成了重傷、死亡結果的才屬于“嚴重危及人身安全”,完全有可能造成其他結果甚至根本不會造成重傷死亡結果。正如車浩教授所言,“法條明確規定的,是嚴重危及人身安全,這里的危及人身安全,是一種不確定的狀態,可能是會造成重傷,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侵害”。[4]因此,當被威脅人受到的并不是死亡威脅,而是強奸、綁架威脅,事前做好防衛準備,在不法侵害確實發生時憑借防衛準備進行防衛的,也同樣沒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同樣符合國民規范意識的預測。比如,甲女長期受到乙男的騷擾,對乙男抱有恐懼厭惡心理,然后有一天甲女收到乙男的短信:“遲早我都會到你家去強奸你”,從而極其驚慌與恐懼,于是購買了開刃匕首放在自己的枕頭底下防止乙男如果真的到自己家對自己進行強奸時能夠防身。結果一周后乙男真的在晚上撬門闖入甲女家中意圖對甲女實施強奸,甲女在反抗過程中抽出該匕首將乙男直接刺死,在這種情況下,乙男的行為在甲女不反抗的情況下并不會造成甲女重傷、死亡,但是仍然屬于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乙男給甲女發送的威脅短信屬于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威脅,甲女針對這種威脅進行的防衛準備也沒有危害公共安全,因此甲女的行為依然屬于正當防衛,沒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如此認定完全契合國民規范意識的合理期待。
(二)防衛準備為社會倫理道德所容許
社會倫理道德是社會秩序安定的最低程度的保障。防衛人和被侵害人收到了不法侵害人明示的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威脅(如周六晚上我要到你家里去殺你),為了防止在不法侵害人真的實施不法侵害的時候驚慌失措,來不及進行反抗,而在事前進行一定程度的防衛準備(如安裝監控,或者在床邊放一把刀),肯定會被社會倫理所容許,至少不會為社會倫理所反對。因為如果一個人聽到他人親口對自己說將要在未來的某個時間對自己實施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基于保護自己的正當目的而進行事前防衛準備,社會倫理道德是絕對不會也不應當禁止的,因為任何國家的社會倫理道德都不會強求一個人在即將遭遇暴力犯罪時消極忍受,甚至束手無策地等待著侵害的發生。因此,防衛人和被侵害人面對著已經知曉的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威脅進行了防衛準備的,該防衛準備并不會遭到社會倫理道德的非難和反對,反而會為社會倫理道德所容許,司法機關不適宜一律將防衛準備認定為防衛過當。
(三)正當防衛中不法侵害人法益的闕如
正當防衛的本質是“正”對“不正”,正義無需也不應當向不法讓步,防衛人在被侵害時不應當向不法侵害人讓步,這就意味著,在針對不法侵害實施防衛行為的過程中,相對于被侵害人的法益而言,不法侵害人的法益因為其并沒有選擇合法行為,遵守法秩序而不值得保護。即在不法侵害人實施了不法侵害的情況下視為不存在該不法侵害人的法益,這就是正當防衛的一個重要的正當化依據。“不法侵害者既然違反守法義務實施不法侵害行為,在為制止其不法侵害行為所必需的限度內,亦自動喪失履行守法義務的守法公民本來享有的法益保護,面對正當防衛行為對其進行的反擊,不法侵害人既不得借口自身法益面臨威脅而進行反擊,亦不得對防衛行為對其惹起的損害結果尋求法律救濟”。[5]防衛人或者被侵害人事前作出了一定的防衛準備工作也根本沒有背離這個正當化依據,如果簡單地將防衛人或者被侵害人面臨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威脅,事前進行了一定的防衛準備,并最終依靠防衛準備造成不法侵害人重傷或死亡認定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全然不考慮被侵害人所面臨的威脅的內容和防衛準備的必要性,那么就等于承認了在正當防衛中,不法侵害人的法益不但沒有被徹底否認,反而得到了特權,獲得了大于被侵害人法益的要保護性的優待。這明顯違背不法侵害人的法益在正當防衛中應當被否認這一正當化依據,也明顯與正當防衛的本質相背離,進而使得我國刑法關于正當防衛的規定成為一紙空文。相反,將為防止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威脅現實化而事前進行一定的并不危害公共安全的防衛準備,并最終依靠防衛準備保護了被侵害人的生命、身體、性的自主決定權等法益認定為正當防衛,就能完全符合不法侵害人的法益應當被徹底否認這一正當化依據,從而推動正當防衛制度的真正落實。
(四)正當防衛不需要額外要件
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是刑法中最為典型的違法阻卻事由。但是正當防衛的本質與緊急避險的本質(“正”對“正”)完全不同,緊急避險是為了保護一種法益而不得已損失另一個無辜者的較小或同等法益的行為,緊急避險對于避險人來說屬于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對于無辜的人來說則屬于“飛來橫禍”。因此,特定行為若要成立緊急避險進而阻卻違法,必須具備這樣的額外要件:在當時的緊急情況下不存在選擇其他更加輕緩的行為的可能性。但是正當防衛是以正義抗擊不法的制度,防衛人無需向不法侵害人讓步,不需要具備上述額外條件。防衛人在面臨我國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所規定的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時不需要考慮自己是否應當選擇其他更加和緩的行為(比如消極忍受、躲避等)。因此,防衛人或者被侵害人面對來自于不法侵害人的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威脅時,根本不需要考慮是否應該選擇更加輕緩的手段保護自己,防衛人或被侵害人在不法侵害發生前完全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防衛準備。因為此時防衛人或被侵害人不需要選擇比防衛準備更加輕緩的行為,不需要在面對嚴重的不法侵害的威脅時消極容忍或者坐以待斃。所以,進行事前防衛準備也能成立正當防衛。
(五)防衛準備符合正當防衛的性質與目的
正當防衛是刑法賦予公民保護公法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和個人法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財產及其他權利)的重要權利,刑法既然將其規定為公民的一項權利,就應當為公民針對不法侵害進行防衛提供必要而充分的支持,從而使得公民在面對不法侵害時能夠有效行使正當防衛這項權利,從而保護自己或他人的權益。
在被侵害人已經受到了不法侵害人明示的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之威脅的情形下,被侵害人或者防衛人已經預見到在將來的某個時間會發生針對被侵害人不法侵害,此時,防衛人若要充分有效地在不法侵害發生時行使正當防衛權利,就必須進行一定程度的防衛準備(在屋中準備必要的防衛工具、安裝監控等)。否則的話,在不法侵害現實發生時,被侵害人就會在自己的生命、健康、身體法益遭遇現實、緊迫的危險時毫無招架之力,結果就是被侵害人的重大法益肯定會遭受嚴重侵害。
因此,如果我國刑法要求防衛人、被侵害人在遭遇的暴力犯罪的威脅時不能進行預先的防衛準備,那么防衛人或被侵害人面對將來極有可能發生的重大不法侵害就只能采取消極忍讓的態度,而不法侵害人所實施的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為往往具有很大的不可預測性,何時何地發生是防衛人或被侵害人根本估計不到的。因此如果防衛人、被侵害人面對來自于不法侵害人的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威脅不能進行防衛準備,那么不法侵害發生時,面對著不法侵害人進行了充分準備與預謀的暴力犯罪(如用長刀捅刺、用斧頭砍殺等),因為沒有進行任何準備,基本上不可能立刻就能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不法侵害,從而也就不能有效行使正當防衛權利。相反,如果我國刑法不禁止防衛準備,不禁止防衛人或不法侵害人在已經受到不法侵害人明示的暴力犯罪的威脅的情況下進行一定程度的事前準備,那么防衛人或不法侵害人就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預先準備,在不法侵害現實發生時就可以憑借已經準備的工具和其他措施進行防衛,制止不法侵害,從而有效行使正當防衛權利。
(六)被法治發達國家的刑法理論所認可
首先,德國刑法理論認為,事前安裝的自動防衛裝置在正當防衛中可以實現正當化而阻卻違法。金德霍伊澤爾教授認為,“從實質上講,借助于自動的自我保護裝置(鐵蒺藜、自動射擊裝置、地雷以及會咬人的狗)以實施防衛,是可以因緊急防衛而正當化的(所謂‘預先的緊急防衛’)。如果觸發這種裝置的時候,正在發生違法攻擊,是成立緊急防衛的”。[6]依照德國刑法理論的觀點,在正當防衛中,預先設置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防衛裝置(如安裝地雷,在院中飼養不栓鐵鏈的藏獒、高加索等烈性犬)都能夠實現正當化,那么針對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威脅(殺人、強奸、搶劫等威脅),事前進行一定的并不會危害公共安全的防衛準備(在屋子里放置防身刀具、棍棒、安裝探頭,飼養只起到報警作用的非烈性犬等)并憑借此進行防衛的,就更應當在正當防衛中實現正當化,不應當認為防衛準備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因此,德國刑法關于正當防衛的認定并沒有禁止防衛準備。
其次,日本刑法判例也認為,“僅僅憑借預見到侵害這一點,并不會直接喪失侵害的急迫性,但預見到侵害之后,出于積極的加害意思而面對侵害的,就不能認定存在急迫性”。[7]日本刑法關于正當防衛的規定是:為了防衛自己或者他人的權利,面對急迫不正之侵害,不得已而實施的行為。“急迫,是指針對法益的侵害現實存在或正在迫近。”[8]由此可見,在日本司法中,單純預見到不法侵害并不會導致正當防衛的起因條件(現實的不法侵害)喪失。因此,預見到不法侵害同樣可以成立正當防衛,僅僅是在預見到不法侵害后,并不是為了保護法益免遭不法侵害,而是出于積極加害的目的所實施的防衛行為才不會成立正當防衛。而防衛人或者被侵害人在受到來自于不法侵害人的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威脅以后,就屬于預見到不法侵害的情形。在此基礎上,防衛人或者被侵害人所進行的的防衛準備,并不具有積極加害不法侵害人的意圖,而是只具有保護被侵害人的法益免遭不法侵害的意圖,因此并不會為刑法所反對。在這個意義上,日本刑法中的正當防衛制度也沒有禁止防衛準備。
因此,在德國、日本兩國的刑法運轉流暢的正當防衛制度中,并沒有禁止防衛準備,并沒有將進行了事前防衛準備排除在正當防衛之外。因此,德日兩國刑法理論關于正當防衛的適用為我國提供了經驗:成立正當防衛并不否定防衛準備,司法機關完全能夠將預見到不法侵害后的防衛準備認定為正當防衛。
我國刑法關于正當防衛制度的規定與德日兩國具有相似之處,我國刑法甚至放寬了正當防衛的成立條件,并沒有像日本刑法那樣規定正當防衛必須是“不得已”而實施。那么,既然正當防衛成立條件比我國更為嚴格的日本刑法沒有禁止防衛準備,我國不將防衛準備認定為防衛過當也不存在障礙。
在淶源反殺案中,淶源縣人民檢察院正是進行了這樣的正確認定,沒有將王某某一家人面對王磊的死亡威脅所進行的事前防衛準備認定為防衛過當。
四、結語
淶源反殺案的正確處理,是我國法治進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必將推動我國刑法關于正當防衛的規定的正確適用。本案最大的啟示,就是為應對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行為的威脅,事先進行一定程度的防衛準備,最終憑借這些防衛準備制止了不法侵害,保護了被侵害人的法益,即使造成不法侵害人重傷、死亡的,也同樣符合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的規定,不屬于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行為,不應當認定為防衛過當。這個啟示將促進司法實務對正當防衛的正確理解,進而防止錯誤地將防衛準備認定為防衛過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