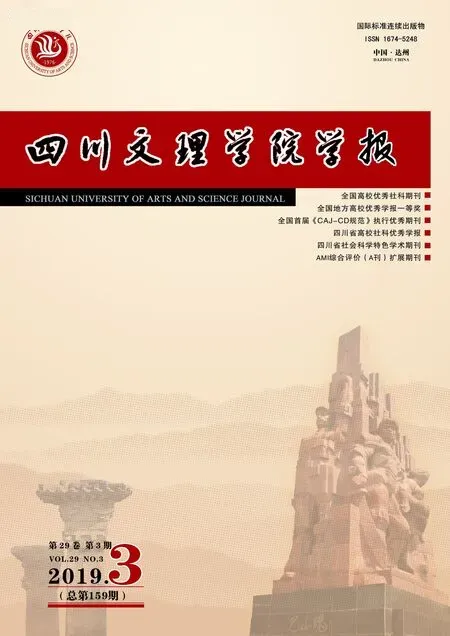體育活動與心理健康狀況關系的基因假說
艾 水,梁 琴
(1. 達州職業(yè)技術學院黨政辦公室;2. 達州市兒童中心,四川達州635000)
常規(guī)的體育活動不僅僅能夠減少軀體疾病的發(fā)病率,而且經(jīng)常進行體育活動的人還會表現(xiàn)出認知能力尤其是額葉執(zhí)行功能上的優(yōu)勢,[1]他們的思維更加敏捷,心理也更加健康 。[2]
體育運動對心理健康的促進是與焦慮和抑郁癥狀減輕相聯(lián)系的。Landers and Petruzzello(1994)對1960年到1991年之間關于體育活動和焦慮癥狀之間關系的27篇綜述進行檢驗,發(fā)現(xiàn)81%的綜述中作者都作出了體育活動與體育運動后的焦慮減輕存在相關的結論,而且這些綜述的結果都很一致;而其他19%作出體育活動和心理健康之間沒有相關結論的綜述中,大多數(shù)的結果也支持體育活動和焦慮減輕之間的相關性。而對體育活動和抑郁癥狀關系的綜述發(fā)現(xiàn)(Craft, 1997; Calfas & Taylor, 1994):體育活動與抑郁癥狀的減輕是相關的,尤其是當體育訓練項目的時間超過9周(Craft, 1997; North et al., 1990),活動時間更長、強度更大、每周進行更多天數(shù)的時間時(Craft, 1997)其癥狀減輕的效果更加明顯。
體育活動和心理健康之間的正向關系得到了廣泛的承認。但是進一步的問題是:這種關系是一種因果關系,還是僅僅為一種相關關系?換句話說,這種伴隨著體育活動而出現(xiàn)的心理健康狀況的改善到底是由于體育活動本身所直接導致的,還是由于二者背后所隱藏的某種“調(diào)控杠桿”的作用而產(chǎn)生的?另一方面,先前關于體育活動促進效應的研究結論大多是建立在大樣本平均效應基礎上(population-level)的,這種平均效應卻掩藏著個體差異,即不同的被試在體育活動之后所獲得的心理健康狀況的改善程度卻不同。那么,是什么因素在決定和影響著“體育活動效應”的表達?
先前研究者大多認為體育活動和心理健康之間的這種關系是一種因果關系,它反映的是由體育活動這個變量的變化對心理健康水平的直接影響。但是最近來以De Moor等為代表的行為遺傳學研究者則提出了體育活動與心理健康關系的基因假說。本綜述主要目的就是對該假說進行介紹并評述,首先介紹該假設的基本內(nèi)容,并列舉支持支持基因假說的相關證據(jù);隨后對該假說進行評論,并指出今后值得研究的一些問題。
一、體育活動——心理健康關系的基因假說
基因假說(De Geus, & De Moor, 2008)認為:個體的體育活動參與情況、以及體育活動與心理健康狀況之間的關系都受到基因因素的調(diào)控,體育活動和心理健康的關系也受到基因因素的影響;基因通過基因的多效性和基因-體育活動交互作用這兩個具體的機制對心理健康狀況產(chǎn)生影響。[3]
基因不僅僅能夠影響心血管疾病和抑郁癥等癥狀的發(fā)生率,而且也會影響個體的自主體育活動行為。這種低級的生理變異對機體和行為水平上更加復雜的特質(zhì)產(chǎn)生影響的現(xiàn)象被成為基因的多效性(pleiotropy)。基因多效性對理解體育活動與心理健康關系的意義在于:如果基因對體育活動的影響比它對心理健康狀況的影響更早發(fā)生,那么如果不考慮基因的作用就會高估體育活動對心理健康狀況的作用。另外,即使先前的實驗室訓練研究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體育活動的效應,但是這種效應具有個體差異,一些被試會很快表現(xiàn)出更強的體育活動促進效應,而其他一些被試的促進效應則相對較慢、較少,甚至沒有表現(xiàn)出任何的促進效果。如果體育活動效應的個體差異是來自于不同體育活動者的基因差異,那么這種體育活動效應稱為基因-體育活動的交互作用(gene-by-exercise interaction)。
二、體育活動行為的可遺傳性
先前大量的研究都從社會或者環(huán)境的角度探討影響自主體育活動的因素,例如體育活動設施的狀況(Matson-Koffman, Brownstein, Neiner, & Greaney, 2005),社會經(jīng)濟水平(Haase, Steptoe, Sallis, & Wardle, 2004),高度工作壓力(van Loon, Tijhuis, Surtees, & Ormel, 2000; Payne, Jones, & Harris, 2005),家庭、同伴、同事的社會支持水平(Orleans, Kraft, Marx, & McGinnis, 2003; Sherwood & Jeffery, 2000)。但是這些因素沒有一個被證明是體育活動的決定因素。[4-7]
體育活動的可遺傳性已經(jīng)得到了廣泛的承認。對19歲到60歲之間的雙生子成年人的研究顯示:基因因素和非共享的環(huán)境因素能夠解釋體育活動的變異,其中基因因素能夠解釋其中的35%-83%。[8-11]
體育活動行為遺傳性的最有力證據(jù)來自于雙生子研究。雙生子研究可以通過比較同卵雙生、異卵雙生和非雙生子的體育活動行為,從而把基因的影響和環(huán)境的影響分離開來。同卵雙生子具有相同的基因,而且常常擁有相同的家庭環(huán)境;異卵雙生子有相同的家庭環(huán)境,但是他們平均來講只有一半的相同基因。如果同卵雙生子之間體育活動行為的相似性比異卵雙生子更高,就意味著基因會影響體育活動行為。如果兩種雙生子的體育活動相似性沒有差異,那么就說明環(huán)境因素對體育活動的影響 。[12]與家庭親-子設計(parent-offspring family design)不同,雙生子研究可以從同一代人的不同成員來驗證體育活動行為的遺傳性。大量雙生子研究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基因因素對體育活動參與度、體育活動頻率、時間和強度等都具有顯著影響。[13-15]而Stubbe等所進行的一項由7個國家共7個雙生子中心的協(xié)作研究(Stubbe, Boomsma, et al., 2006)也證實了以上的結果,這項研究對37051對雙生子的體育活動進行了調(diào)查評估,結果發(fā)現(xiàn)每個國家的被試都表現(xiàn)出體育活動的基因效應(基因因素對體育活動參與狀況的解釋力度范圍為40.5%-70%)。[16]
基因對體育活動的影響強度是隨著年齡的變化而變化的,其中最顯著的變化發(fā)生在青少年期。在兒童和青少年早期直至13歲,基因對于體育活動的個體差異都沒有顯著解釋作用,而環(huán)境因素卻具有顯著的解釋作用;到了青少年中期和晚期,環(huán)境因素的效應逐漸減小,而基因因素則開始決定體育活動的個體變異;在19-20歲的時候其解釋力度達到最高(85%),隨后基因的影響又逐漸降低,到成年期則達到平穩(wěn)(其解釋力度為50%左右)。
三、心理健康的基因多效性
先前研究大多認為:經(jīng)常參與體育活動的被試所表現(xiàn)出來的良好心理健康狀況是由于體育活動本身所引起的。但De Moor的基因假說則認為:體育活動行為和心理健康之間的這種關系可能反映的是某些基因的作用,這些基因不僅僅對體育活動參與狀況產(chǎn)生影響,同時也會影響心理健康狀況;而那些阻止個體參與體育活動的基因則可能同時也與諸如焦慮、抑郁等癥狀有關。
Stubbe等人(Stubbe, De Moor, Boomsma, & de Geus, 2006)對來自荷蘭雙生子注冊中心的162對同卵雙胞胎(discordant monozygotic twin pairs),174對異卵雙胞胎(discordant dizygotic twin pairs)以及2842名非雙生子被試(年齡范圍18-65歲)進行了體育活動和心理健康狀況的因果關系分析。他們通過調(diào)查收集了被試的體育活動類型、頻率和持續(xù)時間,并用Ainsworth' Compendium of physical acitivity 收集了被試的能量代謝當量(metabolic equivalent value)。并用生活滿意度量表和主觀幸福感量表調(diào)查了被試的心理狀態(tài)。結果發(fā)現(xiàn),非雙生子被試中,經(jīng)常參加體育活動的被試比不參加體育活動的被試生活滿意度更高,幸福感更強;而對于同卵雙生子和異卵雙生子被試來說,經(jīng)常鍛煉者與不經(jīng)常鍛煉者在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上并不存在顯著的差異。研究者認為這些結果否定了體育活動與心理健康之間存在因果關系,而基因因素可能在背后對二者產(chǎn)生著影響。
在接下來的一項研究(De Moor, Posthuma et al., 2007)中,De Moor等人用健康狀況自評的方式對來自于2831個家庭中的5140名荷蘭成人雙生子以及他們的非雙生子兄弟姐妹進行了調(diào)查。結果顯示影響體育活動參與情況和自評心理健康狀況的基因因素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重疊(r=0.36),而更重要的是這種重疊能夠完全解釋體育活動參與情況和心理健康狀況的關系。研究者們認為這些結果再次支持了基因的多效性,并認為即使雙生子的體育活動參與程度不同,基因相同的雙生子的心理健康狀況也表現(xiàn)出了高度相似性。[17]
De Moor等人(De Moor et al,2008)對8558名雙生子及其家庭成員進行了2,4,7,9,11年的跟蹤,從而對體育活動與心理健康之間因果假設的各種結果預期進行了驗證。其中第一個預期是:“如果體育活動是影響焦慮和抑郁癥的原因,那么所有影響體育活動參與情況的基因和環(huán)境因素都會對這兩種癥狀產(chǎn)生影響”。然而,研究者用結構方程模型對雙生子的數(shù)據(jù)分析發(fā)現(xiàn):體育活動和心理癥狀之間僅僅在基因變量上的相關達到顯著(不同癥狀量表和不同時間間隔之間的相關系數(shù)介于-0.16和-0.44之間),而在環(huán)境變量上的相關為0。這些就意味著無論時間間隔多久,那些促使被試去參加體育活動的環(huán)境因素并不能導致焦慮或者抑郁癥狀的降低,而與此相反,那些促進被試體育活動參與情況的基因因素同時也會導致焦慮和抑郁癥狀的降低。
因果假設的另一個預期是:“同卵雙生子對之間每周新陳代謝指數(shù)(MET)的差異應該與每對間焦慮癥狀或抑郁癥狀的差異量存在相關”。然而,De Moor等人(De Moor et al,2008)的研究結果發(fā)現(xiàn):二者間的相關系數(shù)僅僅為-0.04到0.03之間,這說明同卵雙生子的心理癥狀水平差異與體育活動的差異沒有顯著的相關關系。另外,每個被試不同時間段內(nèi)體育活動的情況并不能夠預測他們焦慮癥狀或者抑郁癥狀的水平(相關系數(shù)為-0.05到0.05之間)。
總之,研究者們認為這些結果都支持了基因的多效性,而不支持體育活動與心理健康水平的因果關系。當然,這并不排除對某些特定群體來說,體育活動可能對心理健康水平具有直接影響,而且De Moor等人也認為他們的結果與臨床中所發(fā)現(xiàn)的通過體育活動緩解病人焦慮和抑郁水平的研究結果之間并不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基因因素是如何對體育活動和心理健康進行調(diào)控的呢?
四、基因和體育活動的交互作用如何對心理健康產(chǎn)生影響
De Moor等人認為(De Geus, & De Moor, 2008):體育活動的這種情緒體驗是受到基因因素的調(diào)控的。個體的基因型決定了體育活動所帶來的積極情緒和厭惡情緒體驗的差異。不經(jīng)常進行體育活動者的基因型導致體育活動給他們帶來的厭惡情緒體驗超過了積極情緒體驗。而對于經(jīng)常進行體育活動的個體而言,體育活動所帶來的積極效應應該超過它帶來的厭惡效應,而體育活動之后所體驗到的這種“良好感覺”會成為他們較好心理健康狀態(tài)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體育活動帶來的厭惡效應大于積極效應的話,個體就會減少或者中斷體育活動。反之,個體就會越來越多的參與到體育活動中,成為經(jīng)常鍛煉的人。對于經(jīng)常鍛煉的人來講,體育鍛煉能夠導致心理的健康狀態(tài)。基因和體育活動之間的這種交互作用不僅僅能夠解釋為什么經(jīng)常鍛煉者認為在運動之后情緒得到更大的增強(相對于不經(jīng)常鍛煉者而言),而且還有利于解釋體育活動和心理健康水平之間的關系。
五、基因對體育運動影響心理健康狀況的可能神經(jīng)機制
來自神經(jīng)生理學和認知神經(jīng)科學的研究發(fā)現(xiàn):由于體育活動過程中的一元胺消耗會導致個體疲勞,因此體育運動所導致的厭惡效應可能依賴于單胺能系統(tǒng)的基因型差異,而體育運動之后的獎賞效應則可能依賴于類鴉片活性肽(opioid)和多巴胺系統(tǒng)的基因性差異,發(fā)現(xiàn)劇烈運動對神經(jīng)活動有顯著的影響,而這種神經(jīng)活動一方面是由正向傳輸?shù)倪\動命令引起的,而另一方面則是由于肌肉的傳入性反饋而引起的。[18-19]而這些神經(jīng)活動的區(qū)域(杏仁核、扣帶回前部的背側、扣帶回膝和眶額葉皮質(zhì))與內(nèi)臟感覺和情緒評價相關區(qū)域是相互重合的。[20]由于基因對于這些區(qū)域的大小和功能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因此有可能這也是基因-體育活動的交互作用的一個來源。[21]
厭惡情緒和獎賞情緒的基因差異還反應在體育活動后不同時間。如果體育運動后立即對被試進行訪談,被試會報告出顯著的情緒水平的提高,包括緊張感、焦慮和憤怒感的降低,以及活力感的增強。[22]。研究者認為體育活動之后的正性情緒后效可能與opioid mechanisms和單胺能機制等有關。[23-24]而這些效應的強度或者方向則是受到相應基因影響的。與此相似的是,體育活動之后的厭惡情緒也會受到基因型的影響,一些基因型的被試比其他基因型的被試更容易產(chǎn)生厭惡情緒。
六、對基因假說的述評
基因假說的提出,對于幫助研究者理解體育活動和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先前研究大多從心理、人格、社會環(huán)境等各個角度去論證二者的關系,但是這些研究大多僅僅是一種相關關系的探討,而基因假設為研究者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從生理和遺傳機制的角度去探討二者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先前研究結論大多是建立在大樣本平均的結果基礎之上的,這種方法忽視了其背后所隱藏的每個個體之間的差異,基因理論則強調(diào)每個被試的基因傾向的差異性,以及這種差異對體育活動效應表達所能夠產(chǎn)生的影響。
但是,基因假設僅僅是根據(jù)行為遺傳學研究而做出的一種推測。究竟是什么基因型決定著個體的體育活動以及相應的心理健康狀況?盡管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等的發(fā)展使得研究者能夠發(fā)現(xiàn)了肥胖、心血管疾病相關的基因,而且已經(jīng)有研究暗示某些染色體與體育運動行為有關,甚至發(fā)現(xiàn)了一些可能相關的基因。[25-27]但是要確定是否真正存在著決定這二者的基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對這些可能基因的效應進行不斷重復驗證,如果能夠找到對體育活動具有影響的基因,接下來再探討該基因與心理健康狀況之間的關系,就能夠找到基因、體育活動與心理健康三者之間關系的最有力的證據(jù)。[28-30]
盡管研究者提出基因-體育活動之間交互作用的是影響行心理健康的可能機制,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關于這種交互作用的直接證據(jù)。今后的研究可以對基因水平和體育活動水平兩個變量進行系統(tǒng)的操縱變化,例如對不同體育活動水平的雙生子、非雙生子被試進行調(diào)查甚至是進行不同水平的體育活動訓練,從而觀察他們心理健康狀況的改變。[31-33]另外,應該意識到,除了基因等先天因素之外,還有其他許多對個體體育鍛煉行為、個體心理健康產(chǎn)生影響的因素。除了對心理健康狀況進行調(diào)查之外,還需要搜集被試的體育活動過程中相關生理指標以及情緒、認知評價等心理指標,這樣才能更詳細的探討這種交互作用的具體機制。
基因假說對于體育活動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基因假說并不否認體育活動在心理健康狀況中的作用,也并不是暗示“基因決定了心理健康狀況,體育活動無用”。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一些人能夠堅持從事體育活動,而其他人則很容易放棄;一些人能夠從體育活動或者體育療法中得到心理健康狀況的改善,而另一些被試則很難獲益。基因假說的實踐意義在于,在開展各種體育活動以及實施體育療法時,必須考慮基因變異的影響,這意味著對于不同個體需要不同的體育活動計劃,這些個性化的活動計劃能夠促進個體的積極情緒,而避免厭惡情緒的增長,而理解和探討相關的基因機制則是成功指定和設計個性化活動計劃的必要前提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