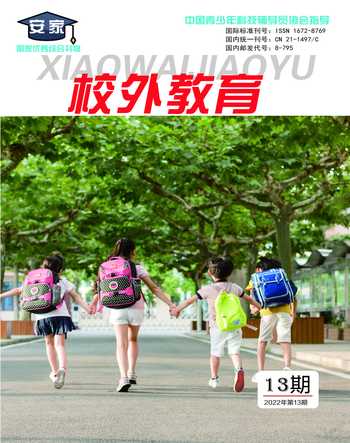核心素養背景下的中小學體育健康教育模式探析
廖仁海
摘要:隨著社會的進步,經濟不斷發展,我們對于具體的教育教學也有了新的認知和更高層次的要求。目前在新課改的不斷推進下,教育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也在進行相應的調整。在推崇核心素養培養的當今時代,小學體育教學與健康教育的部分占到了很大的比重。我們如何對于中小學體育健康教育模式展開研究已經成為我們在具體的教育教學中需要重視的一個部分。本文針對目前體育與健康科學在核心素養中所提到的健康教育教學要求進行了闡述,并且對于相應的教學內容進行了分析。最后給出了具體的中小學體育健康教育模式完善相關建議和對策,希望能夠為相關研究提供借鑒。
關鍵詞:核心素養;中小學生;體育;健康教育;分析;對策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隨著新課改的不斷深入和發展,我們對于中小學生的整體心理健康有了更高層次的重視。我們必須在兼顧學生學習進步的同時,也要全力的確保學生的整體身心健康的發展,促進他們從內而外的實現進步和提升。因此,在具體的小學體育與健康課程中,我們要明確健康教育的意義,對于核心素養下小學體育健康教育的內容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促進整體教育教學模式的提升[1]。
一、核心素養下中小學體育健康教育的新要求
新課改對于體育健康教育教學等整體做出了規范。通過對于新課標的研讀我們發現新課標中對于體育和健康學科的整體核心素養進行了明確,其內容主要包括健康行為、體育品德以及運動能力這三個部分。其中又將運動能力分為專項運動和基本的某種能力,而基本運動能力則是指的生活中我們必備的一些能力,專項運動能力則是某項運動特定的一特定的能力。而健康行為則囊括衛生習慣、作息、鍛煉以及飲食等方面。具體的教學要求要求學生在具體的學習生活中學會如何遠離不好的行為習慣,預防運動中產生的損傷和疲勞。幫助學生調整心態,保持良好的心態和習慣,形成健康的體育意識和體育習慣,對于健康的相關知識有一定的掌握和認知,并且能夠運用到自身鍛煉上來。而具體到體育品德則包括體育道德、品格以及精神這幾個方面。能夠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社會責任感、勝負觀以及養成良好的體育品格和精神,幫助他們在今后的學習生活中能夠更好的團隊協作,實現自身身體以及心理的健康實現全面發展。這些教學變革和教學要求都是之前所沒有的,對于學生的整體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和作用,能夠很好的幫助學生實現自身發展和進步,最大程度的促進學生核心素養的發展和提升[2]。
二、體育健康教育的具體教學內容及問題
在中小學具體體育健康教育中內容涵蓋了很多方面。在新課改的不斷推進,我們發現在具體的教育教學中表現出來幾個方面。縱觀中小學整體的體育教育,整體呈現出各個年級層層遞進的關系。比如:在健康教育的數量以及主題內容上,小學和初中年級的健康教育就呈現出層層遞進的關系。我們在具體的內容教學內容中發現,基本上教材還是注重于對于學生基礎健康知識以及體育技能等方面,同時也側重于學生安全與安全避險方面的培養。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具體的教育中,缺少學生心理健康以及體育道德方面內容的設計。這而這兩個方面恰恰十分有利于核心素養的培養,能夠幫助學生最大程度的實現自身整體體育品德、行為以及體育健康思維的養成。心理健康對于學生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存在,只有心理積極陽光,健康向上才能夠促使他們更加積極的投入到具體的體育運動中,逐漸輔助學生養成良好的體育習慣以及體育品質。除此之外,在具體的教學內容中,對于生長發育、保健和膳食營養等等方面的內容在中學年級的體育健康教育中出現的也較少。而相比之下在小學體育健康教育中出現的較多,這難道是說明中學生在這一部分學習上是不想要的嗎?并不是,這是教學內容一定程度上的缺失,這就會導致學生在這一部分知識的學習上的欠缺,這是需要我們進行彌補和延伸的,最大程度的幫助學生實現全面的學習和認知[3]。
三、中小學體育健康教育模式完善的建議
(一)結合時代特征,促進中小學生身心發展
在具體的教育教學,學生的整體發展一直是我們教育教學中十分關注的重點,也是我們今后學生發展的基礎所在。因此,我們在具體的教育教學中要特別注重學生身心發展,確保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夠有效的實現對于體育健康的理解和實踐。比如:教師應當將相關的健康教育內容與具體的時代特征和訊息相結合,引入相關的實踐案例來講述目前我們時代特征下存在的問題,如何通過我們的體育健康教育實現相關問題的改善。
(二)結合學生實際,促進教育發展
在具體的教育中我們發現,教師在具體的教育中需要深入的了解學生的整體特征,對于本年級的學生有深入的了解和分析,通過了解來適當的安排體育健康教育內容,實現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促進他們擁有健康科學的體育狀態,最終促進他們綜合核心素養的提升比如:教師可以在教學中安排討論環節,對于學習中產生的問題進行探討,拉近師生之間的關系。除此之外,教師還可以利用微信平臺去學生展開對話,讓學生將學習中遇到的問題反饋給自己,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幫助學生解決問題,實現自我發展和進步[5]。
(三)引入生活實例,促進學生學習興趣的提升
在具體的教學中,我們發現很多教學內容是與生活實踐相關聯的,我們必須在聯系生活實際的基礎上,拉近課程教學內容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引導學生在具體的學習和生活中積極搜集與教學內容相關的信息主題和生活故事。通過這些案例故事的分析以及分享,引導學生積極主動的投入到學習中來,提高學生對于體育健康學科學習的興趣,促進整體教育教學效率的提升。通過實踐檢驗健康教育的意義。在具體的教育中學生由于年齡階段較小,他們對于健康教育的理解和認知不是很深刻,也沒有真正的了解到這些知識對于自身發展的意義[6]。因此,教師應當積極的準備一些相應的活動,將具體的健康知識應用到實踐中來,通過實踐應用,實現學生對于相關知識的理解和感受,讓他們能夠更加深刻的體會到健康教育的意義,以及健康教育為自己帶來的實踐效果,讓他們在學習中能夠更加積極努力的投入到學習中來,對于相關學習更加感興趣,實現整體教學和學習效率的提升。
綜上所述,隨著新課改的不斷推進,我們對于中小學體育健康教育有了新的要求。我們通過本文的研究發現在具體的中小學體育健康教育中存在的具體教學內容和教學要求進行了改革,面對教育教學內容上存在一些問題進行了探討,都是需要我們進行深刻的整改和優化的,以此來促進中小學體育健康教育的發展和完善。
參考文獻
[1]楊同春, 鄒旭鋁. 核心素養背景下的中小學體育健康教育內容分析[J]. 體育教學, 2018,34(434):343-344.
[2]楊惠燕. 體育學科核心素養培育背景下健康教育的實施策略研究[J]. 當代體育科技, 2019, 339(30):342-343.
備注:廈門市教育科學“十三五”規劃2019年度課題;題目:核心素養視角下中小學健康素養研究;課題批準號: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