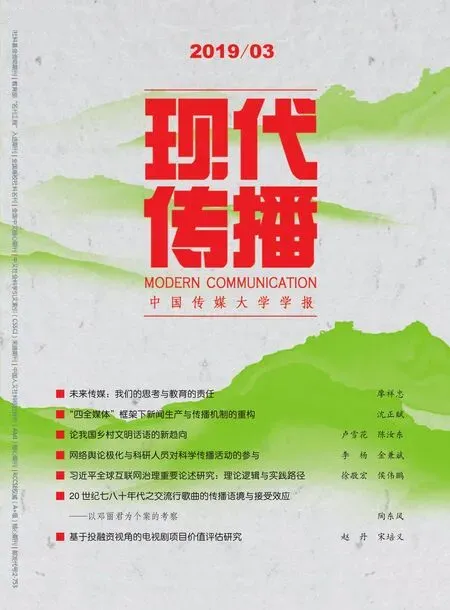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流行歌曲的傳播語境與接受效應
——以鄧麗君為個案的考察
■ 陶東風
在談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鄧麗君熱時,著名散文家葉匡政回憶說:“當年國內的報紙、雜志、電視、電臺,都極難發現她(鄧麗君)的身影或聲音。沒有任何包裝或炒作,她就這么溫存地撫慰了億萬人的心靈,成為一代人心中永遠的偶像。相信對音樂傳播史來說,這也算得上一個奇跡。”①
對習慣于今天的大眾文化傳播方式——在官方電臺或電視臺播出,由官方出版發行批量化的磁帶或光盤,舉辦大型演唱會,作為電視劇的插曲隨電視劇獲得流行等——的聽眾而言,鄧麗君流行歌曲在當時的傳播和接受方式是不可思議的,她的流行的確是一個奇跡,一個值得認真解讀的奇跡,一個時過境遷就不可能再出現的奇跡,甚至還是一個能夠挑戰、修正西方大眾文化傳播—接受理論的奇跡。
一、轉型期流行歌曲的三種傳播方式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是一個轉型期,文化領域的開放還沒有全面展開,除了政治化的革命文化,其他文化類型幾乎不存在,更沒有商業化的流行文化。音樂領域也依然是革命歌曲、革命音樂的天下,沒有流行文化、流行音樂的份。
據當事人回憶,最早的流行歌曲應該是通過收聽所謂“敵臺”進入中國大陸的。②讓我們接著看葉匡政的回憶:“在海峽兩岸冰冷對峙之時,很多人最早是從‘敵臺’聆聽到她的歌聲的。當時的臺灣方面倡導對大陸的軟性宣傳,于是委托‘央廣’特別制作了‘鄧麗君時間’欄目,每周一到周六晚8點播出,25分鐘,內容全是鄧麗君的新聞或歌曲。這檔節目通過‘央廣’短波,向大陸播放。”③除了臺灣地區和美國的“敵臺”,還有澳洲的澳洲廣播電臺華語節目也是鄧麗君進入大陸的重要媒介。1978 年,澳洲廣播電臺的著名主持人王恩禧在澳洲廣播電臺(簡稱“澳廣”)中文部創辦并主持以點歌為主的節目《您喜愛的歌》,其中鄧麗君歌曲一度成為點播率最高的曲目。據王介紹,澳洲廣播電臺以娛樂和旅游節目居多,相比臺灣和美國的廣播聲音更為清晰,甚至超過國內的一些廣播電臺。澳洲電臺從而成為人們收聽鄧麗君的最佳選擇。④
那個時代流行音樂傳播的第二種方式是走私。學者宗道一在其著名散文《聽鄧麗君的年代》中這樣寫道:“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一位小我好幾歲的不同寢室的學友趙君慨然將其那只視為珍寶的三洋盒式錄音機(已放入鄧麗君的磁帶)借我消受一宿。夜深人靜,萬籟俱寂,周遭一片寧靜。為防不測,我放下蚊帳,躲進被窩,輕輕按下了放音鍵。萬萬沒有想到的,那第一首歌就是讓人心驚肉跳的《何日君再來》! ”⑤流行音樂的這種傳播—接受場景在當時是有普遍性的,它在電影《芳華》里的文工團出現過,在其他與宗道一年紀相仿者的回憶錄里也不斷得到印證,比如張閎的《文化走私時代的鄧麗君》:“20世紀70年代末的某一天,一群大學生聚在簡陋的寢室里,圍著大板磚似的三洋牌單聲道收錄機聽歌。……當時,這種‘靡靡之音’是不可能被公開傳播的,如同其他一些海外物品一樣,只能通過隱秘的地下管道來傳播。事實上,那是一個走私活動很活躍的時代。一些較酷的日用消費品,諸如牛仔褲、T恤衫、墨鏡、折疊傘、打火機、電子表、收錄機、電視機,等等,都是走私的對象。便攜式收錄兩用機和錄音磁帶,也是必不可少的構件。當時,大鬢角飛機頭發型、墨鏡、喇叭褲、花襯衫、三節頭皮鞋和四喇叭收錄機是有叛逆傾向的所謂‘不良青年’的全副‘行頭’。他們斜提著收錄機,吹著不成調的口哨,招搖過市,一路惹來道德純潔的市民的白眼。這一情形,構成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城鎮的文化奇觀。”⑥
可見,走私在當時不只是一種民間商品交易活動,也是一種民間的文化傳播活動——張閎所謂“文化走私”。與走私一道進入大陸的,包括一整套相關的生活方式、文化觀念和情感結構,并對革命的生活方式、文化觀念和情感結構形成了極大沖擊,這印證了威廉斯“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著名論斷。鄧麗君就是這場“文化走私”浪潮中規模最大的“走私品”。
走私活動最為普遍的地區當然是廣東。廣東毗鄰港澳,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外貿港口城市,素來有走私傳統,建國后也未曾被完全鏟除(即使在1966年至1976年“文革”期間,廣東和港臺之間的走私活動也還零星存在)。粉碎“四人幫”不久,廣東的走私活動開始迅速恢復。鄧麗君的流行歌曲和港臺地區的通俗劇作為發生期最早的流行文化,就是從那里通過走私錄像帶、錄音帶的方式傳入大陸的。
據1981年1月13日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發布的“批轉省委宣傳部關于制止不健康的錄像帶錄音帶在社會上流傳的報告”⑦披露,20世紀80年代初走私并出售、播放錄像帶、錄音帶的活動在廣東非常普遍。僅以1980年為例,那一年,湛江地區相關部門查緝到香港走私船中的錄音帶27萬盒,其中有數萬盒包含《瘋狂的周末》《馬場得意》《有錢有面》《情絲剪不斷》所謂“色情、低級、庸俗歌曲”⑧,其中很多歌曲是鄧麗君唱的。汕頭地區查獲走私錄音帶33萬4千多盒,其中有被認為“內容反動”的《日落北京城》《我們的決心》《莫待失敗徒感慨》《躍馬中原》《國恩家慶》等我國臺灣地區歌曲。這些錄音帶除少數內部銷售給“干部”外,大多數由公安部門交給當地商業部門公開出售,價格不菲(3—5元/盒)。珠海市拱北樂聲電子廠和中山縣坦背珍寶電子廠,本來是為外商加工裝配空白錄音帶的,但從1980年以來,未經宣傳、文化主管部門同意,就從香港進口有聲錄音帶進行復制,并在國內市場銷售。廣東還有一些地區的文化部門還有自己的錄像隊放映走私錄像帶以盈利。比如博羅縣文化局錄像隊,從1980年6月至10月,共放映香港、臺灣地區錄像帶161場,觀眾達11萬多人次,收入人民幣2萬3千多元。該隊放映的錄像帶有《龍門客棧》《真假千金》《庭院深深》等十幾部。
從這些不完全的資料可以看出,走私、翻錄、銷售、播放港澳臺地區錄像帶、錄音帶現象,在當時非常普遍,數量不小,且大多有官方機構和人員參與其中,并不完全是民間的或非法的。這就難怪廣東省廣州市革命委員會1980年的一個文件“關于禁止出售、轉錄內容反動和色情的錄音帶、唱片的通知”⑨會這樣表述:“近年來,從各種渠道流入我市的錄音帶、唱片等數量很多。據調查,這些錄音帶、唱片的內容十分龐雜,甚至發現有反動和色情的歌曲。有些單位為了獲取利潤,公開或私下收購、出售、代客轉錄,致使這些歌曲在社會流行,特別是在青少年中廣為流傳,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可見這些走私活動背后的推手之一就是地方政府或企事業單位,其主要原因是有利可圖。廣州市園林系統和服務行業還辦有音樂茶座(另一種流行文化的傳播方式),其收入提成被作為職工獎金發放。音樂茶座所賣的飲料、食品價格遠高于市場價,其提價部分的收入,一半歸職工均分。⑩
從這里也可以看到,在當時的特殊時期,這種現象屬于法律的灰色地帶,是否違法難以一概而論。地方政府更多通過臨時性政策加以管理,而這種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據則是中央的意見。比如,在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1980—1983年間,廣東省委(革委會)省政府、廣州市委(革委會)市政府、廣州市旅游局、服務局、公安局等,就接二連三地發布了很多政策文件,集中整肅走私錄音帶、錄像帶(以及音樂茶座和舞會、涉外電視臺和電視節目等)。但這些數量眾多的文件之所以要三令五申反復下發,似乎從反面證明了其整治力度的不足,也缺乏一而貫之的法律依據。
發生期流行音樂的第三種傳播—接受方式是音樂茶座(有時伴有舞會)。還是以廣州為例,廣州市服務旅游局宣傳科1983年11月7日曾經受中共廣州市服務旅游局委員會委托,做過一個“服務旅游系統音樂茶座、閉路電視等文娛設施的情況調查”,其中披露了非常有價值的信息。依據這個調查,音樂茶座出現于1980年初,原來是廣州的一些涉外賓館——如東方賓館、廣外賓館、人民大廳、流花賓館、新亞賓館——為外賓、港澳臺客人提供的。據1983年11月的統計,廣州各音樂茶座共設有座位1880個,每晚顧客約900多人,最多時達到每晚2600人,最少時也有600人,票價為每人5到6元。東方賓館和人民大廳還各有迪斯科舞廳1處。此外,全市還有播放流行音樂的夜茶市11處,座位約4870個。在當時,這已經屬于具有相當規模的商業活動了。
這些音樂茶座本是政府特許的,對主辦者的資質(涉外大賓館)、演出者(一般是文化局派出)、參加者(外國人和華僑)和演唱內容(比如流行歌曲有一定比例)都進行了規定(參見1981年12月省政府頒發的248號文件)。但因為音樂茶座收費較高,舉辦這樣的茶座顯然是一筆有利可圖的生意,因此,這些規定實際上常被違反,使各級政府的“規定”“意見”“通知”的實際效果大打折扣。據廣州市文化局1982年3月13日發布的《貫徹粵府(1981)248號文情況的報告》,文化局下屬文藝科曾成立專門小組對全市舞會及音樂茶座進行全面的甄核、登記、調查,反映的情況如下:
1.舞會、音樂茶座的數量在248號文件下達后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更是迅猛發展”,其范圍大大超出市內各大涉外賓館,市園林系統的各公園和市服務行業的一些酒家飯館,都紛紛自行辦起了舞會或音樂茶座,而且均未按文件規定向文化部門辦理申報手續;
2.音樂茶座沒有按照各級政府的要求對消費服務對象進行限制(各級文件明確規定只能為外國人、華僑、港澳臺僑胞),隨著茶座的急劇增加,本地的青年聽眾數量急劇增加;
3.各音樂茶座的聽眾中外國人和港澳臺同胞比例高的地方,中國本民族或廣東本地的歌曲反而能受到歡迎,而“本地聽眾比例越大的場所,越是出現本地青年聽眾熱衷追求港、臺流行歌曲的情況,對演唱中國歌曲反感,甚至起哄、喝倒彩”。據其介紹,海珠區曲藝隊的曲藝名演員賴天涯在音樂茶座唱粵曲,還被轟下臺,“現已無人敢在音樂茶座唱粵曲了”。
二、流行歌曲的傳播語境與接受效應
以上簡單歸納介紹了大眾文化發生期流行音樂的三種特定傳播—接受方式。那么,通過這些方式傳播的流行音樂在當時產生的又是什么樣的接受效應?聽眾的感受如何?為什么有這樣的感受呢?
在這方面,同樣有相當數量的當事人(他們大多數是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一代,也有一些屬于20世紀4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一代,但很少有70后,絕沒有80后90后)留下了可貴的見證回憶。在葉匡政的筆下,鄧麗君“就像一個人們夜夜幽會的心靈情人”。類似的回憶還有很多,比如阿城:“我記得澳洲臺播臺灣的廣播連續劇《小城故事》,因為短波會飄移,所以大家幾臺收音機湊在一起,將飄移范圍占滿,于是總有一臺是聲音飽滿的。圍在草房里的男男女女,哭得呀。尤其是鄧麗君的歌聲一起,殺人的心都有。”今天的鄧麗君迷恐怕很難想象:聽了鄧麗君軟綿溫潤的“靡靡之音”,怎么會連“殺人的心”都有了?其實“殺人的心”在這里只是一個隱喻,喻指接受者那種騷動不安、無法自制的極端化情感,而不是真的要去殺人。民謠歌手周云蓬回憶道:“那時你聽那種歌,簡直是天籟!電臺信號本身不清楚,你就拿著收音機,變著方向聽。鄧麗君的聲音就從那里面傳出來。那時剛開始發育,身邊又沒有任何愛情歌曲,你一聽到鄧麗君這種甜蜜的、異性的聲音,真的是……音樂的震撼力,那個時候是最強的。”
這些回憶文字包含的信息是極為豐富的,值得認真解讀。對剛剛經歷“文革”浩劫的大陸年輕人而言,“敵臺”對于流行歌曲的傳播過程,同時是一個“人性復蘇”的啟蒙過程。正如王朔所言:“聽到鄧麗君的歌,毫不夸張地說,感到人性的一面在蘇醒,一種結了殼的東西被軟化和溶解。”王朔用“人性”這個詞可謂抓住了一代人感受的核心。這“人性”的內涵,既有精神成分,也有身體成分。因此,雖然葉匡政突出的是聽歌時的心靈感受(所謂“心靈情人”),周云蓬強調的是身體反應(所謂“異性的聲音”),但兩者在當時其實是分不開的,它們都包含了人性的內容。就是這種今天看來平常不過的“人性”,原先卻長期被“革命文化”冰封,以至于“結了殼”——卻又僵而未死,現在則被鄧麗君的“靡靡之音”喚醒、解凍了。
產生這種感受的一個關鍵因素,是與革命文藝、革命歌曲的對比: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其所代表的則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感結構和社會文化形態。因此,我們必須從兩種聲音、兩種文化的斗爭、博弈的語境,來理解鄧麗君和當時大眾文化所引發的接受震撼。對于從單一的“革命文化”(以樣板戲為典型)中長大的、時值20歲上下的青年人,聽鄧麗君的溫軟圓潤的流行歌曲真是如沐春風、醍醐灌頂,其震撼力、親切感難以言表。用張閎的話說,這是“只有在革命電影里的敵方電臺里出現過”的“曼妙歌聲”,它“讓一群青春年少的男生心醉神迷。”在此之前,這種聲音,“屬于國民黨女特務和十里洋場上墮落的歌女。”“文革結束之后,這種消失多年的聲音卷土重來,使我們這些前不久還是‘紅小兵’的人大為迷醉,不能自已。”作家孫盛起的回憶也是著眼于這種對比:“由于從小滿耳朵的樣板戲和‘紅歌’,而‘紅歌’大多是要吼的,所謂的‘鏗鏘有力’,所以鄧麗君那柔美的歌聲乍一在耳邊響起,我的心一下子就醉了。那對我來說無異于天籟之音!有生以來,我第一次知道:歌還可以這樣唱,詞還可以這樣寫!那種美妙醉心的感覺,真是用語言無法形容。”
除了人性復歸的震撼感和解放感,那時人們偷聽鄧麗君,還伴隨一種冒犯感、緊張感、危險感乃至犯罪感,它與震撼感、解放感、如沐春風感等一起,共同構成了一種我所稱的僭越的快感:一種震撼、解放、緊張、危險混合的感受。這既與他們接受的教育有關,也與當時的社會形勢有關。宗道一寫道:“像我這般年紀,又受過完整的傳統教育,當然清楚此曲的政治傾向。40 多年前,流寓中國的李香蘭(即山口淑子)唱的這首歌傳遍了燈紅酒綠的淪陷區。這位后來成了日本駐緬甸大使夫人的著名女歌星與女漢奸川島芳子(即金璧輝),同樣在我年輕的記憶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是,在夜幕籠罩的深夜,我束手無策。我根本不知道怎樣擺弄‘快進’‘暫停’之類的按鈕。手足無措的我只好無可奈何地任其‘毒害’我的靈魂。”但是很快,他的這種緊張、危險的感覺就煙消云散了:“隨著時間的悄悄流逝,我急促的呼吸終于歸于平緩。《小村之戀》《月亮代表我的心》《獨上西樓》……待到錄音機里流出那首優雅清新的《小城故事》,我緊繃的心弦已經完全松弛下來。”比受眾所接受的傳統教育更重要的是當時的懲罰政策。孫盛起回憶:“那天回家后,我坐立不安,吃完晚飯,就盼著父母早些休息。那時大陸以外的所有廣播,都是‘敵臺’,鄧麗君這境外傳來的聲音,當然屬被禁之列。我親眼目睹了有的學生因為穿著‘資產階級’的喇叭褲,被老師在校門口用剪子把喇叭褲剪成布條的慘狀,因此我絕不敢當著父母的面去聽那些‘靡靡之音’,怕他們把錄音機從樓上扔下去。”
這就是鄧麗君為代表的“靡靡之音”引發的接受心理效應。要理解這種效應,我們還需要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鄧麗君流行歌曲的傳播—接受是在雙重語境下進行的:一方面是大陸的改革開放、世俗化的進程剛剛開啟,許多禁忌還沒有完全沖破,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方興未艾;另一方面,當時的國際形勢、臺海形勢也依然緊張,冷戰沒有結束,兩岸的敵對宣傳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因此,收聽鄧麗君的歌曲是要冒極大風險的。離開了這樣的語境,王朔、阿城、孫盛起、宗道一等人描述的那種接受感受就是不可思議的,比如,我們很難想象當時大陸外的海外華人聽眾(包括香港臺灣地區和其他國家的),或者今天大陸的80后、90后聽眾,能夠在聽相同的鄧麗君歌曲時產生這種感受。
在今天看來,無論是情感層面的人性啟蒙,還是身體層面的性的覺醒,都屬于阿倫特所謂“私人領域”的事務。但是在當時,在一個從文革到后文革的特殊年代,私人情感的宣泄、私人領域的回歸卻與公共領域的重建、公民身份的重建同時進行,因此具有突出的公共性。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隨著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世俗化轉型,長久以來被壓抑的情感和世俗欲望,以一種反叛的姿態釋放出來,其中夾雜著改革開放初期人們重建世俗公共生活的憧憬,人的解放的準確含義是從1960年代極左的控制、從虛假的“主人公”幻覺中解脫出來,而對性、私、情等的肯定,正是它的內在組成部分。鄧麗君歌曲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飄洋過海而來,它積極參與了當時公民主體和新公共性的建構。只有這樣去認識,我們才能理解:私人的回歸具有公共的意義,情感的宣泄具有理性的維度。溫軟的靡靡之音具有驚人的解放力量。流行歌曲風行全國的時期正好也是大眾對公共事務的關注熱情空前高漲的時期,而那些被“靡靡之音”感動落淚的年輕人也絕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聽鄧麗君的自戀青年。
三、建構中國本土的大眾文化研究范式
改革開放初期大陸流行歌曲(當然也包括其他流行文化類型)的生產、傳播方式,以及受眾的接受經驗,都具有突出的地方性和時代性,因此也是最有中國特色的。它與西方、特別是法蘭克福文化批判理論所描述的大眾文化生產和傳播方式、受眾的接受經驗,都非常不同。
首先,對于發生在中國轉型時期的流行文化、對于它依托的社會歷史環境,應該有一種不同于西方的定位。法蘭克福大眾批判理論誕生于反思晚期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大環境中,它批判的是經濟、行政、文化高度集中統一的西方壟斷資本主義(阿多諾稱為“晚期資本主義”)時期的大眾文化(阿多諾更喜歡用“文化工業”這個概念),是他“試圖從商品、資本的層面對資本主義統治新格局首先解釋進而批判的一種嘗試。”在阿多諾的環境中,他所批判的大眾文化和傳媒工業已經被深刻地整合進資本主義的一體化經濟生產體系,“最有實力的廣播公司離不開電力公司,電影工業也離不開銀行,這就是整個領域的特點,對其各個分支機構來說,它們在經濟上也都是相互交織著。”大眾文化由此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獨立性和審美自主性,幾乎完全遵循資本主義的生產法則,比如商品拜物教、消費主義、批量化、一體化、模式化等等,大眾文化的所謂意識形態整合、控制功能(“社會水泥”)也是建立在這上面的。阿多諾說:“文化工業調劑出來的東西既不是幸福生活的向導,也不是有道德責任感的新藝術,而不過是要人們順從的訓誡,而這一切的幕后操縱者則是最為勢利的利益集團。”
問題恰恰在于,這個晚期資本主義統治的新格局,與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相去不啻十萬八千里,它顯然不適合用來分析當時中國大陸的大眾文化。由于歷史發展階段不同,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不同,所面對的政治文化權力格局不同,大眾文化及其所依托的文化市場化、世俗化、商業化轉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國所發揮的作用,完全不同于其在西方發揮的作用。掌握當時文化領域主導權力的,不是私營的文化市場,不是文化的商業化,不是娛樂文化,而是從1960年代延續下來的體制、文化和意識形態。當時中國根本沒有商業化、私有化、市場化的文化工業部門。無論是大眾文化還是催生大眾文化的世俗化、市場化、商品化浪潮,當時都還處于新生的、邊緣的地位,它們的出現和發展恰恰有助于走出極“左”體制和極左思想的陰影,沖破原有的計劃體制和文化禁欲主義,拓展文化的空間和生活方式的選擇。這就決定了以維護邊緣文化、肯定文化的僭越性的大眾文化研究,其批判性應該體現在對當時本土主導文化權力的反思和批判,應該針對并指向本土的主導文化權力,而不是盲目地跟隨西方的批判理論,把西方文化研究反市場化的立場移植到中國的文化研究上。
其次,由于阿多諾把大眾文化和大眾傳播定位為具有相同商業目的和經濟邏輯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工業體系的一個部門,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結構主導了整個體系——不僅主導了媒體的生產和傳播,而且主導了受眾(消費者)的意識和需要,于是出現了生產、傳播、文本、接受等各個環節的一體化、標準化、模式化。依據阿多諾的分析,連接受者的趣味、需要也是標準化的。“在今天,文化給一切事物都貼上了同樣的標簽,電影、廣播和雜志制造了一個系統。不僅各個部分之間能夠取得一致,各個部分在整體上也能夠取得一致。”“在壟斷下,所以大眾文化都是一致的。”就連大眾文化中出現的那些對于模式和一體化的偏離——各種似乎出乎意料的細節、插科打諢、玩笑,也都是生產者出于利潤需要預先設計、定制和配備好的。文化工業部門對不同的受眾進行分類統計,“消費者的統計數據經常可以在組織研究的圖標上反映出來,并根據收入狀況被分為不同的群體,分成紅色、綠色和藍色等區域”。于是產生了阿多諾所謂的大眾文化的“偽個性化”:“通過偽個性化,在標準化本身的基礎上賦予文化上的大量生產(cultural mass production)以自由選擇或開放市場的光環。可以說,走紅歌曲的標準化,其控制消費者的辦法是讓他們覺得好像是在為自己聽歌;就偽個性化而言,它控制消費者的手法是讓他們忘記自己所聽的歌曲被‘事先消化’(pre-digested)過了。”個性化或獨特性成為一種計劃之中的營銷策略。
在文化工業體系高度集約化、統一化的西方發達國家,這樣的描述和定位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把這些觀點運用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鄧麗君流行歌曲乃至整個大眾文化上,就脫離了發生時期中國大眾文化的發生語境和基本事實。如上所述,當代中國大眾文化最初是從海外走私進來的,而不是在本土生產的,也不是通過市場化的大眾傳播公司傳播的(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認為收聽“敵臺”和走私屬于集中化標準化的大眾文化傳播)。中國大陸本土完全沒有自己集約化的大眾文化生產和傳播部門(當時中國的文化生產和傳播單位,全部都是國家集中控制的事業單位,而且不生產大眾文化)。鄧麗君的流行歌曲在海外的生產即使是標準化、模式化的,但進入大陸語境之后,其傳播和接受環境也使其極大地去標準化。何況,阿多諾關于流行音樂標準化和偽個性化的判斷,參照的是現代主義藝術和高雅音樂(阿多諾本人就精通高雅音樂),但在鄧麗君剛剛流行的那個時代,標準化還是去標準化、個性化還是偽個性化,其參照對象恰恰是千篇一律的革命文化和革命歌曲,與這種真正模式化、標準化、千篇一律的革命歌曲相比,鄧麗君的流行音樂及其所代表的大眾文化,恰恰是高度個性化和反標準化的(這也是當時的青年人聽了之后感到震驚的原因)。可見,標準化還是去標準化、模式化還是去模式化,同樣取決于具體的語境。在西方是標準化的東西,在中國卻不一定是標準化的,相反可能是反標準化的。
再次,最讓人覺得與中國大陸發生期大眾的流行歌曲經驗格格不入的,是阿多諾對于流行音樂聽眾的接受經驗的分析。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大眾文化的傳播是高度計劃、自上而下的集中統一傳播,這個傳播過程也是一個控制大眾、欺騙大眾的過程,觀眾在接受過程中是被動的,其心理反應就是心不在焉。阿多諾的《論流行音樂》《論音樂中的拜物教特征與聽覺的退化》等文章,使用了“心神渙散”(distraction)、“漫不經心”(inattention)、“注意力分散/心不在焉”(deconcentration)來描述流行音樂聽眾的感知覺,這被認為是標準化的流行音樂所導致的聽覺退化(regression of listening)現象。流行音樂的聽眾“無法處于注意傾聽的緊張當中,便只好順從地向降臨在他們身上的東西投降。只要他們聽得心不在焉,他們就能與所聽的曲子平安相處”。對此,約翰·斯道雷這樣總結道:“消費流行音樂需要人們漫不經心和思想分散,而流行音樂消費又在消費者中產生漫不經心和思想分散的效果。”
這番描述與我們前面引述的王朔、孫盛起、王宏甲等人所回憶的初聽鄧麗君流行音樂時的感受,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依據這些當事人的回憶,鄧麗君流行歌曲所喚起的不但不是什么心神渙散、心不在焉,正好相反,那時的聽眾感受到的是無比的震撼、莫名的驚訝和深深的恐懼,以及這三者交織而產生的“觸電一般的感受”:既如沐春風又膽戰心驚。造成這種錯位的原因仍然是:阿多諾對流行音樂接受狀況的分析,是以嚴肅音樂為參照對象的;而中國聽眾聽流行音樂時是以千篇一律的革命歌曲為參照的。換言之,從鄧麗君流行歌曲的傳播和接受看,發生期中國大陸的受眾與大眾文化相遇方式與經驗感受與法蘭克福描述的正好相反:這是一種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的“不期而遇”——突然被“敵臺”廣播或朋友偶然獲得的錄音帶中的“靡靡之音”觸電般地“擊倒”,其所起到的不但不是麻痹大眾、控制大眾、整合大眾的“社會水泥”作用,而是解放其情感結構、融化其被階級斗爭冰封的心靈世界。
最后,即使在西方大眾文化和大眾傳播領域,法蘭克福學派和意識形態批判理論(認為大眾文化傳播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大眾的控制是徹底的和全盤的)也受到了極大質疑。比如,能動受眾理論的代表人物約翰·菲斯克指出,法蘭克福學派和20世紀70年代意識形態批判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這兩者都視觀眾為無力抵抗的群體”,徹底受制于文化工業生產者的操縱和文本權威的控制。菲斯克認為,“這種模式存在著與生俱來的弱點,它無法適應社會變遷的可能性,也無法使用除了在文化工業或文本面前無能為力的‘文化愚民’之外的大眾化理論。”針對法蘭克福學派的“整合”、伯明翰學派的“收編”概念,菲斯克提出了“外置”說。所謂外置,就是指社會文化系統中的被支配者從宰制性體制所提供的資源、商品和文化產品中,創造出屬于自己的意義(文化)。菲斯克寫道:“‘外置’是這樣一個過程:憑借它,被支配者可以從宰制性體制所提供的資源和商品中,創造出自己的文化,而這正是大眾文化的關鍵之處,因為在工業社會里,被支配者創造自己的亞文化時所能依賴的唯一源泉,便由支配他們的那一體制所提供。”“大眾文化必然是利用‘現成可用之物’的一種藝術。這意味著大眾文化的研究者不僅僅需要研究大眾文化從中得以形成的那些文化商品(菲斯克認為被支配者不可能自己創造這種商品,引注),還要研究人們使用這些商品的方式。后者往往要比前者更具創造性和多樣性。”這被菲斯克稱為“權且利用”的藝術(The art of making do)。菲斯克舉例子之一是牛仔服。牛仔服無疑是資本主義工業提供的統一化、模式化、標準化的商品,被統治者自己不能完全拒絕這種大眾文化產品(因為不掌握生產資料),但是她或他卻可以通過“權且利用”的藝術對牛仔服進行創造性使用(消費)(比如對無差別的牛仔服進行改型、撕裂和變形)。受眾當然也可以對某一個作品的主人公進行類似的改造,從而創造出自己的意義。也就是說,文化工業部門雖然能夠控制文化產品的生產環節,卻不能控制文本的使用、效果和意義的生產,意義的生產更關乎接受語境。菲斯克甚至舉了這樣的樣子:當美國生產的《豪門恩怨》在荷蘭播出時,其“美國性”在荷蘭所承載的“抵抗意義”“在美國本土是不可能有的”。“美國大眾文化商品的‘美國性’在其他民族國家中,常常被用來表達對社會宰制力量的抵抗。”這是因為“一種解讀,就好像一個文本,不可能自然而然在本質上就是抵抗式的或因循守舊的,是那些身處社會情境的讀者的用法,決定著它的政治涵義”。這是我目前為止看到的最接近我對發生期中國大眾文化特點和功能的看法。
但是,菲斯克的理論盡管因其看到了受眾和接受的復雜性、主動性和反抗性而能給我們以極大啟示,但卻同樣不能照搬到中國發生期的大眾文化身上。這是因為,菲斯克認定被支配者創造自己的大眾文化時所能依賴的唯一源泉,是由支配他們的那個體制提供的,他所能做的只是對文化工業提供的產品進行創造性利用。然而,發生期中國流行音樂卻不是在中國大陸本土生產的,當時中國文化和工業部門根本不生產鄧麗君流行歌曲這個意義上的大眾文化。后者是從港臺地區生產(有些則是20世紀30年代國統區的老歌)、通過敵臺或走私傳播到大陸的,而且,當時大陸的受眾在接受這些流行文化時并沒有對之進行撕裂、改型、改造,也沒有感到有這種“再創造”的必要,因為比之于集中統一生產和傳播的革命歌曲,它們本身已經是充滿了新穎性、顛覆性、叛逆性的青年亞文化,根本沒有必要進行改造才能顯示其顛覆性和叛逆性。而與荷蘭的情況不同的是:荷蘭的大眾是用美國生產的《豪門恩怨》來抵抗和顛覆美國的宰制性權力(因此屬于民族主義范疇),而中國大陸當時的大眾則是利用港臺地區的大眾文化在抵抗和顛覆本土的宰制性權力。這個重要差別不可不察。
行文至此,我想我已經充分證明:無論是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還是菲斯克的能動觀眾理論,與發生時期中國大眾文化經驗之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錯位。離開對于大眾文化的在地化的發生學考察,結果往往是也只能是對西方文化批判理論的機械套用。這樣,回到歷史現場對中國大眾文化進行發生學研究,不僅僅是一種經驗研究,它同樣具有不可小覷的理論意義。通過對這類中國式大眾文化現象的研究,或許能夠建構一種適合中國國情、能充分展現中國大眾文化特殊性的本土范式,這種研究既能與西方的文化研究進行有效對話,又能充分關注到大眾文化的本土性。
注釋:
① 葉匡政:《白天聽老鄧,夜里聽小鄧》,http://mail.cponline.gov.cn/2017/12/01/,2017年12月1日。
② 已經很難確定鄧麗君流行歌曲最初進入中國大陸的確切時間。目前能夠見到的說法基本上是一些私人回憶錄。一個網友寫于2005年的文章說:“大約三十年前”(也就是1975年),作為知青的他在農場通過澳洲廣播電臺偷聽到鄧麗君的《在水一方》(霜冷長河:《一水隔天涯——鄧麗君逝世十周年祭》,見趙勇、祝欣:《鄧麗君、流行歌曲與20世紀80年代的批判話語》,《文化與文化》,2014年第1期)。這是筆者見到的關于聽鄧麗君流行歌曲傳入大陸的最早記錄,但作者并不明確和肯定(“大約”)。李皖坦言:“對不同的人來說,這一天(聽到鄧麗君的歌曲,引注)的具體日期各不相同”,但緊接著補充“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它一定出現在1978、1979年的某一個夜晚。”(見李皖:《鄧麗君與靡靡之音》)。同樣帶有推斷的成分。《鄧麗君畫傳》作者師永剛的說法是:1979年初,各大都市的報攤出現了鄧麗君的照片,南方城市有些地方把鄧麗君的音樂磁帶作為必備嫁妝。幾乎凡是有收錄機的地方都有鄧麗君歌曲,包括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到處都能聽到鄧麗君的歌聲”。(見《永遠的鄧麗君》,《文史博覽》,2005年第11期)。照這個說法,1979年初鄧麗君已經成為大眾偶像。
③ 葉匡政:《白天聽老鄧,夜里聽小鄧》,http://mail.cponline.gov.cn/2017/12/01/ 。所謂“央廣”,應為臺灣地區的“中央廣播電臺”,其源頭可以追溯到1928年成立于南京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廣播無線電臺”(簡稱“中央廣播電臺”或“央廣”),隸屬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之后,“央廣”曾多次改名、遷移,改變隸屬單位、組織性質和名稱。更準確說,葉匡政文章中說的“央廣”,應為1951年開始對中國大陸播出的“中央廣播電臺—自由中國之聲”,每天播出6個小時。“央廣”是什么時候開始播出鄧麗君歌曲的?可以參照馬多思的回憶:“1979 年開始,臺灣‘中央廣播電臺’開辟對大陸聽眾廣播的《鄧麗君時間》節目,這個節目每周播出6 次,每次25 分鐘。1995 年鄧麗君去世后,節目才停播。這樣的播出方式有政治因素,只不過是柔性的政治宣傳手段。”“當時,臺灣對大陸的‘自由中國之聲’廣播政治性很強,但為了吸引大陸聽眾,電臺設置了很多音樂元素。除了晚上6 點播放的《為您歌唱》欄目,每個整點的節目開頭也都要播放10 分鐘的歌曲,很多都是鄧麗君的,還有鳳飛飛和劉文正的。”這里“中央廣播電臺”所指與葉匡政說的“央廣”應該是同一個電臺。參見馬多思:《偷聽鄧麗君的日子》,《文史博覽》,2013年第11期。這篇文章對當時偷聽敵臺的情況記述比較詳細。
④ 馬多思:《偷聽鄧麗君的日子》,《文史博覽》,2013年第11期。
⑤ 宗道一:《聽鄧麗君的年代》,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2512af0100i30o.html。
⑦ 粵發[1981]5號,廣州市國家檔案館,全宗號3.4,1981年第5號,總第201號。
⑧ 這些歌曲其實談不上“色情、低級”,比如《瘋狂的周末》(鄧麗君演唱)的歌詞是:“禮拜一大家起身太早,禮拜二生意買賣太好,禮拜三偷偷摸摸打電話,哈羅達令給支票。禮拜四整天伸著懶腰,禮拜五看場電影吃過飽,禮拜六下午跑馬贏了錢,再排節目玩通宵,酒醉三份興致好,隨著音樂搖又擺。恰恰恰rock and roll,越瘋狂越是美妙,你不妨自由自在逍遙,不妨痛痛快快歡笑,享受這瘋狂過來的好時光,明天禮拜天再睡覺。”
⑨ 穗革發[1980]164號,廣州市國家檔案館,全宗號146一九八O年第3號,總號第56號。
⑩ 參見廣州市文化局1982年3月13日發布《貫徹粵府[1981]248號文情況的報告》,穗文化(82)27號,全宗號97,一九八二年第51號總號第30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