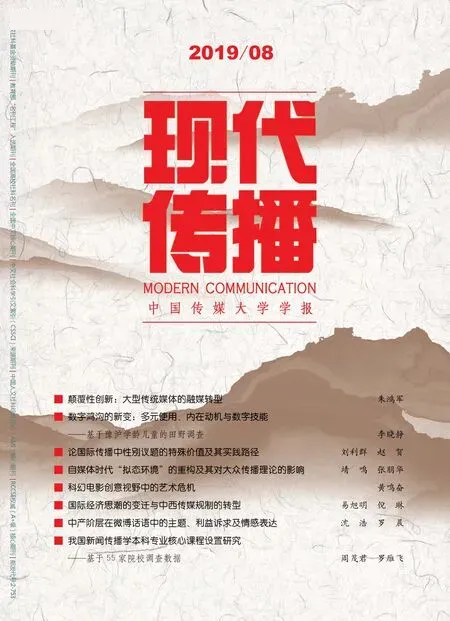版權可以拯救新聞業嗎:歷史上的新聞版權之爭*
■ 許永超 陳俊峰
版權即復制權,保護藝術家、出版商或其他所有者免受對其作品未經授權的使用,以確保其對作品使用的控制并從中獲得部分收益的權利,屬知識產權之一部,后者還包括專利、商標等。①現代版權觀念是隨著古登堡金屬活字印刷而來的。世界歷史上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版權法即英國1710年安娜女王法,即處理書商和作者關系的,并不明確涉及新聞和新聞業。新聞業版權爭議主要是伴隨電報出現而出現的。當然本文并不試圖從版權法的角度回答這一問題,而是從歷史的角度說明,尋求新聞版權借以保護新聞業似乎并不樂觀。宋建武先生在論文中曾說:“在過去的180多年中,從1833年第一份大眾化報刊《太陽報》誕生開始,不僅在中國,即使在世界范圍內,對于新聞的轉載,基本沒有產生過較大爭議”。②但實際上,無論是在英美,還是在歐陸,因為電報這種“新技術”的出現,都曾發生過激烈的關于新聞版權的爭議。本文試圖探討以下問題:新技術在新聞版權保護觀念發展史上起到什么影響?歷史上的新聞版權有何爭議?對今天又有何啟示和教訓?
一、新聞版權觀念的歷史來由
1.電報與新聞版權觀念的出現
作為歷史上的新技術,電報對新聞生產、傳播、消費的影響,對新聞業產生的變革作用,與互聯網類似,也最早引發了大規模有關新聞版權的爭論。
電報出現之前,并無新聞版權的觀念。報紙之間相互轉載新聞是一種習慣。19世紀上半葉,美國各地報紙主要通過轉載來收集新聞。一些在大城市有良好基礎的報紙往往與外地上百家報紙相聯系。政府也支持這種慣例,一直到1873年,郵局未向報紙收取任何費用。這甚至可以追溯到本杰明·富蘭克林和威廉·亨特任郵政局長的1785年所頒布的法令。1792年美國國會將此寫進法律:“每一個印刷商都可以將自己的報紙寄給美國任意一份報紙,不收郵費。”③
在大城市,相對外地報紙,本地報紙擁有“首發”優勢,即使是同城報紙相互競爭,因為當時的技術條件,時間延滯也會有幾個小時,甚至是一天。所以當時的報紙雖然都十分強調第一時間,但并不畏懼轉載。如霍勒斯·格里歷說:“搶到最早新聞的報紙很快就會出名,誰都希望自己的報紙在早餐前送到,這樣人們就可以邊吃早餐邊看報。但是即使有報紙將我們的新聞拿去,也不會造成什么影響,因為排版、印刷需要時間。”④
但是1840年代中電報的出現打破了這種時間延滯以及地方性。電報使復制和傳遞新聞輕而易舉。隨之而來的是對轉載新聞這一習慣的質疑。如Bently所說:“毫無疑問,因為電報能夠將倫敦報紙上的新聞在倫敦報紙抵達小城之前送達”。⑤除此之外,電報還滲透到新聞消費環節。比如電報公司設立的“新聞閱讀室”(news room)(類似閱報欄,不過是封閉的),“任何信息一經刊登,立即被電報公司發往各地。電報公司只需購買一份泰晤士報,然后將上面的消息送往各地,公司不需要為此承擔任何責任,只需要聲明,消息來源于泰晤士報、郵報、先驅報。這些十分有價值的信息是公眾急需并想要獲知的”。⑥這與今天互聯網打破時空界限并帶來全新的新聞消費模式何其相似。
通訊社的到來更加劇了新聞版權觀念。因為通訊社的出現,新的信息收集分發模式,即一種更加中心化,控制更嚴格的秩序開始形成。通訊社以賣新聞為業,禁止會員向非會員分享信息。但許多報社仍試圖利用電報無償使用電訊,比如因為時差的原因,美國部分西部報紙退訂美聯社電訊,其駐在紐約等東部城市的記者將美聯社電訊用電報發回西部報社。⑦
2.新聞商業化革命的背景
新聞業的商業化革命,即新聞業從政黨報向商業化報紙、大眾化報紙的轉變,是新聞版權觀念出現的背景。
政黨報沒有版權觀念。因為首先政黨報以宣傳為宗旨,它渴望的正是自己的新聞、評論被大規模復制和傳播;其次政黨報以政黨津貼或政黨選舉勝利后承包給印刷商的印刷合同,來維持正常運轉,“上至總統,下到鎮議會的負責人,都可以把打印合約和辦公文件的生意包給報社,借此增加報紙收入”。政黨成員還以隨筆、信件和其他新聞稿件的形式支持報社⑧。因此政黨報很少有商業觀念、版權觀念。
但是19世紀30年代以后,美國便士報革命,迅速擴展至英國、法國乃至整個歐陸。⑨新聞相對政治獨立,依靠大發行量吸引廣告來維持生存,不再依靠訂報費和政黨補助,新聞逐漸成為報紙的重心。便士報不再坐等報道常態新聞,而是去尋找新聞。各報開始紛紛雇傭記者……直到便士報出現,報紙才變成銷售給一般讀者的商品。19世紀前葉,越來越多的報紙開始努力提高時效,特別是船抵信息。便士報使新聞變成為一種市場化的產品,其特性可以進行量化。電報以及通訊社出現以后,新聞作為商品的觀念更加深入人心。因為通訊社本身就以出售新聞為生。
新聞競爭加劇,以至于如凱瑞所說“簡約的文筆和精簡的篇幅使得新聞——實際上是迫使新聞——被當做商品一樣對待,一種甚至會受到偷竊的制約。”“偷竊”正是因為電報的出現引起的。如果沒有電報的出現,沒有新聞商業化革命的背景,那么就不會有新聞版權觀念,即保護自己的新聞不被人無償使用。
二、英、澳、美、法的新聞版權爭論
歷史上部分新聞業為爭取版權保護的努力,曾如同今日一樣熱烈。英國出現新聞版權爭議最早,起于1830年代。它產生于英國政府關于廢除印花稅法案的討論。
印花稅雖不利于印刷業發展,但客觀上卻起到保護大報免受競爭的作用,所以廢除印花稅遭到許多大報的反對。他們要求在廢除印花稅之前,確立新聞版權法來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擔心一旦印花稅廢除,會涌現出大量的便士報,甚至半便士報,不僅沖擊原有的報業秩序,而且會“抄襲”他們的新聞。1851年Henry Rich在報告中認為:“大報特別是倫敦的日報,為公眾收集和報道有價值的信息,耗費巨資,如果印花稅廢除,有理由相信大量半便士報將會涌現,抄襲這些我們耗費巨大收集的信息。所以我們建議以某種短時間內的版權保護之。”這份報告在委員會中以6-3通過,英國曾距離新聞版權立法只一步之遙。
澳大利亞則是較早也是英、澳、美、法中是唯一一個通過立法保護電訊的。早在19世紀下半葉,澳大利亞各個殖民地曾分別立法保護電訊的獨享權。這些立法在當時是專門為應對新媒介形式即電報的出現所產生的。因為國際電報線路的鋪設,澳大利亞報紙上的國際新聞幾乎全部來自路透社。當時以墨爾本Argus報和悉尼先驅晨報為首的澳大利亞報業協會獲得使用路透社電訊的獨享權。從倫敦到澳大利亞的電報費用很高,占到當時報紙開銷的最大部分。所以出于對這些電訊的保護,報協游說政府立法,規定在電訊刊出24-72小時之內的獨享權。他們部分獲得了成功,在澳大利亞幾個殖民地成功立法,如維多利亞,1871年立法;南澳大利亞,1872年;塔斯馬尼亞,1891年;西澳大利亞,1895年。此后澳大利亞還產生了許多有利于保護電訊的判例。盡管遭到地方報紙的激烈反對,這些法律到1905年一直有效。
再來看法國,乃至歐陸的情況。這部分材料主要來自ICP(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ress)大會的討論。其源起是1886年《伯爾尼公約》版權保護將新聞排除在外,引起大會不滿,所以連續幾屆大會上新聞版權保護都是作為大會主要議題加以討論的。Beradi在1894年安特衛普報業大會上提請伯爾尼公約以及其他立法者注意,無論是讀者還是新聞業都已發生了變化,“如今的讀者想要的并不是享受文章的文學形式,而是盡可能快的知道最新、最準確的消息——新聞。”他認為獨家新聞應該受到保護,并建議擴大版權保護至電訊(telegraph),保證用戶在一定時間內的獨享權。他認為一位著名作家的死和一個關于他臨終時的詳細描述,前者是事實無版權,而后者則是一個記者的作品,應當得到保護。在1897年Stockhom大會上,巴特拉也說過一段類似的話:“今天我們必須認識到,新聞業盡管也捍衛或宣傳特定的觀點,但已成為一項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的產業。今天報紙的天職是盡可能迅速的讓公眾知曉最新的信息。報紙不惜耗費巨資,盡心竭力收集信息,為的是公眾能夠獲得迅速準確的消息。所以對于一份報紙的業主而言,最重要的是他所刊的文章受到尊重,其他期刊不要竊取它并爭奪他的讀者”。
在美國,幾乎與ICP大會的討論同時,從19世紀80年代起,美聯社因為新聞電訊的使用問題不斷卷入與各地報紙的糾紛。1883年底,美聯社派亨瑞·沃特森到華盛頓國會游說,尋求通過一法案賦予報紙上所刊登的文章短時間的保護。但是立法風聲一出,便遭到激烈反對。在寫給國會的請愿信中,至少有60份是反對的,只有一份支持,最后,尋求立法保護新聞版權的努力失敗了。但沃特森被派駐華盛頓時,一位非常有經驗的律師曾告訴他,其實他們未必一定要通過立法保護新聞,也可以通過普通法,歷史上至少有4-5則有利于保護新聞的判例。后來西部聯合社訴全國電訊新聞社的案子中,后者通過收報機(ticker tape)照搬前者的電訊,并以低于競爭者的價格在自己的網絡中分發。全國電訊新聞社以西部聯合社的新聞并未注冊,因此不能享受版權法保護。但西部聯社出于戰略考慮,轉而竟宣稱新聞并無版權,注冊無法應用于新聞,然后轉而尋求普通法保護。法官支持了西部聯合社的訴求,美國聯邦法院第一次得出結論,基于原創性的觀點,新聞僅僅是“記錄”無法獲得版權,但表達新聞的字句、方式可以受到保護。一直到1918年美聯社訴國際新聞社的判例提出“熱點新聞盜用”的原則,法院才通過不正當競爭法承認了新聞的部分版權或類版權。
三、反對新聞版權立法的結果及原因
以上各國爭取新聞版權立法,除了澳大利亞外,全部以失敗告終。到最后各國不約而同采取“不正當競爭法”的方式適度保護新聞的“類版權”。
我們發現無論是在哪一個國家,爭取新聞版權保護最力者均是主要的新聞生產者,無論是倫敦、巴黎的大報,還是美聯社、西部聯合社。所以立法保護新聞版權的提案一經提出,就遭到地方小報、晚報(在美國還有西部報紙)的激烈反對。他們反對的理由,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一,新聞不同于文學、藝術,往往被認為缺乏創造性,是“冬蟲”“僅有一天的壽命”。甚至認為新聞無所謂作者,新聞得自街談巷議,新聞是事實、歷史,并非記者創造。第二,出于公共性的考慮。最突出的是法國。而英美則引到了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上,認為新聞版權將造成一種壓抑的氛圍,因此無論是對個人還是社會都是不利的。第三,賦予新聞版權不可行。即使同情新聞行業,但是新聞和其他事實性作品,如地圖、黃頁、航海圖等不同,它是敘事性的,因此容易被復制、模仿,任何編輯都可以通過復述的方式逃避責任。所以英國議員最后拒絕立法時說,如果真的立法,那么法官將面臨無休止的訴訟,如何判定侵權,甚至任何主編都有可能站在被告席上。
但是英國、美國、法國,甚至是立法的澳大利亞,因為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關于新聞版權立法并不是鐵板一塊,雖然都遭到了各種反對,但仍有具體差異。
在美聯社的案例中,可以看出美國文化的兩種價值觀。首先,反對新聞版權更強調原創性的觀點,這源于個人主義的影響;其次,美聯社尋求立法失敗,反映出美國小田園主義的價值觀,害怕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美聯社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尋求立法,卻威脅到了各地報紙的利益。其中最顯著的是小城鎮報紙。19世紀90年代美國所有報紙期刊總和大約在1.5到1.6萬之間,大多數是地方性報紙。地方報被諷刺“其編輯的剪刀也許比他們的筆更加重要”。所以新聞版權立法遭到了地方報紙的激烈反對。《紐瓦克日報》認為“法案將會導致壟斷,小城鎮的讀者將不得不仰賴于大城市各報,因為家鄉的報紙將會垮掉。”一位來自《伊麗莎白日報》的編輯則說:“通過這樣的法案,結果將是新澤西本地媒體的消失,使當地人完全依賴紐約和費城的報紙的恩惠。而他們對當地的福利并不關心,因此也就不會留有空間討論當地事務。”
法國反對新聞版權立法的理由似乎更強調新聞的公共性。這與法國商業報紙發展滯后,以及更加強大的政治平行性以及文學性傳統有關。法國報紙與政黨、各個利益團體有密切聯系,如天主教、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等。法國不認為新聞業是單純的商業,相反是最重要的理性捍衛者,是一個政黨的旗幟,觀點的宣傳者。一個代表天主教和君主制利益的地方報紙代表說:“從新聞發表的那一刻起,它就進入了公共領域,想要限制新聞的發表,就如同限制空氣或陽光一樣虛妄”。地方報紙轉載巴黎報紙上的新聞已成為一種習慣,他們將這種習慣比喻為像“各報之間的貸款”一樣正常。就連當時的巴黎《時報》經理阿德恩·赫伯德都反對說:“新聞(simple and pure news)不應獲得和文學作品一樣的保護,但應給出來源,并譴責大量的轉載,不會贏得尊重”。
法國報業有著文學性的傳統。法國報社的許多從業者本身就是文學家,或者許多記者以成為作家為目標,法國報紙上以述評、辯論性文章和評論為主,而不是新聞。他們認為“文學是永恒的,新聞僅僅持續一天”。強大的文學性傳統使法國新聞業輕視新聞,因此也不會像英美新聞業那樣熱衷于新聞版權保護。到1869年,在法國記者仍被描述為一直尋找新聞的人、問太多問題的人,含有負面意義。20世紀70年代,法國的報刊才開始雇傭記者。1888年法國小說家、記者左拉,表達了他的不安:“不受控制的信息流達至極端,已改變了新聞業,殺死了討論性的偉大文章,殺死了文學批評,而越來越重視電訊瑣碎的新聞和記者、采訪者的文章”。
英國反對新聞版權立法則表現出更加實用主義的特點。他們最后考慮更多的是新聞版權在實踐上的困難。第一,他們最后傾向認為新聞版權立法并不必要。有議員強調廢除印花稅并不會因此出現大量盜版,即使有,其危害也不會像想的那么大,因為像《泰晤士報》這樣的報紙并不會因此受到影響,靠抄襲的報紙并不會成功,摘編的文章無法完全取代原文;第二,如果立法保護新聞版權,將會造成一種壓抑的氛圍,甚至限制新聞的流通,會給公眾造成損失。任何一個主編都有可能因卷入版權糾紛而站在法官面前;第三,新聞不同于受版權保護的其他作品。
所以各國經過激烈爭論,到最后大多未能以成文法的形式賦予新聞版權保護,因為確實存在太多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困難。最大的挑戰應該是公共性,因為關于公共性的考量,深埋在版權法的基因當中。歷史上第一部版權法即安娜女王法開創先例,將版權保護限制在一定時間內,過了時限,即進入公共領域。加上新聞業的特殊性,與公共利益、政治、社會密切相關。所以最后大家轉而以一種“不正當競爭”的方式處理新聞版權問題。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實現保護新聞業與公共利益的平衡,它將版權法形式/內容的原則應用在新聞上,形式上即禁止大規模復制新聞以保護新聞業,但是同時在內容上,以新聞事實無版權,來保證關于新聞的合理使用。
四、結語
19世紀中后期,在新聞業商業革命的背景下,電報作為一種“觸媒”,促使有關新聞版權的討論在世界各地出現。但是技術僅僅是觸媒,決定新聞是否應該受版權保護的,最終是特定的歷史社會條件下,新聞業和整個社會利益的均衡過程。我們注意到,尋求新聞版權保護的主要是新聞內容的主要生產者。在新聞業與整個社會利益均衡過程中,新聞及新聞業的獨特性始終讓人們懷疑保護新聞的正當性和可行性。
盡管歷史告訴我們尋求立法保護新聞很難,但絕不是說新聞不應該尋求保護。從歷史上看,無論版權法(其中關于創造性觀點)還是新聞業自身都是隨著歷史不斷發生變化。版權法及司法過程應顧及新技術如互聯網沖擊對傳統新聞業的影響。特別是關于新聞的觀念,早已不再是19世紀那樣的“以事實為中心”。今日報紙上有大量的特稿、調查性報道,如不加以區別保護,將不能鼓勵媒體繼續投入,由此將造成新聞內容的枯竭。實際上這一點對今天的新聞業來說是越來越真切的。技術話語不應成為一種“托詞”,技術的影響是客觀的,但技術影響的偏向是必須考慮的,“不做新聞,只做新聞的搬運工”,因此造成傳統媒體收入的急劇下降,在此種情境下,我們有理由相信成本高昂的新聞,特別是調查報道,可能會最先消失。這恐怕是連那些主張新聞公共性而因此反對保護新聞的人都不愿意見到的。所以我們無法說新聞版權一定不可能,我們更愿意說,在新技術的環境下,探索一種新聞業和整個社會利益的新的均衡,是有意義的。但是話說回來,媒體也不應該完全寄希望于借版權保護自己,陷自己于被動,只有努力求新求變,與新媒體融合,不斷探索,才是解決目前困境的方向和出路。
注釋:
① 版權與著作權,保羅·戈斯汀稱版權是一種財產權,英美法系國家未將其視作自然權利,而是鼓勵作者創作作品的公共政策產物。著作權主要是以作者為中心的人身權,即精神、人格權(moral right),包括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以及保護作品完整等權利。在本文語境中,更多是一種復制權、財產權。參見美保羅·戈斯汀:《著作權之道:從古登堡到數字點播機》,金海軍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版,第139頁。
② 宋建武:《新聞版權即新聞獲利權——兼論以數據庫版權解決新聞版權問題的可能性》,《現代傳播》,2017年第11期。
③ Richard B.Kielbowicz.NewsGatheringbyMailintheAgeoftheTelegraph:AdaptingtotheNewTechnology.Technology and Culture,vol.28,no.1,1987.pp.26-41.
④ Frederic Hudson.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from1690-1872.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873,p.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