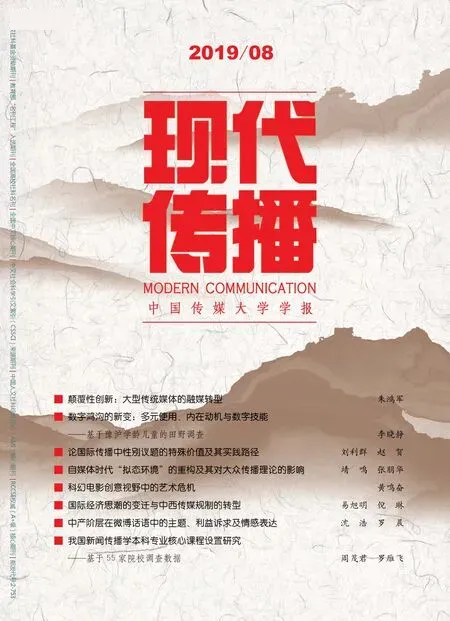營造“共同體”意識:論主流媒體話語調適的轉向*
——基于電視文化類節目的思考
■ 吳 雁 袁 瀚
一、問題的提出
當前我國主流媒體的話語輸出和傳播效果存在著困境,制約著主流文化在不同社會群體間的融入。一方面,主流媒體固有的單向式話語傳播力不佳,無法有效地融入民間輿論場。中心式話語過分強調、肯定、認同官方立場,采取灌輸的傳播模式讓公眾容易對政治傳播產生疏離感、厭惡感,不利于執政黨話語體系下沉。①同時,多元社會思潮的傳播,消解我國官方的議程設置。自媒體的崛起、不同群體的意見表達導致正確與錯誤的思潮并存,“眾聲喧嘩”的傳播環境對主流媒體話語權造成一定的沖擊。
另一方面,主流媒體的話語模式存在著娛樂化凸顯、消費主義日益泛濫的趨勢。隨著我國主流媒體市場化進程加快,在資本邏輯的推動下,媒介話語向市場和利潤“獻媚”,呈現出教育意義讓位于商業屬性的缺失。法國學者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認為:“今天享受不再是權利或樂趣的約束機制,而是公民義務的約束機制……消費者把自己看作是處于娛樂之前的人,看做是一種享受和滿足的事業。”②主流媒體為了迎合社會大眾的感官滿足,導致選秀、競技、明星生活等各類娛樂真人秀節目充斥于大眾的視野,而社教類節目因模式固化、趣味不足等原因逐步離場。過度娛樂化的媒介話語稀釋了主流價值觀的政治傳播效果。
主流媒體的話語困境推動其在新的社會環境和媒介語境下進行話語調適,重新獲得文化領導權。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話語即權力,話語與權力二者相輔相成、密不可分。“話語”是權力的外衣,只有依賴于“話語”才能實現真正的權力。權力并不僅僅局限于統治階層或者執政黨所掌握的強制力、征服力,而更多地指影響力、輻射力、說服力。③換言之,公眾對于權力的認同和信任有賴于話語體系的致效。執政黨、政府通過政治傳播,使信息在共同體范圍內擴散,溝通官方與民間的立場,使權力與執掌權力的代表具備合法性。在社會矛盾日益加劇的情況下,主流媒體需要進行話語轉型,突破固有的話語體系的局限,在堅守核心價值觀的前提下采取社會公眾喜聞樂見的話語模式進行輿論引導和價值引領,以實現緩和社會矛盾和增強民族認同感的媒介功效。
二、電視文化節目中的話語轉型
央視及地方衛視作為執政黨價值傳播的載體,承擔主流文化輸出和傳播的功能。文化類節目作為國民教育的重要手段,從發軔伊始就印上了全面而深刻的文化教育意識。④目前國內學者對電視文化類節目的定義、功能眾說紛紜,尚未形成一個明確、清晰的概念,但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定的共識,即電視文化節目“以傳承文明、宣傳知識、教育大眾為己任”⑤。一方面,電視文化節目具有社會教育意義,需要借助優秀文化進行價值引領、道德規范,從而影響社會公眾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另一方面,由于電視文化節目面向全體社會成員,因此在節目制作、編排中需要采取“大眾化”路線,利用符合大眾審美心理和媒介消費習慣的節目語態,推動主流文化在不同群體的融入與致效。
電視文化節目具備教育性和大眾性,既承載了媒介的價值導向功能,又覆蓋了廣泛的受眾人群,是執政黨和主流媒體話語傳播的有效載體。近年來主流電視媒體積極在文化類節目上發力,提升主流價值觀和主流社會文化的傳播力、影響力、鮮活性。《朗讀者》《見字如面》《中國詩詞大會》《國家寶藏》《信·中國》《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等文化類節目蔚然成風、百花齊放,在社會上取得了不俗的傳播效果。以《朗讀者》為例,該系列節目是央視推出的中外文學作品朗讀節目,一開播就成為新媒體傳播的“現象級”節目,掀起社會的“朗讀熱”。⑥《見字如面》是全國首檔書信朗讀節目,挑選中外名人的信件,運用獨特的電視話語展現書信中的人物內涵,彰顯時代價值;《信·中國》則是對《見字如面》的繼承與發展,將執政黨建黨以來收錄的黨員書信作為文本來源,挑選出其中的一部分加以呈現,旨在傳遞執政黨的文化與價值。⑦
縱觀近年熱播的《朗讀者》《見字如面》《中國詩詞大會》《國家寶藏》《信·中國》等電視文化類節目,可以發現這些節目呈現一個大趨勢:基于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在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傳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電視媒介話語中營造民族共同體。美國社會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民族國家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通過小說、報紙等印刷傳播媒介在不同社會人群間喚起“共同體”意識。安德森指出:“報紙創造了一個超乎尋常的群眾儀式:對于作為小說的報紙幾乎分秒不差地同時消費(‘想象’)……報紙的讀者們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樣的報紙也同樣在地鐵、理發廳或者鄰居處被消費時,更是持續地確信那個想象的世界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見……創造出人們對一個匿名的共同體不尋常的信心,而這就是現代民族的正字商標。”⑧電視文化類節目作為大眾傳播媒介,挖掘并呈現優秀中華文化內涵,并創新敘事模式、傳播語態,使觀眾參與到觀看的過程中,激發文化認同意識和民族身份認同意識,從而提高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具體而言,主流媒體話語調適的電視文化傳播路徑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立足民族文化,展現民族特色。美國人類學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提出:“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為歷史的產物,其特性決定于各民族的社會環境和地理環境”⑨。一個民族的歷史運行軌跡和社會發展模式決定了其特殊的文化模式。反之,文化是不同民族和社會形態分野的標志,民族文化、民族符號折射出獨特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自然環境和人文社會。
近年熱播的電視文化節目,內容大部分來自中華民族文化。依據筆者對《朗讀者》(第二季)中的演說文本進行的統計,其中超過六成的文本來源于中國古今的文學作品;《見字如面》(第二季)的演說文本超過八成來自中國大陸的作者所撰寫的書信;《信·中國》的演講書信來源則全部都是中國共產黨員的信件。誦讀類節目選取優質的中華媒介文本,呈現華夏民族不同時期的時代內涵,并通過演說者與主持人之間的話語互動進行情感抒發與價值傳遞,實現文化育人的傳播效果。《國家寶藏》作為一檔文博類節目,通過展現故宮博物院等九家國家級重點博物館的歷史文物及其背后的前世今生進行民族文化科普,讓社會公眾了解文物所承載的文明和中華文化薪火相傳的精神內核,提升民族文化自豪感。《中國詩詞大會》取材源自中國古代詩詞歌賦的精粹,融合了競技對抗的敘事模式,實現了中華優秀古典文化的全民普及。電視文化類節目展現優秀民族文化,利用全民族共同的文化瑰寶有機地聯結“分散的”“孤立的”“異質的”社會大眾,維系民族共同體。正如法國哲學家列維-布留爾(Lucien Lévy-Bruhl)所言:“它們在該集體中的每個成員身上留下深刻烙印,同時,根據不同情況,引起該集體中每個成員對有關客體產生尊敬、恐懼、崇拜等感情。”⑩
第二,凸顯民族身份,彰顯民族認同。國家是包含了政治制度、歷史文化、民族血緣的共同體,因此國家認同感的構建有賴于在政治、文化和民族三個層面進行。其中,政治認同指認同國家的基本制度、社會發展道路和國家方針政策;文化認同指認同國家的歷史底蘊、燦爛文明、大好河山;民族認同指認同各族人民共屬一體的國民心理。觀之近年熱播的文化類節目,在傳播社會主流文化的過程中較少“直抒胸臆”地宣傳我國社會道路、發展方向、政策方針的先進性和正確性,更多的是倡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成員”意識,即每個社會成員同屬于民族共同體,華夏兒女是大家的共同身份,在“統一”身份中提升民族認同感。美國學者M萊恩·布魯納(M.Lane Bruner)認為:“國家認同不僅僅是一種或者一套隨后將促進一系列行動并且證明這些行動合理性的敘述,它也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修辭過程。相應地,在此所采用的修辭方法不是為了發現一個國家的認同,而是用以分析那些碰撞的時刻,也就是相互競爭的闡述在有關想象中作為國家的一名成員意味著什么的持續的話語協商過程中產生碰撞的時刻”。借助萊恩的觀點,我們可以發現,電視文化節目除了對國家與執政黨的認同與歌頌,更多地趨向讓社會公眾清晰地認識到自己屬于中華民族,明確民族身份,并認識到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以樹立起民族共同體意識。
最典型的體現在《信·中國》這檔節目上。該節目選取的是中國共產黨員的信件,但是仔細閱讀這些信件可以發現,節目主題不會局限在歌頌執政黨,而是借助革命與建設的時代背景,展示共產黨員對自己華夏兒女身份的深切認同,倡導一種民族身份歸屬的意識。比如開國元勛聶榮臻斥責日本侵略者的信件中,是這樣寫的:“我八路軍本國際主義之精神,至仁至義,有始有終,必當為中華民族之生存,與人類之永久和平而奮斗到底,必當與野蠻橫暴之日閥血戰到底。”這實際上就突破了單一的執政黨視角的局限,轉而呈現了對民族命運的重視與人類和平的呼吁。
第三,倡導民族責任,實現國民教育。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在《單向度的人》一書中提出,在發達工業社會,“公共運輸和通訊工具,衣、食、住的各種商品,令人著迷的新聞娛樂產品,這一切帶來的都是固定的態度和習慣……產品起著思想灌輸和操縱的作用;它們引起一種虛假的難以看出其謬誤的意識”。當前中國電視節目市場呈現出過度娛樂化、消費主義泛濫的現象,具體表現為娛樂真人秀節目的濫觴。真人秀節目通過生動的敘事和視聽語言向觀眾提供觀看的“快感”,豐富了大眾的文化消費。但與此同時,真人秀節目也因娛樂性、虛假性、低俗性等消極因素沖擊了電視媒介話語的良性教育功能,傳播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思潮,導致社會公眾公共意識淡漠,沉浸于感官的滿足而忽視了對社會、民族應承擔的責任,并且觀眾并未察覺到自身責任意識、參與意識和理性批判精神的缺失。在社會轉型期,多種社會思潮蕪雜交錯,主流媒體更應當發揮正面的價值導向以實現公眾的良性教育。當下熱播的電視文化節目倡導公民應該承擔起對社會、對民族、對國家的責任,正是對消費主義思潮泛濫的規范和矯正。源自共和主義傳統的積極公民觀倡導公民參與到公共領域中,為共同體做出貢獻、承擔責任,因為這是精神升華、人格提升和自我實現的途徑。
《朗讀者》(第二季)開篇就邀請清華大學薛其坤等學者朗讀了《禮記·大學》,表達了中國古代士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通達情懷。《見字如面》(第二季)中呈現了抗戰時期“愛國縣長”給日本侵略者田島壽嗣的回信,表達自己堅決不向侵略者屈服的決心以及保全一方水土的勇氣。《信·中國》里也呈現了一批共產黨員在抗戰時期堅持革命的故事,承擔起對民族和對親人的責任。
三、從“勸服論”到“共同體”:對主流媒體話語調適的展望
“勸服論”是古典修辭的中心觀點,在此觀點下,話語修辭被認為是一種“語言的策略性使用”,運用修辭的目的在于“通過自己的言辭使一個團體獲得特定的意志、計劃、希望和前途”,因而帶有明顯的工具主義和實用主義傾向。“勸服論”長期貫穿于主流媒體的話語模式中。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媒介體制秉持蘇聯無產階級政黨和馬克思列寧新聞觀所倡導的“喉舌論”,各級媒體長期作為執政黨“宣傳工具”而存在,在革命時期、建設時期發揮了輿論動員和精神鼓舞的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隨著我國社會環境日益開放,社會文明日漸繁榮,傳媒生態日趨豐富,單一的“勸服論”與“喉舌論”不適應新的社會文明生態,媒介體制與媒介管理理念亟待革新。基于上述電視文化節目話語轉型的分析,我們可以窺見未來主流媒體話語調適的一個發展趨向:營造“想象的共同體”,統合官方與民間二者的立場,在話語層面上傳遞民族共同體意識。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考察了在歐裔移民者移居美洲大陸、建立政治治理體系的過程中語言文字和印刷傳播媒介發揮的作用。其中,以報紙為代表的印刷傳播媒介淡化了官方的政治性,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以呈現,讓大眾在媒介消費的過程中產生對共同體的歸屬感。他提出:“想要了解為何行政單元——不只是在美洲,在世界其他地方亦然——在經過一段長時間之后會被逐漸想象成祖國,我們必須探究行政組織創造意義的方式……加拉加斯(Caracas)的報紙以相當自然的,甚至是不帶政治性的方式,在一群特定組合的讀者同胞中創造了一個這些船舶、新娘、主教和價格都共同歸屬的想象共同體。當然,可以預期的是政治因素遲早會進入到這個想象之中。”
借助安德森的觀點,可以發現,近年來主流媒體在電視文化節目的話語調適的過程中發掘優秀民族文化,展現民族特色,彰顯民族內涵,實際上是在突破“勸服觀”帶來的傳播局限,克服民眾對主流媒體話語模式產生的僵化、權威、生硬的消極刻板印象,營造一個“大中華”的傳播共同體,有利于提升社會大眾的民族認同、文化認同、政治認同、國家認同。據此,筆者立足“共同體”的傳播理念和話語模式,針對主流媒體的話語調適和轉型提出如下展望:
1.集體記憶:民族共同體歷史遺產的再現
民族共同體的集體記憶是一個民族的歷史遺產,是實現民族團結的精神紐帶。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認為記憶是一種重塑機制,借此可以構建作為整體的自我,“我們保存著對自己生活的各個時期的記憶,這些記憶不停地再現,通過它們,就像是通過一種連續的關系,我們的認同感得以終生長存”。同時,集體記憶也是根據我們的現實需求或對現在的關注而被形塑的。
主流媒體積極構建集體記憶,是對當前民族虛無主義思潮涌動的矯正。民族虛無主義思潮否認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歷史遺產,主張民族是虛構的概念,長此以往不利于民族團結和民族認同。在媒介話語層面,民族虛無主義表現為照搬國外娛樂節目的制作模式,而忽視了對優秀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再現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并創新集體記憶的敘事模式、傳播風格,在營造民族記憶景觀中喚起歸屬感。近年來主流的黨媒、央媒在營造集體記憶上積極實踐,除了央視等電視主流媒體,人民日報、新華社等主流媒體也把握住國家公祭日、唐山大地震紀念日、“5·12”汶川大地震紀念日等關鍵時間節點,利用短視頻、H5、VR等新媒體技術再現民族集體記憶,取得了較好的傳播效果。
2.身份確認:緩解“他者化”的社會情緒
由于封建時代我國長期存在高度集中的皇權政治體制,這一歷史因素導致中國人的思維易于形成官方與民間二元對立的藩籬。而到了當前的社會轉型期,由于社會矛盾顯露,社會成員面臨著較多的“不確定性”,更容易產生“他者”的思維。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認為,在后現代社會,由于流動性、不確定性突出,“認同成了難題”。鮑曼提出,生活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后現代人深受感情的匱乏、邊界的模糊、邏輯的無常與權威的脆弱等諸多因素的困擾。結合當前的社會實際,我國目前的發展尚未到達高度穩定的社會形態,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穩定性,社會矛盾的暴露使公眾容易產生“認同失焦”的情緒。
對此,主流媒體作為社會心緒的“調節器”和“矯正器”,在“認同焦慮”的社會背景下應該強化民族共同體成員身份確認,告知、確認和強化全體成員的歸屬,即同屬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將“分散的大眾”嵌入共同體中,以緩解“他者化”的社會情緒。例如,在2017年7月30日,人民日報客戶端推出數字產品《快看吶!這是我的軍裝照》。主流媒體在建軍節這一節點推出的新媒體產品將落腳點放在“我”的角度,將人民解放軍的象征符號與受眾的閱讀體驗相勾連,旨在努力溝通官方和公眾的兩個輿論場,積極破除雙方的隔閡。
3.情感動員:激發社會凝聚與集體行動的共同信仰
主流媒體在意識形態建設與政黨形象塑造上較長時間采用說理、灌輸的權威式話語,較易給公眾留下負面的刻板印象。民族情感動員正是應對這一弊端的有效工具。涂爾干說過:“就本質而言,社會凝聚來源于共同的信仰和感情。”情感性因素是集體行動生成的內在機制,兼具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影響。其中,情感性因素發揮的積極作用表現為在集體行動中,歡樂、友愛、和諧的正向情感發揮了“潤滑劑”的作用。所以,主流媒體在維護民族團結中應當克服一味說理、闡明利益的局限性,更應該重視情感在輿論動員中的作用。重視情感的作用近年來在主流媒體的新聞報道、電視節目制作中得到了踐行。在社交媒體時代,“新黨媒”在內容傳播時大量采用情感語匯和符號,并吸收民眾話語營造親民、活潑的氛圍。同時也有意識地淡化了官方的色彩,滿足民眾的情感訴求。
注釋:
① 張寧:《政治傳播中的“非傳播”現象》,《新聞記者》,2016年第8期。
② [法]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頁。
③ 趙歡春:《意識形態話語權及其當代建構》,《江蘇社會科學》,2016年第5期。
④ 顏梅、何天平:《電視文化類節目的嬗變軌跡及文化反思》,《現代傳播》,2017年第7期。
⑤ 劉曉欣:《電視文化節目研究綜述》,《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5年第12期。
⑥ 過彤、張慶龍:《〈朗讀者〉:文化類電視綜藝節目的大眾化探索》,《傳媒評論》,2017年第3期。
⑦ 張步中、李晨:《〈信·中國〉:書信題材文化類節目的敘事創新——與〈見字如面〉的對比分析》,《中國電視》,2018年第8期。
⑨ 夏建中:《文化人類學理論學派:文化研究的歷史》,中國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頁。
⑩ 趙世林:《論民族文化傳承的本質》,《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