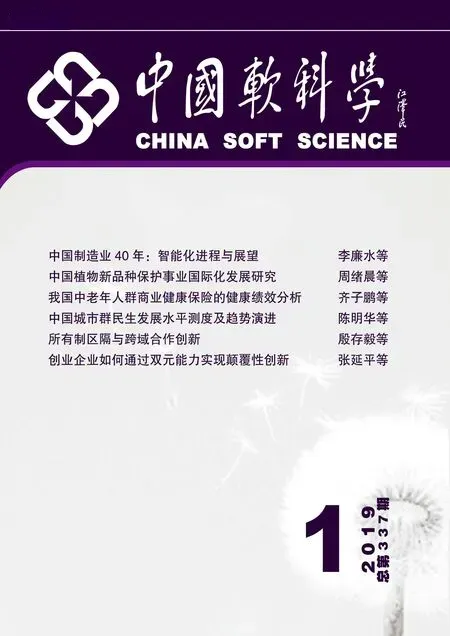中國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測度及趨勢演進
——基于城市DLI的經驗考察
陳明華,劉玉鑫,張曉萌,仲崇陽
(山東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一、引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人民生活不斷改善,但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需要繼續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1]。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僅指物質的更加富足,還表現為與人民福祉相關的各個領域的發展與改善。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的人類發展報告,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在1990年僅為0.499,到2015年已升至0.738,年均增長1.58%,實現從低人類發展水平向高人類發展水平[注]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最新劃分標準, 人類發展指數在0.550以下為低人類發展水平, 介于0.550和0.699之間為中等人類發展水平, 介于0.700和0.799之間為高人類發展水平, 0.800以上為極高人類發展水平。的躍升,中國是同期同級人類發展水平國家中唯一一個達到高人類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2]。民生發展取得的成就應歸功于黨和國家的高度關注與大力支持[注]2002年十六大首次將“民生”一詞寫入黨的報告;2007年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2012年十八大報告指出加強社會建設,必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2017年十九大報告強調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要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是實現“中國夢”的根本保障[3],在謀民生之利的同時,也不能忽視解民生之憂。2014年黨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城鎮化有利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和諧進步,要“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走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文化傳承的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全面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可見,民生的發展與改善作為新型城鎮化的關鍵任務,應始終貫穿于我國新型城鎮化的全過程[4]。而城市群作為推進新型城鎮化的主要形式,也將成為促進全國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生活質量改善的主要推動力。在此背景下,全面考察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空間差異、分布動態及趨勢演進對于補齊民生短板、解決民生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從已有相關研究進展看,對民生問題的研究大多從理論層面展開,主要包括民生的內涵及外延[5]、民生的保障與改善[6-7]以及民生與發展的關系[8-10]等方面。還有部分學者從省際視角對我國民生發展進行了實證研究:第一,民生指數測算。中國統計學會“地區發展與民生指數研究”課題組(2011)運用Delphi專家打分法設定權重,基于41項指標合成地區發展與民生指數(Development and Life Index,DLI)[11]。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民生發展報告”課題組(2011)也利用Delphi專家打分法對民生質量指數、公共服務指數和社會管理指數三者所包含的62項指標進行賦權,然后采用線性加權模型計算得到中國民生發展指數[12],但這一指數對經濟發展因素的考慮不夠全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民生指數研究”課題組(2015)構建了包含民生客觀指數和民生主觀指數在內的中國民生指數,該指數綜合反映了各省份民生發展和改善狀況及城鄉居民滿意度[13]。第二,民生發展空間非均衡考察。基于這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劉華軍和何禮偉(2015)利用Dagum基尼系數方法,從東、中、西、東北四大區域視角考察了中國2000~2012年民生改善的地區差距[14]。除此之外,也有少數學者基于城市群視角就其民生發展狀況進行了考察,王二威等人(2016)通過構建涵蓋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民生改善、生態環境的民生評價指標體系,采用改進的TOPSIS方法對珠三角地區九個城市的民生狀況做了簡要評價[15]。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發現,已有研究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具體表現為:(1)多數文獻采用專家打分法對評價指標進行賦權,帶有一定的主觀性,不利于對民生狀況的客觀評價;(2)大多民生評價指標體系對經濟發展狀況的考慮不夠全面,而我國發展經濟的目標和最終歸宿就是改善民生,因此將經濟發展因素全面納入民生評價更為客觀;(3)大多學者從省際視角對民生問題展開分析,基于城市視角的考察較為匱乏,更鮮有研究注意到我國城市群民生發展的重要性,未能對其進行深入剖析;(4)已有研究僅對我國民生發展的省際空間差異情況進行了考察,而未涉及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的動態分布狀況,未能揭示城市群民生發展的時空演進規律。
鑒于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將從城市視角考察中國八大城市群[注]根據《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和《北部灣城市群發展規劃》,本文選取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長江中游、成渝、中原、哈長以及北部灣城市群進行研究。民生發展的空間非均衡及趨勢演進。首先,基于經濟、社會、民生、生態以及科技五個方面的指標體系,運用熵權法進行客觀賦權,借鑒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DI)的測量方法,首次構建城市發展與民生指數(城市DLI),并測算中國八大城市群的民生發展水平;其次,借助Dagum基尼系數分析方法考察城市群民生發展的空間差異狀況并予以分解,進而揭示城市群民生發展相對差異大小、來源及其貢獻;再次,利用Kernel密度估計方法刻畫八大城市群整體和各城市群內部民生發展的絕對差異與極化趨勢;然后,采用Markov鏈分析方法揭示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演進的時空規律;最后,依據前文分析,得出結論與啟示。
二、研究方法
1. 熵權法
熵權表示信息在同一指標之間的競爭程度[16],同一指標當中包含的信息量與其數值差別正相關,數值差別越大,反映的信息就越多,該指標在綜合評價中所起的作用也越大,所占權重則越高。由于它僅依賴于數據本身的離散性,避免了人為因素對各評價指標的影響,使評價結果更加客觀有效[17]。具體計算步驟如下:
①確定評價對象,建立評價指標體系,構造指標水平矩陣,并進行標準化處理得矩陣R=(rij)m×n,如式(1)。
(1)
②將各指標同度量化,計算每一年各城市第j項指標的比重Pij,如式(2)。
Pij=rij/∑rij
(2)
③計算第j項指標的熵ej,如式(3),熵值越大,則指標間的差異性越小,指標越不重要;反之,指標就越重要。
ej=-k∑pijlnpij,其中k=1/lnm
(3)
④計算第j項指標的差異性系數aj,如式(4)。
aj=1-ej
(4)
⑤計算第j項指標的權重gj,如式(5)。
(5)
基于熵權法算出的各指標權重,借鑒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DI)的測量方法便可測得城市發展與民生指數(Urban Development and Life Index,以下簡稱“城市DLI”)。基本思路是:根據每個評價指標的上、下限閾值計算單個指標指數(即無量綱化),無量綱化后的值為Zj;再將評價指標體系中各指標無量綱化后的數值與其權重gj按公式(6)計算得到城市DLI,同時將反映民生狀況的各個方面按公式(6)合成類指數。這種方法測算的指數不僅橫向可比,而且縱向可比;不但可以比較各城市民生發展水平的相對位次,還可以考察每個城市民生改善的歷史進程。
(6)
2. Dagum基尼系數及其分解方法
根據子群分解方法,總體基尼系數G可以分解為區域內差異貢獻Gw、區域間凈值差異貢獻Gnb和超變密度貢獻Gt,分別反映了每一城市群內部各城市民生發展水平的差異、各城市群之間民生發展水平的差異以及各城市群的交叉重疊現象,見公式(7),具體測算方法[注]因篇幅所限,此處沒有列出具體計算公式。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參考Dagum(1997)[18]。G、Gw、Gnb和Gt都基于指標均值做平均處理,因此,它們反映的是相對差異狀況。相較于變異系數、泰爾指數和綜合熵指數等其它測度區域差距的方法,Dagum基尼系數的優越性在于它充分考慮了子樣本的分布狀況,能夠有效解決樣本數據間交叉重疊的問題,正確識別區域差異來源問題[19-21]。
G=Gw+Gnb+Gt
(7)
3. Kernel密度估計
作為研究空間分布非均衡的一種重要工具,核密度估計方法能夠對隨機變量的概率密度進行估計,并用連續的密度曲線描述隨機變量的分布態勢,進而反映變量分布的位置、形態和延展性等信息,它對模型的依賴性較弱,具有較強的穩健性。假設隨機變量X的密度函數為f(x),如式(8)。其中,N是觀測值的個數,Xi為獨立同分布的觀測值,x為均值,h為帶寬。帶寬越小,估計的密度函數曲線越不平滑,但估計精度越高,因此應盡可能選擇較小的帶寬用于實際估計。K(·)為核函數,通常包括高斯核函數、三角核函數、四角核函數、Epanechnikov核函數等,本文選擇高斯核函數研究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的分布動態演進,如式(9)。
(8)
(9)
4. Markov鏈分析
Markov鏈是一種時間和狀態均為離散的隨機過程,它通過把數據離散化為k種類型,并計算相應類型的概率分布及其隨時間的變化,以近似逼近事物演變的整個過程。假設Ft=[F1,t,F2,t,…Fk,t]為t時刻事物屬性類型的概率分布向量,則不同時刻屬性類型間的轉移可表示為一個k×k的傳統馬爾科夫轉移概率矩陣(P)[22],如式(10)。
(10)
其中,pij是某區域由t時刻的i類型在下一時刻轉移為類型j的概率,利用極大似然估計法求得pij=nij/ni,nij表示在樣本考察期內由t時刻類型i在t+1時刻轉移為類型j的區域數量之和,ni為所有時段上類型為i的區域數量之和。


(11)
(12)
(13)
三、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測度
1. 指標選取及權重設定
民生發展不僅要求縱向水平的提高,還要求橫向涵蓋領域的拓展。為了揭示城市群民生發展的客觀情況,本文基于經濟、社會、民生、生態以及科技五個維度,借鑒國家統計局關于省際地區發展與民生指數(DLI)的指標設定方案,結合數據可得性選取了23項指標,利用熵權法對各指標進行客觀賦權,并合成各一、二級指標權重,進而構建城市DLI。各指標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表1為各級指標及其權重計算結果。
2. 民生發展水平測度
基于《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規劃》、《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規劃》、《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中原城市群發展規劃》、《哈長城市群發展規劃》、《北部灣城市群發展規劃》,本文選取了八大城市群共109個城市[注]各城市群的具體界定如下:京津冀包括北京、天津、石家莊、唐山、秦皇島、保定、張家口、承德、滄州、廊坊;長三角包括上海、南京、無錫、常州、蘇州、南通、鹽城、揚州、鎮江、泰州、杭州、寧波、嘉興、湖州、紹興、金華、舟山、臺州;珠三角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肇慶、惠州、東莞、中山;長江中游包括武漢、黃石、鄂州、黃岡、孝感、咸寧、襄陽、宜昌、荊州、荊門、長沙、株洲、湘潭、岳陽、益陽、常德、衡陽、婁底、南昌、景德鎮、鷹潭、新余、宜春、萍鄉、上饒、撫州、吉安;成渝包括重慶、成都、自貢、瀘州、德陽、綿陽、遂寧、內江、樂山、南充、眉山、廣安、達州、雅安、資陽;中原包括鄭州、開封、洛陽、平頂山、新鄉、焦作、許昌、漯河、鶴壁、商丘、周口、晉城、亳州;哈長包括哈爾濱、大慶、齊齊哈爾、牡丹江、長春、吉林、四平、遼源、松原;北部灣包括北海、欽州、南寧、玉林、湛江、茂名、陽江、海口。作為研究對象。根據表1指標權重,借鑒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DI)的測算方法得到2002~2015年各城市民生發展水平,并合成了八大城市群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社會發展、生態建設和科技創新的各類指數。
表2報告了八大城市群城市DLI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八大城市群2002~2015年整體城市DLI均值為23.36,標準差為9.98。其中,得益于我國對外開放政策而率先崛起的珠三角城市群,在樣本考察期內城市DLI均值最高,由表2還可知2015年八大城市群中城市DLI排名前十的城市有3個位于珠三角,且有“世界之窗”之稱的深圳位列第一,這些都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對于促進民生發展的卓著成效。而仍處于城市群發展初期的長江中游城市群[24]樣本期內城市DLI均值最低,且作為規模最大的城市群,它僅有武漢一個城市擠入前十,說明長江中游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25]。珠三角與長江中游城市群城市DLI之差相當于長江中游的80%,且八大城市群整體城市DLI變異系數超過0.4,說明各城市群的民生發展水平存在顯著的空間差異。此外,各城市群內部城市DLI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均相差很大,京津冀、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各自城市DLI的變異系數都大于0.4,其余城市群城市DLI的變異系數也都在0.2以上,說明城市群自身民生發展過程中也存在明顯的內部非均衡性。

表1 城市DLI評價指標及權重

表2 樣本數據的描述性統計
圖1報告了2002~2015年八大城市群DLI均值演變趨勢。由圖1可見,各城市群城市DLI均呈明顯的上升趨勢。盡管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對我國造成了一定沖擊,但僅有長三角城市群的民生發展受到了比較明顯的影響,其城市DLI在2008至2012年間略有下降,而其余城市群城市DLI始終保持逐年上升的狀態,說明總體而言我國八大城市群的民生發展狀況自2002年以來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各城市群均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城市群發展戰略的益處。此外,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民生發展水平與其它城市群分界明顯,其余五個城市群的民生發展水平較為接近,且其走勢極為相似,說明五個后起城市群尚處于相對低水平的民生發展階段,民生仍有較大改善空間。
此外,本文借助雷達圖從民生所涉及的五個方面反映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的相對短板,見圖2。通過城市群之間的對比可知,經濟發展八邊形中,長江中游成為凹進的一角,說明相對于其他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民生改善八邊形中,長江中游和中原城市群為最不凸出的兩角,說明在民生改善方面長江中游和中原城市群比較欠缺;社會發展八邊形中,長江中游和北部灣城市群幾乎成為兩個平角,說明長江中游和北部灣城市群的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生態建設八邊形中,成渝和北部灣城市群對應的兩個角較平,相對而言這兩個城市群的生態建設最為緊要;科技創新八邊形中,北部灣是明顯凹進的一角,說明北部灣城市群對科技創新的重視度在八大城市群中最低。

圖1 八大城市群城市DLI演變

圖2 八大城市群民生狀況雷達圖
四、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的空間差異及其來源
以上分析表明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存在一定空間差距,為揭示其差異大小及來源,本文將利用Dagum基尼系數及其分解方法進一步展開分析。
1. 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的總體空間非均衡狀況
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總體基尼系數的均值為0.2105,城市群民生發展的空間非均衡性比較明顯。圖3反映了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總體差異的具體演變趨勢,總體基尼系數在2002~2004年小幅上升,此后保持逐年遞減狀態,在2015年下降到了0.1721,相較2002年的0.2255下降幅度為23.68%,樣本考察期內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總體差異的年均遞減率為2.06%,說明近年來中國實施的城市群協同發展戰略取得了一定成效。
2. 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的內部非均衡狀況
根據圖3、表3可知我國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的內部非均衡程度及其來源和貢獻。樣本考察期整體來看,民生發展的內部非均衡程度最高的為珠三角城市群,其區域內基尼系數均值為0.2222;其次,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區域內民生發展差異也較大,其均值分別為0.1983、0.1881;哈長、長三角以及長江中游城市群區域內民生發展差異相對較小,分別對應均值0.1579、0.1551、0.1448;最后,中原和北部灣城市群區域內民生發展差異的均值分別為0.1080、0.1055,北部灣城市群民生發展的內部非均衡性最弱。此外,區域內差異來源的均值僅為0.0226,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平均為10.73%,且考察期內其貢獻基本在稍高于10%的水平上保持平穩狀態。
考察期內八大城市群內部民生發展非均衡水平的變化過程如圖3所示。各城市群民生發展的內部非均衡性不斷改善,但城市群之間非均衡程度分級明顯。珠三角城市群內部民生發展差異始終最大,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民生發展的內部非均衡程度也較高,其次是長三角、哈長和長江中游城市群,而中原和北部灣城市群的區域內民生發展差異較低。從演變趨勢來看,考察期內珠三角、京津冀、中原、北部灣城市群的區域內民生發展差異基本均保持嚴格遞減狀態,分別年均下降2.01%、2.17%、2.97%、5.08%;長三角、長江中游城市群的區域內基尼系數均呈波動下降態勢,年均遞減率分別為1.65%、2.64%;而成渝和哈長城市群民生發展的內部非均衡性整體來看都變化不大,基尼系數曲線均呈現小幅度的“上升—下降—上升—下降”形態。

圖3 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總體及區域內基尼系數的演變
3.八大城市群區域間民生發展差異
表3、表4給出了八大城市群區域間民生發展差異大小、來源和貢獻,城市群民生發展的區域間差異均值為0.22,考察期內區域間差異來源的均值為0.123,其平均貢獻率高達58.35%,且區域間差異來源的貢獻一直都在一半以上,說明區域間差異是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總體差異的主要來源。其中,長三角與長江中游、成渝城市群的區域間差異,珠三角與京津冀、長江中游、成渝、中原、哈長、北部灣城市群的區域間差異,以及京津冀與長江中游、成渝城市群的區域間差異,均大于八大城市群區域間差異的平均水平,珠三角與長江中游城市群區域間差異最大,均值為0.33;其他城市群區域間差異小于八大城市群區域間差距的平均水平,中原和北部灣城市群區域間差異最小,均值為0.11。樣本考察期間整體來看,各城市群之間民生發展差異均有所降低,但下降的程度不盡相同。其中,長三角與中原城市群間的民生發展差異下降最快,年均遞減率高達4.4%;而京津冀和哈長城市群區域間基尼系數的年均遞減率僅為0.34%,二者發展差異下降最慢。因此,解決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非均衡問題的關鍵在于降低區域間民生發展差異,尤其應著重縮小珠三角與長江中游城市群、京津冀與哈長城市群的區域間民生發展差異。

表3 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差異的來源及其貢獻

表4 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的區域間基尼系數
注:“1”“2”“3”“4”“5”“6”“7”“8”分別代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長江中游、成渝、中原、哈長和北部灣城市群。
五、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的分布動態演進
Dagum基尼系數分析結果反映了經過城市DLI均值調整后的民生發展相對差異大小及其來源,而Kernel密度估計方法能夠有效刻畫城市群民生發展絕對差異的動態演進規律(陳明華等,2016)。因此,接下來利用Kernel密度估計方法對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的分布位置、分布態勢、分布延展性、極化趨勢等進行深入分析,具體如圖4~圖12所示,表5總結了分布動態的演進特征。
(1)八大城市群整體及各個城市群內部的民生發展水平總體來看均呈上升趨勢,這一特征與前文客觀事實相符。其中,長三角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分布先左移后右移,大致在2010年左右達到最低點,與前文客觀事實中長三角城市DLI均值曲線在2008年之后略微下降的情況相印證,說明金融危機可能對我國的金融中心造成了一定沖擊。而其他資本市場沒那么發達的城市群基本都保持右移趨勢,但移動幅度各有不同。珠三角、長江中游、中原和北部灣城市群右移幅度較大,民生發展水平得到較大提升,京津冀、成渝和哈長城市群右移幅度相對較小,民生發展水平的提升速度相對較慢。
(2)總體來看,成渝城市群內部民生發展的絕對差異稍有擴大,八大城市群整體及其它各城市群內部民生發展的絕對差異縮小。具體而言,成渝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分布的主峰峰值先降后升,總體上略微下降,主峰寬度先增后減,總體上有所增加。八大城市群整體、長三角、珠三角和中原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分布的主峰峰值呈現“下降—上升”趨勢,寬度則呈“增大—減小”趨勢。長江中游、哈長和北部灣城市群恰好相反,其主峰峰值先升后降、寬度先減后增,京津冀城市群的主峰則呈現峰值“上升—下降—上升”、寬度“縮小—擴大—縮小”的演進過程。八大城市群整體、長三角、珠三角、中原、長江中游、哈長、北部灣和京津冀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的分布雖然有所不同,但總體均表現為主峰峰值變大、寬度減小的演進態勢,說明大多數城市群民生發展的絕對差異呈減小趨勢。

表5 中國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分布動態的演變特征
(3)八大城市群整體及各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分布曲線均向右拖尾,且總體上分布的延展性均呈拓寬趨勢,說明城市群中存在“優者更優”的現象,即DLI較高城市的民生發展水平在考察期內得到提升,越發高于所在城市群的平均水平。其中,北部灣城市群的向右延展度基本保持直線上升趨勢,而其他城市群及八大城市群整體表現為波動上升形態。
(4)八大城市群整體及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長江中游和哈長城市群的民生發展呈多極分化狀態,成渝、中原和北部灣城市群的民生發展則大體上分化為兩極。就極化的程度而言,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哈長城市群始終存在顯著的多極分化現象,長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的主峰及側峰呈階梯狀排列,珠三角城市群的主峰有兩條高度相差無幾的脊線,三個側峰峰值也基本相同,而哈長城市群兩個高度相當的側峰最初是由一個側峰轉化而來;北部灣城市群的極化程度更甚,左峰總體上僅稍低于右峰,雙峰在有的年份甚至不分主側,城市群內部城市的民生發展水平基本收斂于兩個均衡點;八大城市群整體及長江中游、成渝和中原城市群的多級或兩極分化程度則比較微弱,側峰峰值均較低。

圖4 八大城市群整體

圖5 長三角城市群

圖6 珠三角城市群

圖7 京津冀城市群

圖8 長江中游城市群

圖9 成渝城市群

圖10 中原城市群

圖11 哈長城市群

圖12 北部灣城市群
六、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轉移的時空規律
Kernel密度估計方法以連續的密度曲線刻畫了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的分布動態,展現了城市群民生發展的非均衡特征及其演進趨勢,但未能揭示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的具體轉移規律,無法科學解釋城市群之間民生發展的差異情況和極化現象等,接下來本文運用Markov鏈分析方法就這一問題展開分析。
1.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變動的時間特征
在不考慮空間因素作用的條件下,首先利用傳統Markov鏈分析方法計算整個樣本考察期及兩階段內八大城市群總體和各城市群內部民生發展水平的狀態轉移概率矩陣,如表6所示,具體轉移路徑和特征如下:
(1)樣本考察期內,八大城市群整體存在明顯的“俱樂部趨同”現象,但這一現象在2008年之后減弱。城市群整體的轉移矩陣中對角線概率均大于非對角線概率,對角線轉移概率的均值為0.8768,說明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總體上保持穩定的可能性較大。具體到各城市群內部,長三角和長江中游城市群的對角線轉移概率大于非對角線轉移概率,對應的城市民生發展易出現自我固化,“俱樂部趨同”現象顯著,但在2008年之后有所改善;京津冀和北部灣城市群的對角線轉移概率均小于相應的向上轉移概率,說明這兩個城市群的民生發展呈現自我強化的趨勢,且這一趨勢在2008年之后更加明顯;珠三角城市群低、中低、中高水平城市對角線轉移概率和向上轉移概率相等,均為0.5;其他城市群內部則表現出“粘性”和“流動性”并存的特點,即不同水平城市的民生發展能力存在差別,有的容易固步自封,而有的可能突破自我。
(2)樣本考察期內,八大城市群整體、長三角、長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民生發展的“馬太效應”顯著,但在2008年之后有所減弱。大多城市群中處于低水平、高水平的城市發生轉移的可能性較小,尤其高水平城市,說明正常情況下高水平的民生發展不會倒退,而低水平城市的民生發展則易陷入“貧困陷阱”,因而城市群民生發展存在空間非均衡性。相對于2002~2008年間城市不同民生發展水平的轉移概率分布,2009~2015年間除高水平城市外,其他三級發展水平城市向其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轉移的概率均增大,表明八大城市群的民生發展差距總體上有降低傾向。
(3)矩陣對角線兩側的轉移概率大多不為0,說明城市民生發展水平在一年內發生向上或向下轉移的情況較多,而出現跳躍轉移的可能性較小。具體來看,存在跳躍轉移的僅有長三角、長江中游和北部灣城市群的低水平城市以及中原城市群的中低水平城市,且轉移概率較低。長三角城市群低水平城市在2009~2015年、2002~2015年向中高水平城市轉移的概率分別為0.0417、0.0192,長江中游城市群低水平城市在2009~2015年、2002~2015年向中高水平城市轉移的概率分別為0.0714、0.0330,北部灣城市群低水平城市在2009~2015年、2002~2015年向中高水平城市轉移的概率分別為0.25、0.1154,中原城市群中低水平城市在2009~2015年、2002~2015年向高水平城市群轉移的概率分別為0.1667、0.0769,說明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城市民生發展水平實現大幅度向上跨越的可能性并非沒有,但目前難度仍然較大。
2.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變動的空間特征
傳統Markov鏈描述了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隨時間推移而變化的轉移特征,但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地區之間經濟社會活動具有較強的關聯性,各地區的民生發展存在一定空間交互影響和溢出效應[26-27],接下來本文運用空間Markov分析方法進一步研究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的空間轉移規律。考慮到八大城市群的地理位置比較分散,城市群之間的相互作用可能比較微弱,本文主要考察城市群內部各城市間民生發展的相互影響,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的空間Markov轉移矩陣見表7[注]因篇幅所限,其他城市群的空間Markov轉移結果不再一一報告。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表6 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的傳統Markov轉移矩陣
注:L、ML、MH、H分別代表低、中低、中高、高水平狀態。
(1)長三角城市群城市民生發展水平轉移的空間特征。當“鄰居”城市民生發展處于低水平時,低水平城市向上轉移的概率為0.0769,中低水平城市向上轉移的概率為0.3333;當“鄰居”城市為中低民生發展水平時,同為中低水平的城市向上轉移的概率為0.5,而中高水平城市向上轉移的可能性相對較小,轉移概率為0.1667;當“鄰居”城市民生發展到達中高水平時,低水平城市向上轉移的概率僅為0.0769,而中高水平向上轉移的概率為0.7692;當“鄰居”城市民生發展是城市群內最高水平時,低水平城市向上轉移的概率高達0.8462,并有向中高水平跳躍轉移的可能,概率為0.0769,中低水平城市向上轉移的概率也超過一半,為0.5294,但中高水平城市向上轉移的概率較小,僅為0.0909。
以上結果說明長三角城市群中位于“落后區”的城市靠自身力量改善民生比較困難,即周圍城市民生發展水平都很低的情況下,某一城市“脫貧”難度較大;中高水平城市仍不足以帶動周邊城市的民生發展;群內最高民生水平城市才能帶動其鄰域民生改善,但帶動力度在其不同水平的“鄰居”之間有所不同,民生發展水平與它差距越大的“鄰居”所受的帶動作用越明顯,主要體現在低、中低、中高水平城市民生發展向上轉移概率依次降低;無論鄰近城市民生發展水平如何,正常情況下城市的民生發展一般不會倒退,即民生發展水平基本無向下轉移的可能。
(2)珠三角城市群城市民生發展水平轉移的空間特征。低民生發展水平城市的“鄰居”也為低水平時,下一年其發展保持平穩的概率為1,而擁有中低水平“鄰居”的低水平城市下一年保持平穩的概率為0,向上轉移概率為1,將進入中低民生發展水平城市行列;中低民生發展水平城市的轉移模式類似,在中高水平“鄰居”的帶動下,下一年所有中低水平城市均達到中高水平;中高水平城市通過高水平“鄰居”的帶動在下一年也將發展成為高水平城市,即向上轉移概率為1。
上述結果表明珠三角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城市對其相對欠發達“鄰居”城市的溢出效應相當顯著,中低水平以上的城市就能以100%的概率帶動鄰域相對較低水平城市的民生發展向上轉移。
(3)京津冀城市群城市民生發展水平轉移的空間特征。當“鄰居”城市為中低水平時,同為中低水平城市的民生發展將實現正向跳躍轉移,在下一年達到高水平,中高水平城市向高水平轉移的概率也較大,為0.6667;“鄰居”城市處于中高民生發展水平的情況下,中低水平城市下一年發展到中高水平的概率為0.75,也有向高水平跳躍轉移的可能,其正向跳躍式轉移的概率為0.1667,中高水平城市的民生將在下一年發展為高水平;鄰近高民生發展水平的城市時,低、中低、中高水平城市都有向上轉移的可能,轉移概率分別為0.5385、0.3846、0.8571。
可見,京津冀城市群中較低民生水平的城市自我發展能力本身就較強,且易受較高民生發展級別城市的帶動,但高水平城市對于其不同水平“鄰居”的作用存在差異,中高水平城市受其影響最大,低水平城市次之,中低水平城市所受作用最弱。
為檢驗鄰域城市民生發展水平對城市民生發展的上述影響是否統計顯著,本文利用卡方檢驗進行了驗證,原假設為鄰域城市民生發展水平對相鄰城市的民生發展沒有影響,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的Q統計值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鄰居”城市的民生發展水平對其相鄰城市的民生發展具有顯著影響,具體檢驗結果見表7。

表7 城市群民生發展的空間Markov轉移矩陣及卡方檢驗結果
注:L、ML、MH、H分別代表低、中低、中高、高水平狀態。
另外,其他五個城市群內部各城市的民生發展也都存在一定交互作用和溢出效應,空間因素影響均在統計意義上顯著但作用程度不同。北部灣城市群較高民生發展水平城市對較低水平鄰域城市的帶動作用較強,中原和哈長城市群次之,長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內部城市對鄰近較低民生發展水平城市的帶動作用均較弱。由于篇幅所限,此處不再詳細展開。
七、結論及啟示
本文基于2002~2015年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長江中游、成渝、中原、哈長和北部灣城市群的城市DLI,借助Dagum基尼系數、Kernel密度估計方法以及Markov鏈分析方法對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的空間非均衡特征及趨勢演進展開了分析。研究結論如下:(1)樣本考察期內,八大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均呈明顯的上升趨勢。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民生發展水平顯著高于其它城市群,五個后起城市群尚處于相對低水平的民生發展階段,民生仍有較大改善空間。(2)八大城市群之間及其內部的民生發展差異不斷縮小,但民生發展水平的空間非均衡性仍然顯著。其中,珠三角城市群的區域內差異最大,哈長城市群區域內差異的平均下降幅度最小、速度最慢;珠三角與長江中游城市群的區域間差異最大,京津冀和哈長城市群之間民生發展差異的平均下降幅度最小、速度最慢。區域間差異來源的貢獻始終都在一半以上,是民生發展差距的主要來源。(3)只有成渝城市群內部民生發展的絕對差異呈擴大趨勢,各城市群的民生發展均始終存在明顯的極化現象。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長江中游和哈長城市群的民生發展呈多極分化狀態,成渝、中原和北部灣城市群的民生發展則大體上分化為兩極,區域內民生發展的協調性有待增強。(4)在不考慮空間因素的條件下,京津冀和北部灣城市群民生發展水平的自我提升能力較強,而八大城市群整體、長三角、長江中游存在顯著的 “俱樂部趨同”現象,其對角線轉移概率均大于非對角線。八大城市群整體、長三角、長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的民生發展具有 “馬太效應”,低水平和高水平城市發生轉移的可能性很小,使得其民生發展水平呈現明顯的空間非均衡特征。但城市群的“俱樂部趨同”現象和“馬太效應”在2008年之后均有所減弱。(5)將空間因素納入考察后,城市群內部相鄰城市的民生發展水平普遍存在較強的交互影響和溢出效應,其中長三角、長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俱樂部趨同”現象和“馬太效應”減弱趨勢較為顯著;珠三角城市群較高民生發展水平城市對其鄰域城市的帶動作用最強,中低水平以上的城市就能以100%的概率帶動鄰域相對較低水平城市的民生發展向上轉移;長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內部較高水平城市對鄰近城市的帶動能力相對較弱。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本文認為改善城市群民生的過程中,不僅要關注城市群民生發展的充分性,更要重視其平衡性。著重縮小城市群之間的民生發展差距的同時,也要減弱各城市群內部民生發展的極化程度,具體啟示如下:
第一,應基于各城市群自身的民生短板,實施差異化民生發展戰略。根據雷達圖顯示的我國八大城市群各民生領域的非均衡狀況,各個城市群應針對其民生領域的短板,選擇與其所處民生發展階段相適應、能夠充分發揮其區域優勢的民生發展戰略,降低城市群之間民生發展的空間非均衡程度。具體而言,京津冀城市群應大力支持科學技術尤其民生科技、生態科技的創新,借科技力量突破民生發展瓶頸;長三角城市群面對當前經濟增速趨緩的現狀,增強經濟發展活力是其民生發展的主要突破口,應借助其亞太地區重要國際門戶的優勢地位,重點發展國際金融、商務、物流等領域的高科技、高附加值產業,帶動人民生活質量進一步提升;珠三角城市群作為開放的“先行區”、改革的“實驗田”,應先行先試,大膽探索,爭取率先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體制改革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有所突破,實現民生的全面改善,為其他城市群乃至全國各地的民生發展提供新鮮經驗;相對其他城市群而言,長江中游城市群的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和社會發展都屬于其民生短板,長江中游城市群應把握住新型城鎮化發展促城鄉社會結構轉型的契機,充分發掘經濟增長潛力,并進一步改善民生;成渝城市群的民生短板主要是生態建設,成渝城市群地處長江上游,其生態建設關乎整個長江黃金水道沿岸地區的發展,應培育綠色化的生產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設運營模式,推動綠色永續發展進而提高民生發展水平;中原城市群的民生改善相對比較欠缺,應著力改善收入分配,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公共服務體系,進一步保障就業,進而提高居民生活質量;哈長城市群肩負著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任務,應加快建設“中蒙俄經濟走廊”陸海絲綢之路經濟帶,積極參與對外開放的國際分工及合作,推進結構性改革及發展方式轉變,通過讓經濟重新煥發強大生機來發展民生;北部灣城市群社會發展、生態建設和科技創新三個領域相對落后,應借助先天的地緣優勢,發揮有機銜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潛質,引進先進科學技術并推動社會全面發展,同時利用得天獨厚的區域特質發展陸海綠色產業,助力生態建設。各城市群對自身民生短板的精準認識、對民生發展的詳盡規劃可以借助專業的民間組織來實現,以城市群內學術界的代表人物和專家學者為主體建立城市群“智囊團”,為解決各種民生發展問題進行科學論證,在城市群民生發展戰略的制定中形成充分的討論空間并達成共識,為城市群民生的高水平、高質量發展獻計獻策。
第二,應發揮城市間空間溢出效應,促進城市群內部民生平衡發展。通過細化城市群內部職能分工,發揮高水平城市對鄰近地區的正向拉動作用,有效解決產業分工不合理、民生改善不協調、社會發展不均衡、生態環境治理缺乏整體性、科技創新動力和能力不足等民生發展問題,降低各城市群內部民生發展的極化程度。首先,整合群內各城市的優勢與相對優勢,優化城市之間的產業分工和功能結構,減弱城市間的產業同構度,減少城市之間的消耗性競爭,增強城市群內部的凝聚合力和經濟活力;其次,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促進勞動力在城市、行業、企業之間自由流動,保證勞有所得,改善居民生活狀況;再次,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降低公共服務、文化教育、衛生健康、通訊交通和資本融通領域的城鄉差距,促進整個社會的均衡發展;然后,構建城市群生態環境綜合管理體系,實現生態環境的上下共治、政企共建、人人共享;最后,構建城市群一體化、網絡化創新體系,在追求科技創新能力縱深拓展的同時,加強科技創新水平的橫向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