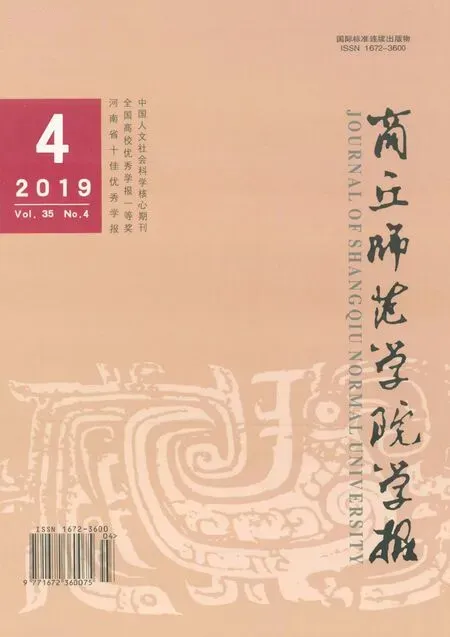法律規避誤區的澄清
張 新
(華東政法大學 法律學院,上海200042)
法律規避通常系指當事人事實上意欲從事某種法律上禁止之行為,卻通過為法律之文義未包含之法律行為架構方式,最終實現了相同的經濟上結果[注]①法律規避亦系國際私法中的一個固定概念,指當事人借助沖突法規則中可變連結因素,故意避開本應適用之強行法而使利己法律得以適用之行為。參見陳衛佐:《比較國際私法——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的立法、規則和原理的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51頁。但本文均在國內法意義上使用法律規避概念。[1][2]。我國《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第1款第7項、《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3項均規定,“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之行為無效。學理上多認為,“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系避法行為(或脫法行為)[3][4][5]。司法實務中,當涉及法律規避時,法院亦多援引該規定徑直判定行為無效[注]②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4號民事判決書、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閩民終字第1054號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四終字第15號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終字第29號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766號民事判決書。。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對“規避”一詞的使用頗為豐富,如規避風險、規避執行[注]③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依法制裁規避執行行為的若干意見》(法〔2011〕195號)。、規避損失、規避制裁、規避準據法[注]④法律規避本就是國際私法的一個概念,指回避原本應當適用的準據法,而使他國或地區準據法得以適用的行為。、避稅、規避法律等。那么究竟何者屬于我們討論的私法中的法律規避?法律規避與規避行為、法律行為、違法行為以及無效行為關系為何?對于這些基本問題,我們尚缺乏清晰的認識,且不乏理解上的誤區,本文擬對此作一探討。
一、法律規避與規避行為
法律規避行為概念于羅馬法后期始逐漸形成,又稱為“對法律的欺詐行為(in fraudemlegisagere)”。我國學者通常采用“法律規避”[3]“規避法律”[5]“避法行為”[2]等稱謂,在臺灣地區民法上又稱之為“脫法行為”[6]333[7]224[8]210,德國法上對應的稱謂為“Gesetzesumgehung”[9][10][11]731[12][13]181-182。在學理或實務上,人們為了使用上的簡便,通常以規避行為指代法律規避行為。但必須明辨的是,二者并非完全等同之概念。規避行為其實系法律規避行為的上位概念。以規避之客體為分類標準,不僅包括法律規范,還包含約定之負擔。換言之,規避行為除法律規避行為類型外,還涵蓋規避約定內容之行為。
茲舉一例加以說明,甲項目公司有一塊地A,系甲公司之唯一或主要資產,甲未確定是否出賣,乙十分想購買,于是主動找到甲,約定了一個優先購買權,支付給甲10萬元。后來丙公司欲購買該地,亦找到甲,由于甲、丙公司之間關系較好,此時甲欲出賣A地于丙,但礙于乙之優先購買權,于是甲、丙決定由丙公司吸收合并甲公司,從而實現取得該地塊的建設用地使用權的目的。甲、丙之吸收合并行為,即實現了規避甲、乙之間約定負擔之目的。因為自客觀經濟效果而言,丙公司取得了該地塊的所有權,而乙公司約定之優先購買權落空。
法律規避與合同規避(Vertragsumgehung)系規避的兩種類型,盡管我們在日常使用中,多指代前者,但不妨礙后者之客觀存在。正如學者弗盧梅精準地定義,規避行為,系當事人通過法律行為之架構方式規避某一法定或意定規則[14]350。在處理路徑上,前者關涉對相關法律規范之解釋,后者涉及對意思表示之解釋,具體而言,系補充性契約解釋。
補充性合同解釋是對存在漏洞的契約所作的補充。首先,對當事人的意思表示進行解釋,確認合同成立后,才可能對合同進行補充性解釋。此時,可能發現合同中未就某一事項作出約定。該結果可能出于當事人雙方故意之不作為,因為他們認為非為必要,也可能系無意之不作為,因為忽視了特定問題或者不可能考慮到該問題。補充性解釋的前提是,法律行為中存在漏洞,法官通過漏洞填補進行補充[15]。而是否存在漏洞,系通過對法律行為進行解釋來查明。只是該解釋不應只停留在對效果意思之查明,還應對引起效果意思之動機及其他情況進行分析。須填補的漏洞在以下情況中存在:締結法律行為之當事人沒有或者以非正確的方式對特定情況加以考慮。無論是當事人在法律行為締結時忽視了既存之情況(原生漏洞),抑或該情況嗣后發生(次生漏洞),對解釋不生影響。
如果在法律行為中發現了需要加以規范的漏洞,那么法官必須對其進行填補。法官須查明,假如當事人考慮到了未想到的情況并且注意到了誠實信用原則及交易習慣,那么其所欲為何。鑒此,其決定性作用的系假設之意思,而非當事人之真實想法。對假設之意思的查明,必須從當事人在合同中的評價出發,并提出以下問題:在知道該漏洞的情況下當事人會如何合理地進行約定。在填補漏洞時,應當以當事人的評價作為基礎。盡管補充的契約解釋以假定的當事人意思為依據,但卻通過假設當事人原本就對實質上正確的東西有所意愿,從而致使那種假定之意思向客觀轉向。如德國帝國法院指出,被表示出來的東西,也包括從合同條款的整體關聯中推出的不言自明的結論;并以此為出發點,當事人基于合同目的及交易觀念,愿意作出此種(補充之解釋)安排,且依照由雙方確立之原則也已作出了該種安排[16]96。有鑒于此,補充之解釋不僅僅因為當事人想到了,就會作出如此之約定,還應將其視為由整體行為之關聯性所附帶之內容。
補充性解釋是一種使個案實現正義的不可或缺的輔助手段[16]99。法官在填補漏洞時如何考慮當事人之評價取決于個案中的情況。因此,必須考慮案件中的所有情況,如動機、目的、交易習慣、利益狀況等。通常而言,探明當事人所追求之目的起決定性作用。例如,乙將某書店轉賣給甲,一個月后,乙又在隔壁重新開了一家書店。甲認為,乙不應當與自己競爭。乙反駁說,并不存在此類競業禁止,因為他們并未在合同中對此進行約定。該案中,乙之行為會對合同造成廣泛的損害,結合契約目的、誠信原則,如果當事人考慮到該情況,將會就特定期間內的重新開店禁止作出約定,如此,漏洞即得到相應補充。
概言之,補充性合同解釋以假定的當事人意思為依據,而假設的當事人意思之探尋,以當事人于契約上所作的價值判斷(契約目的)作為出發點,基于交易習慣和誠實信用原則而為認定[7]327。而合同規避系當事人通過為合同中未明確約定之內容,實現逃避合同負擔之結果,致使合同之目的落空。因此,面臨合同規避問題,法官需要從事的,系判斷是否存在契約漏洞,是否進行補充性契約解釋,以及作出何種補充解釋。倘當事人所為之行為恰巧系補充之解釋內容,則約定之負擔依然發生。有鑒于此,合同規避問題的本質系補充性合同解釋問題。
在法律后果上,合同規避與法律規避存在區別,前者非涉及法律行為效力問題,而僅關涉約定之負擔是否發生的問題。以前文所涉案件為例,查明假定之當事人意思,乙公司與甲公司簽訂“約定之優先權合同”的目的在于當項目公司甲欲出售地塊時,自己享有優先購買之權利。盡管雙方未對甲能否被其他公司吸收合并在合同中作出約定,但考慮到甲公司系項目公司,該地塊系其唯一資產,其被他公司吸收合并與其直接出賣該地塊并無二致,因此,根據契約目的、誠實信用原則,對甲公司之被吸收合并行為之禁止,構成了優先權合同之不言自明的組成部分。如此,契約漏洞即得到相應補充。而甲公司違反該內容,則約定之負擔發生,乙可基于約定向甲主張該優先購買權,即使甲不存在,乙亦可向丙行使該權利。
除此之外,筆者發現,實踐中法律規避之外,還存在一種類于合同規避,但又不完全相同之規避行為,當事人規避的既不是法律,又非合同上約定之負擔,而系附條件要約或承諾之“條件限制”。例如,在呂培從與福建省南安市華洲石業有限公司股票權利確認糾紛案中,原告呂培從與被告華洲公司簽訂《委托代購合同》,約定呂培從委托華洲公司代購南安農村合作銀行股權400萬股,股本金額由呂培從承擔,華洲公司出面購買。股份雖在公司名下,但實際為呂培從資產而由公司代為持有。根據2010年6月22日所發布的《福建南安農村商業銀行增資擴股公告》,明確規定不募集新自然人股東。一審法院認定,原告呂培從與被告華洲公司簽訂《委托代購合同》,主體適格,意思表示真實,內容沒有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該合同合法有效。《福建南安農村商業銀行增資擴股公告》雖然規定不募集新自然人股東,原告呂培從存在規避該公告的行為,但該行為的目的在于購買福建南安農村合作銀行的股份,其行為沒有違反法律法規禁止性規定,并不影響合同的有效性。法院此項認定是否妥當,暫不具論,其須強調者,系本案法律行為所規避之客體,并為規避行為類型上的重要問題。
依筆者所見,福建南安農村商業銀行的增資擴股公告系“附條件之要約”,而案涉委托代購合同正是為了規避該“條件限制”,從而實現訂立合同之目的。從性質上而言,該“條件”非為法律,亦非合同之負擔,因為合同還未成立,充其量可以稱之為“承諾之負擔”。鑒此,規避之客體為要約之條件限制。類似情形還可能發生于房屋買賣情形。例如,房產商甲為回饋家鄉,開發了一棟房屋,以市價的一半出售,但明確表示只售賣給自己所在村的村民。現不符條件的乙與未有資金的村民丙簽訂《委托代購合同》,約定由丙出面購買房屋并代為持有,但房屋實質系乙所有。
綜上,法律規避僅系規避行為之一種,盡管屬于最為典型的類型。除法律規避外,規避行為還包括合同規避,以及規避要約之“條件限制”。
二、法律規避與法律行為
法律規避行為系國內私法中的概念,其前提系以法律行為之架構方式來規避法律。同時,只有規避行為屬于法律行為,才有私法上研究之意義,因為只有法律行為才有效力瑕疵的問題,才可被施以法律上的價值評價。
司法實務中,諸多“規避”與本文所論述之規避行為、法律規避或法律規避行為無涉,只因其全程中并無任何一個法律行為存在。
例如,“故意提高訴訟標的額規避級別管轄”類案件,法院指出:“為了避免當事人故意規避有關級別管轄的規定,應對起訴進行形式審查,并根據當事人提交的表面證據所指向的數額確定訴訟標的額,進而作出判斷。”[注]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轄終326號民事裁定書、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浙民初14號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終字第165號民事裁定書。其實,關于該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1996年專門有一個批復,指出:“當事人在訴訟中增加訴訟請求從而加大訴訟標的額,致使訴訟標的額超過受訴法院級別管轄權限的,一般不再予以變動。但是當事人故意規避有關級別管轄等規定的除外。”[注]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級別管轄規定幾個問題的批復》第2條。
又如,“單純隱藏財產規避執行”類案件,當事人通過單純將金錢、財物隱藏于他處方式,以規避法院執行[注]參見石嘴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寧02執異13號裁定書。。
前述案件中,盡管法院在認定上均使用“規避”一詞,但應明辨,法院充其量只是在“主觀目的”層面使用該詞,客觀實際上,其與法律規避行為無涉,因為從中壓根無法找出一個為了規避目的而為的法律行為。
因此,法律規避行為首先系法律行為,私法中對法律規避之研究的最終落腳點,系對法律規避行為之法效果判定上。
三、法律規避與違法行為
違法行為,顧名思義,當事人之行為直接違反了法律規定。換言之,當事人之行為符合了法律規范之構成要件,被涵攝在法律規范的射程之內。例如,當事人之間簽訂販賣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玳瑁”之契約,直接違反了《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七條第1款、《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之規定,系直接違法行為。又如,當事人之間簽訂買賣人體器官“肝臟”之契約,依據《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三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買賣人體器官,不得從事與買賣人體器官有關的活動”,系直接違法行為。
法律規避的一個關鍵特征,系不違反法律規定之文義(Wortlaut)。易言之,規避行為并不符合法律規范之構成要件,不能直接被法律規范所涵攝。比如,當事人為了規避器官買賣禁令,將器官買賣合同拆分為器官捐贈合同以及器官贈予合同。由于法律不禁止器官捐贈,故不構成直接違法,但實現了相同的經濟上結果。
法律規避與直接違法之間存在兩個維度的問題:其一,通過意思表示解釋認定的法律事實直接落入既有規范之射程范圍,系直接違法,或者將本屬規避之行為,強行進行法律行為解釋,認定為直接違法,實踐中最為典型的例證系“名為……實為……”類案件;其二,通過法律解釋,更具體而言,系目的論擴張解釋,從而將案涉情形涵攝于內,亦系直接違法(或失敗的規避)。下文分別詳述之。
(一)法律規避與“名實不符”
在司法實踐中,大量存在一類案件,法院在判決中認定“名為……實為……”,并據此作出判決。有學者認為,這屬于“虛偽行為”之一種[17];亦有認為,其構成法律規避[注]在“長春中振發展有限公司與長春電影制片廠房地產開發公司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糾紛上訴案”中,一審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即認為,長影廠房地產公司與中振公司簽訂的《關于聯合建房協議書》是名為聯營,實為土地使用權轉讓,雙方以聯建為名,規避法律、行政法規,以達到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之目的,故雙方所簽聯建協議無效。參見最高人民法院(1999)經終字第225號判決書。。筆者對這兩種觀點皆持否定態度。筆者認為,“名為……實為……”類案件,當事人可能存在避法目的,可能涉及隱藏真意目的,但其本質是意思表示或法律行為解釋問題,處理上是撥開字面上的“云霧”,探究當事人真意的過程。其既非虛偽行為規范規制之領域,亦非規避制度輻射之范圍。同時不同于“陰陽合同”,后者客觀上存在“一真一假”兩個法律行為,而前者僅是對“同一事物”認識上的不同而已,一般僅存在一個法律行為。例一,甲、乙之間從事毒品交易行為,為掩人耳目,稱之為奶粉買賣合同。例二,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件投資糾紛案中指出,案涉投資合作關系,實質是投資人僅提供資金,但是不參與經營管理,也不承擔任何經營風險,無論企業盈虧,投資人均享受每月固定回報。這種合作模式違反了合作共享收益、共擔風險的基本原則,屬于“名為合作,實為借貸”[注]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四終字第40號民事判決書。。例三,最高人民法院在李建國與孟凡生、長春圣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案中指出:“該內部承包合同約定的承包范圍為《資質證書》中規定的工業與民用建筑承包范圍,也就是說,究其合同約定之實質,該合同‘名為內部承包,實為建設工程施工企業資質租賃或者有償使用’。李建國在庭審中亦自認其經營建和分公司,主要是利用圣祥公司的資質方便其對外承攬建筑程。換言之,該內部承包合同約定之實質并非承包法律關系。建筑施工企業具有很強的專業技術性,其施工質量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因此不僅要求此類企業要具有符合國家規定的注冊資本,而且要具有與所從事的建筑施工活動相適應的專業資質。實踐中,一些建筑施工企業中所謂承包或者租賃經營的實質,是不具備資質的企業或者個人,以承包或者租賃形式,掩蓋其借用建筑施工企業資質進行施工的目的,由于借用資質進行施工是法律及司法解釋所禁止的行為,故與之相關的承包或者租賃經營合同以及施工轉分包合同亦為法律所不容。”[注]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149號民事判決書。上述案例中只存在一個法律行為,且法院也只是根據掌握的證據,對當事人的意思作出實質認定而已,故不同于一真一假形式的“陰陽合同”,且一般按照實質內容認定后,行為即自動落入法律規范之涵攝范圍,構成直接違法行為,從而與規避無涉。
但在司法實踐中,法院諸多名實不符之認定不免存在僭越之嫌,似超越法律行為解釋之一般規則。例一,在一則涉及采礦權糾紛的案件中,當事人通過投資方式入股煤礦項目,并約定其投資主要用于采礦權價款等費用支付,法院認定該協議是“名為雙方合作經營,實為采礦權購買及權益分配”,而其行為未經依法批準,違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5項、《礦產資源法》第六條之法律強制性規定,依法應認定為無效合同[注]參見“林為曾、陳永河合伙協議糾紛再審案件”,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228號民事判決書。。例二,在朱岳海與海南萬寧大花角海洋文化城有限公司、趙守仁股權糾紛案中,大花角公司的股東將其100%股權全部轉讓給新股東,公司資產中包括海南省萬寧市港北鎮某塊國有土地使用權,一審法院即認定名為股權轉讓,實為土地使用權轉讓,由于該宗土地目前既沒有形成工業用地或其他建設用地條件,轉讓不符合法定條件,故雙方之轉讓行為系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行為[注]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二終字第2號民事裁定書。。
不過令人欣慰的是,早在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已有相關答復[注]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上訴人練志偉與被上訴人陳如明及原審被告林惠貞、鄭秀英及原審第三人福州市常青實業有限公司股權轉讓一案的請示的復函。([2006]民四他字第22號)。案情簡化如下:福州常青公司原股東練長清、林惠貞(甲方)以股東代表練長清的名義與陳如明(乙方)簽訂了一份《企業股份轉讓合同》。該合同約定,甲方權屬常青公司的工廠包括廠區內的建筑物、水、電設施等及凡屬常青公司的財產100%轉讓給陳如明;甲方辦妥市計委立項手續后,乙方應無條件支付甲方股份轉讓金人民幣265萬元。甲、乙雙方即辦理企業法定地址以及法人代表變更。合議庭多數人認為,訟爭合同的性質,應從合同的名稱、內容去審查認定,同時還應考察簽約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從本案合同的名稱、合同訂立的主體、內容及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分析認定,本案訟爭的《企業股份轉讓合同》正像其所表述的那樣,應定性為股權轉讓合同。但少數人認為,本案合同形式上是股權轉讓合同,但內容上明確約定所轉讓標的,僅系常青公司擁有的工廠廠房、設施及土地使用權,既未包括公司擁有的其他財產,也未接管職工,實質上轉讓的是劃撥土地使用權和地上物,故應定性為財產轉讓合同。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就本案合同定性問題,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最高人民法院答復,贊同多數說意見,理由主要有三點:其一,合同名稱本身為“股權轉讓合同”;其二,合同甲方當事人為股東,而非常青公司,故無法實現公司財產之轉讓;其三,從合同諸多條款之文義、體系解釋來看,轉讓之標的物確系公司股權,此為雙方當事人之真意,否則亦無須約定法定代表人變更等事宜。有鑒于此,最高人民法院認定案涉合同為股權轉讓合同。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強調,本案常青公司擁有之土地使用權財產系劃撥用地,因此公司股東通過股權全部轉讓方式,是否實質在移轉土地使用權,應予審查。
最高人民法院的認定殊值贊同。依照其認定思路及精神,上文例一、例二之法院行為定性存在問題皆不言自明。“名為……實為……”系法律行為解釋及定性問題,因此法官不能超越法律行為解釋之一般規則,應以雙方當事人的真意為據,超越當事人意思之行為定性系事實認定錯誤。倘問法院為何如此青睞該種處理方式,究因如此為之,案涉行為自動落入法律規范之涵攝范圍,構成直接違法,法官之樸素的法感情得以“抒發”,且按照此種案件處理方式,不可能再存在法律規避,所有的法律規避行為都將落入直接違法行為的“口袋”。但該種做法,破壞性極強,一旦流于形式,會嚴重戕害意思自治,將所有法律行為置于無效風險之下,絕不足采。司法實踐中,法院對“名實不符”之行為認定應持一種極為謹慎之態度。
(二)法律規避與擴張解釋
法律解釋與法律續造之界分,理論上以言,甚為明晰,但實踐中不無疑義。在法學方法論上,“可能之文義”系劃定法律解釋與法律續造之界限,實在不能發現其他的界分標準,此種界分也受到學界及實務界的普遍承認,具體指依一般語言用法,或者立法者標準之語言用法,該用語能夠指稱之意義[18]202-203。但可能之文義未必始終能精確界定,因此在某些事例,究竟是在作擴張解釋,抑或通過類推適用在作漏洞填補,有時不無疑問。折射到規避領域,如果通過擴張解釋可以涵蓋案涉情形,則仍系直接違法,又被學者稱為“失敗之規避”。易言之,規避必須逾越語言上可能之文義范圍,依法律可能之文義,作最廣義的解釋,尚不能使之涵攝于案件事實時方可。例如,德國法上規定,禁止養老院的老人通過遺囑將護理人員列為繼承人,現某老人將其財產遺贈給其護工的配偶。無論將“護理人員”如何作擴大解釋,亦無法包含非從事護理工作的護工的配偶,故不滿足規范要件,不構成規定之直接違反,但德國法院認定其構成法律規避,進而判決遺贈行為無效[19]。
但是,由于可能之文義范圍之非得準確界定性,所以于規避情形,可能出現擴大解釋與法律續造之爭議問題。茲舉一例加以說明,近期影響較大的“福建偉杰投資有限公司與福州天策實業有限公司以及第三人君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營業信托糾紛案”中[20][21][22],天策公司與偉杰公司簽訂《信托持股協議》約定,鑒于委托人天策公司擁有正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2億股的股份(占20%)的實益權利,現通過信托的方式委托受托人偉杰公司持股。受托人偉杰公司同意接受委托人的委托。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雙方簽訂的《信托持股協議》明顯違反了《保險公司股權管理辦法》第八條關于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保險公司的股權的規定[注]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終529號民事裁定書。。該案中,筆者認為,要作出準確的結論,必須首先辨別 “委托持股” 與 “信托持股”的關系,易言之,前者在文義上能否通過平義解釋甚至是擴大解釋的方式包含后者,不無疑問。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則為直接違法;反之,至多可通過進一步的立法目的探尋,判斷可否類推適用之。
此外,根據原則上的一致意見,法律規避有別于法律避免(Gesetzesvermeidung),后者不違反規范意旨。而法律規避的特殊性在于,雖不違反規范文義(Wortlaut),但違反規范的內容(Inhalt)。類似的表述,如果通過濫用他種法律行為型構方式,致使強行性規定的規范目的落空,則系屬法律規避[23]91。規避之存在,導致強行法的目的被破壞,其他的法律上的手段可能性被濫用。法律規避被看作是對規范意旨之違反,該意旨是通過目的性解釋查明的。因此,學者Teichmann批評該定義,其會導致人們將法律規避與法律解釋相提并論或同質化,但按照主流觀點,法律規避僅存在于被規避規范之解釋界限被逾越時。鑒此,法律規避與違法行為存在共性,即行為經濟上結果相同,且都違反了規范意旨。所以對于法律規避行為(狹義),為了貫徹規范目的,不致使立法目的落空,在德國法上,通常采用類推適用相關法律規定手段進行漏洞填補。
綜上所述,法律規避與直接違法行為區別在于,法律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之構成要件。共性在于,行為之經濟上結果相同或類似,且違反規范意旨。
四、法律規避行為與無效行為
法律規避行為與無效行為關系,具體體現為二者是否必然存在包含關系。如果說《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3項“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指的就是法律規避,由于其法定效果僅系無效一種,所以可能結論很簡單,即法律規避行為是無效行為之一種。但該規定本身廣受詬病,無論是其構成要件上之模糊性,還是其法律效果上之單一性。有鑒于此,學界、司法界皆提出了修正之方案[17]。筆者無意在此展開論述,僅欲提出一個淺顯的問題,即違反禁止性規定,法律行為是否一律無效?依據《民法總則》第一百五十三條第1款之但書內容,答案不言自明,否則該但書規定毫無意義。既然直接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法律行為非一定無效,易言之,行為或有效,或效力待定。那么當事人采用更弱之迂回方式,行為反而一律絕對無效,遭受更嚴苛之負面法律評價,無論按照“舉重以明輕”方法,哪怕依據“同等對待原則”,結論都無法讓人信服。鑒此,至少可初步作一結論,法律規避行為非一定系無效行為,可能有效可能存在效力瑕疵。
從本質上講,法律規避僅系對一種客觀現象的描述,僅具描述性功能(deskriptiveFunktion)[24]11,伴隨著此種現象,法律適用者必須審查既有規范之意旨是否得到貫徹,存在法律漏洞與否,應否進行法律續造,具體而言,系可否類推適用相關規范于案涉法律規避行為。所以法律規避行為的后果非為直接無效,而是得否類推適用被規避規范,最終法律效果如何,取決于該規定之規范性質和立法目的。如果該規范系單純強行規定,則行為一定發生效力瑕疵;如果其性質系禁止性規定,則須援引《民法總則》第一百五十三條第1款(管道條款),并結合規范意旨,經由比例原則手段進行法律行為效力判定,方能得出妥適之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