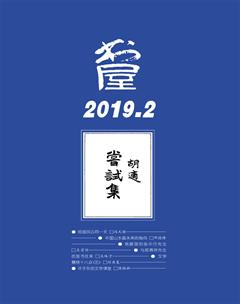許子東的文學課堂
侯桂新
世人大都知道許子東長期擔任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的嘉賓,后來又參與了“圓桌派”與“見字如面”等文化類節目,通過電視感知到的許老師,無愧于當代學者中的“名嘴”之一。然而在這些節目上,受限于角色安排和時間分配,許老師的言談往往只能點到即止,無法盡興,要真正充分領略他的語言魅力,只有進入他的課堂。2006年至2009年,我于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追隨許老師求學三年,深刻體會到他清新脫俗的課堂藝術。
許老師在嶺南大學常年給本科生開設兩門課程,一為“中國現代文學”,一為“中國現代文學選讀”,實際上也可以說是一門課,合起來就是內地大學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因為香港學期頗短,每個學期頂多只上十五個星期的課,要在一個學期內講完現代文學是不可能的,于是許老師將其一分為二:“中國現代文學”側重講述“五四”文學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一些文學大家,“中國現代文學選讀”側重講述三四十年代的重要作家作品。不管是講哪一個時段,都以具體文學作品的研讀為重。考慮到香港學制學期較短的特點與香港學生普遍重視實踐而于宏大敘事欠缺興趣的實際情況,許老師擯棄了內地的概論式、灌輸式授課方式,除了必要的背景介紹,將精力都集中在作家和作品研讀上。因此,雖然他的課堂較少涉及文學思潮與流派、文學社團與運動,但通過精讀數十篇各類文體的代表性作品,也能夠對現代文學三十年所取得的主要成就進行較為全面的覆蓋。
許老師上課有大綱,每次課前給每個學生發一頁打印紙,從上面可以看到授課的基本內容和思路,以及需要閱讀的參考資料和重點引文,便于講者和聽者思維的集中,但他沒有統一的、與他人雷同的教學大綱——香港特區政府和各大學也無此要求。因此,教師可以根據自身研究所長,自主設計教學內容和教學形式。這對于許老師這樣的資深研究者而言是再合適不過了,課堂給了他很大的發揮空間,他不必人云亦云,講的都是自己對文學的個人化理解。雖然,他也指定了錢理群先生等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和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作為學生的參考讀物,但除了引用其中個別重要觀點,書上有的他基本不講,絕不做他人的傳聲筒。
在許老師看來,大學生應當具有較強的自學能力,在一個網絡信息化時代,公共知識的獲取十分便利,大學課堂對學生的主要意義和價值不在于傳授具體知識,而在于引導求學,啟發思考,增廣見聞,開闊視野。大學教師應當平等對待學生,他固然對于事物有自己的獨立價值判斷,但不會呈現出一副獨斷和權威的面孔,相反對于多元價值觀保持著高度尊重。中國現代文學是一門非常特殊的學科,因為它時刻會觸及傳統和現代兩種價值觀的對峙,因此天然具有啟蒙的性質。然而,事情的復雜之處在于,并非一切歸于現代的價值觀便天然正確,啟蒙本身也需要時時反省。即如兩性關系,許老師經常以魯迅等作家的思考為例,言簡意賅地概括出古往今來男人控制女人的三種方法:第一是關起來,用這種野蠻的手段將女性和其他男性隔離;第二是養起來,通過物質籠絡使女性離不開自己;第三是教化,如嵌入芯片一樣,將貞節等觀念注入女性的大腦。大而言之,現代男性知識分子對女性的啟蒙,其實也屬于第三種情況,但通過細讀魯迅《傷逝》、茅盾《創造》和郁達夫《春風沉醉的晚上》這三個短篇小說,會發現啟蒙帶來的結果相當復雜,有時以被啟蒙者為犧牲,有時啟蒙者反而被拋棄,有時啟蒙者卻需要被啟蒙。再聯系知識分子對普通民眾的啟蒙,也是如此。因此,對于“五四”以來以魯迅為代表的啟蒙者,他們的啟蒙事業成效如何,實在不可以簡單判定。既然如此,對于某些作品中或現實中人們的一些“庸俗”價值觀,似也不必責之過苛。譬如,《第一爐香》中的葛薇龍囿于人性的弱點面對物質誘惑而逐漸“墮落”(與之相似的還有《日出》中的陳白露與《啼笑因緣》中的沈鳳喜),現實中一些香港的女孩子以“嫁入豪門”為人生理想,一個確立了男女平等現代價值觀的知識分子,固然可以不認可她們的選擇,但似乎也不必對之義正辭嚴,大加撻伐。從許老師的課上,我感覺他對于許多人和事都抱以理解和寬容的態度,從來不會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去臧否人事,就算有時批評某些現象,也絕不會疾言厲色,而通常面帶笑容,以微諷的言語出之。在他的課堂上,充滿著輕松平和的氣氛。
許老師絕不是一個沒有立場的知識分子,他也從不隱瞞自己的立場,然而他能理解并接受與自己不同的立場。以知識界比較敏感的“左”、“右”而言,無論在課堂內外,他都正視這一問題。譬如對于現代的一些代表性作家,他認為講革命的陳獨秀是“左”,講改良的胡適是“右”,包括“現代評論派”和“新月派”,而以周氏兄弟為代表的“語絲派”則夾在“左”和“右”的中間。“文學研究會”比周氏兄弟更“左”一點,但總體上還是中間派,比如茅盾、巴金、老舍等。對于不同派別的作家,他并沒有厚此薄彼。現代文學研究界一般知道他對于郁達夫和張愛玲有過開創性的深入研究,但事實上他可能對于魯迅的喜愛更多一些,只是他的研究成果還沒有大量面世而已。從社會政治上而言,對于“左”、“右”,他自己的立場是什么呢?他曾開玩笑說,在“鏘鏘三人行”的三人組合里,梁文道坐在左邊,強調平等,關心弱勢群體;他坐在右邊,最關心自由價值;竇文濤坐在中間,強調博愛,左右兼顧。三個人恰好代表了法國大革命的三個精神。這么說來他有點自視為“右”了,然而他同時強調,左派和右派都是中性的,動機都是善良的,都是希望達到社會的平等;左派注重結果的平等,右派強調機會的平等,一個社會有左、右派之爭,其實是社會健全的標志。而他和人的交誼,并不以左、右為分,不管“左”和“右”,只要有真的信念就好。他的這種平和心態與多元價值觀,來自豐富的人生閱歷和跨文化體驗。從青年時期開始,他當過工人,學過工科和文科,先后在上海、芝加哥、洛杉磯、香港長居,經常參與北京、深圳、廣州等地的文化活動,對于不同的制度、文化和價值觀,能在比較對照中同時看到其優劣,因而能形成較為通透達觀的看法,而不會陷入偏執狹隘的境地。
早在1984年,許老師就以一本新見迭出的《郁達夫新論》蜚聲學界,其時他剛到而立之年,任教于華東師范大學,是當時全國中文系最年輕的副教授。求實創新是他從事現代文學研究的最大特點,他的課堂的高質量主要來源于自身對作家作品的獨到研究。許老師的課堂深入淺出,常有四兩撥千斤之效,除了視野廣闊,他的另一個竅門是將課堂變得生活化,常通過打比方和類比等方式,結合香港學生的生活經驗分析文學作品。譬如分析阿Q的精神勝利法的幾個層次,他會聯系學生填報志愿與高考錄取、面對“半瓶水”的不同態度進行說明。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對凌淑華短篇小說《繡枕》的分析。他說,“繡枕”是一個含義深刻的意象,凝聚著女性的“三從四德”,凌淑華通過這一意象,對中國傳統女性將一生幸福系于渺茫婚姻的命運表達了深深的哀悼。然而反過來說,這篇小說本身不也是凌淑華的“繡枕”嗎?她因此獲得了老師陳西瀅的愛情和幸福的婚姻。同樣,張愛玲的《封鎖》也是一個“繡枕”,由此引來了胡蘭成的關注。而今天的不少女性把命運建立在自己的臉上、身體上甚至通過整容手術來爭取幸福,這個社會百年以來到底在進步還是退步?
在許老師的課堂上,聽眾感知到的是一部活的文學史。文學是人學,文學史即是人的活動史與精神史,作為文學的創造者,作家們本身也如常人一樣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樂,他們的為文與為人密不可分。許老師的課堂是名副其實的文學課堂,洋溢著文學性,充滿著他對文學的個人感悟。毫不夸張地說,中文系的師生要和作家一樣具有“文心”、“詩心”,才能進入作家的文學世界。文學研究畢竟與“科學研究”不同,它關注普遍的人心、人情和人性,對文學的理解建立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一基本前提下,幾乎無時無刻不需要讀者調動自己的人生經驗以產生對作品的共鳴。以此,有過創作經驗的讀者,會相對更容易地理解作家的創作。許老師曾寫過小說和長篇回憶錄《廢鐵是怎樣煉成的》,可以說深諳創作之道,因此他常常能從創作的角度提出自己對作品的一些特別的理解。
在文學性之外,許老師的課堂又具有強烈的文學史的現場感。作為一名五零后學者,他雖然沒有親身見證現代文學三十年發展的歷史,但是卻在當代有緣“邂逅”了一些現代文學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他常在課堂上分享這些寶貴的人生經歷,無形中拉近了聽眾和文學史的距離。我印象較深的有他這樣幾件事:一是他1990年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求學時,常常把車停在一個路口,多年后才知道當年深居簡出的張愛玲就住在那條街上的一個公寓里,他當時正在寫《張愛玲小說和上海小市民社會》這樣的論文,多次經過張愛玲居住的街道,卻從來沒有看見過她。二是他1989年在德國偶遇著名美術大師劉海粟,聽他談了一下午好朋友郁達夫的故事。三是在王映霞晚年時,許老師去看她,聽她說過一句話:郁達夫這個人可以做朋友,不能做丈夫。四是1985年他參加一個紀念郁達夫的會議,目睹會議主持人夏衍動了真情,當眾懺悔,說“左聯”當年太“左”了,對郁達夫很不公平。此外,他還和現代作家許杰相識,和晚年的巴金通過信,通過撰寫《辭海》相關條目為郁達夫等“平反”,他的父親是瞿秋白的學生,也是和戴望舒、丁玲的同學……他和現代文學的關系如此之近,應是那代學者中屈指可數的幾人之一。至于他講起自己在“文革”中把茅盾的《蝕》當黃書看,上大學時從郁達夫《日記九種》里抄情書,也都是有趣而引人思考的故事。學生能在課堂上通過這種方式感知現代文學,無疑是一種難忘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