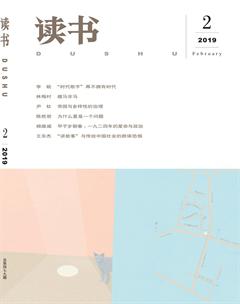“中心”與“邊緣”之間
王麗娜
對中國進行的研究,特別是在區域視角下的研究,經歷了一個視角不斷切換的過程。其中總體的趨勢是從中心轉向邊緣,旨在形成一種從邊緣看中心的視野。中原中心論、朝貢體系(費正清)受到“漢化”的質疑,常被指責為僅僅依靠中心出發的視角難以認識中國歷史的全部圖景。而對邊緣的發現以及從邊緣視角出發,則可能發現中國歷史新的發展動力與機制,這深受國外族群與區域研究的啟發,其中新清史所強調的族群特性與“滿洲中心觀”,更是將邊緣視角上升到國家建構的高度。在此之前,拉鐵摩爾對亞洲內陸邊疆的研究,以及對云貴地區“邊緣的、地方的、土著的視角”研究,都集中體現了邊緣視角的深度與價值。從邊緣出發,實際上隱含著對中心的對比與觀照,對邊緣的審視,則是呈現出對邊緣區域文化多元性與復合型的考慮。而在中心與邊緣之問,實際上還存在著一個過渡地帶,這一地帶連接著核心區域與邊緣區域,其中的典型便是漢藏之間的康區。這一區域如此之豐富,吸引學者們在這一區域作業,并提出各種概念來描述這一區域。
概念與表述
在中國歷史與地理語境中,中間地帶可以說有著具體但是十分豐富的含義,一般被視為處于農耕與其他生計方式混雜交會的區域,其中以青藏高原以東的區域最為典型。這是二、三階梯的過渡地帶,是農牧混雜區域,行政區劃變動不居,經濟上溝通漢藏,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交流交融的典范,同時又存在著頻繁的民族沖突,其歷史過程基本上可以總結為從內陸邊疆到民族地方的演進。
對這一地帶的整體或者部分,學人們提出了各種表述概念,雖然在區域范圍與概念所指上存在一定的差異,但都總結出了該地帶的基本特征。童恩正從考古發現的角度提出了從東北到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這道傳播帶由長城地帶和藏彝走廊兩部分組成,是華、戎集團的文明分野,是諸多族群相互交往、滲透的文化疊加帶,呈現了從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文化傳播的空間形態。拉鐵摩爾將長城地帶視為“貯存地”,是農耕王朝與游牧帝國互動的軸心地帶,從中可以發現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費孝通提出藏彝走廊這一歷史一民族區域概念,旨在宏觀上指出板塊是以走廊相連接并形成地理與文化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過程與動力,其中著重指出了走廊所具有的相對流動的特征。其后,王明珂所描述的“華夏邊緣”以及所界定的“羌在漢藏之間”,強調了華夏族群邊緣的維持與變遷,特別是邊緣人群如何借歷史記憶與失憶來成為華夏或“非華夏”。王銘銘受藏彝走廊概念的啟發提出“中間圈”的概念,指出中間圈是介于核心圈和外圈之間、“半文半野”的過渡地帶,這一概念涵蓋拉鐵摩爾提出的內陸邊疆地區,也包括西南的藏彝走廊和東南的部分少數族群,對中間圈社會與人群的討論,則是強調不同圈層與區域之問的互動以及這一互動本身的聯結與重塑意義。魯西奇受許倬云有關中華帝國體系結構的啟發,將“處于中華帝國疆域內部,卻并未真正納入王朝國家控制體系或國家控制相對薄弱的區域”稱為“內地的邊緣”,認為在這一區域,國家權力相對缺失,民眾生計方式多樣,社會關系網絡具有強烈的“邊緣性”,非正統意識形態影響較大。敏俊卿將回族置于漢藏區域之間,將之稱為漢藏之間的“中間人”,描述這一中間群體的雙向互動過程與獨特認同。
就更大范圍和更為理論化的視野來看,“中間地帶”這一類型的區域不是中國所特有的,其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對這類地帶國外學者們也進行了概念提煉與特征分析,并且進行理論化,形成了具有啟發意義的概念工具。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特納的邊疆論,特納認為邊疆是文明與野蠻交會的地點,這一概念后來被美國邊疆歷史學派發展成為“文化接觸帶”(zone of cultural c nntact),用以描述不同文化在特定空間內的接觸與互動。美國學者理查德·懷特在其著作《中間地帶:一六五〇至一八一五年間大湖區的印第安人、帝國與合眾國》中,提出了“中間地帶”(Middle Ground)的概念,旨在討論印第安人與法、英、美等外來者的互動,其中將印第安人置于中心地位,呈現出一個在互動中形成的跨文化、跨區域、多語言的中間地帶。瑪麗·路易斯·普拉特的《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文化互化》從后殖民的角度,描述了不同文化彼此遭遇、沖突、格斗的空間,也就是“接觸地帶”(conlactzone),其中主要是著眼于文化書寫與文化互化。
中間地帶作為特殊的地理、社會與文化空間受到了廣泛的關注,雖然區位與所指向的重點不同,所提煉出來的概念也各式各樣,但是對于這一類區域關注的旨趣確實基本一致,都是描述兩個或者多個群體及其文化在這一空間地帶內的碰撞與互動,并探索其中的動力及其機制。這些概念,大都成為影響廣泛的理論工具。最近對康區這一漢藏中間地帶的討論成為一個熱點,出現了非常具有深度的著述,其中以鄭少雄《漢藏之問的康定土司》與王娟《化邊之困》為代表。其中,鄭少雄主要關注康定這一漢藏之間區域的核心,通過梳理康定明正土司的人生史來考察這一區域內外政治與族群關系,而王娟的《化邊之困》則是將康區視為漢藏之間的交互地帶,著眼于這一區域從“王朝藩籬”到“民族地方”的過程,其中對康區的內外結構、歷史過程的描述更為宏觀。可以說,這兩本著述將對康區這一中間地帶的研究推向更加深入細致。
內與外
中間地帶的特殊性就在于,在地理、政治、社會與文化等方面處于兩個或多個區域之間,在外部受到來自雙邊的影響,而在其內部由于其地理與生態的原因,形成特定的族群分布與社會形態,表現出內部的多元性。外在地位與內部結構的交互作用,使得中間地帶呈現出復雜的圖景。漢藏之間的康區,即是這樣的中間地帶。鄭少雄著重討論的是作為漢藏中間地帶的經濟與政治中心康定,而王娟則是將整個康區置于視野之內,視角的不同,也就呈現出對這一區域的不同認知。
鄭少雄旨在通過對康定土司的討論,驗證并發展出一種關于中間地帶的社會形態與人物命運的理論。他將康定土司的人生史放置于明正土司家族史、康定歷史以及土司、康定與外部世界三者之間交往互動的歷史中來考察(《漢藏之問的康定土司》,39頁),實際上是討論土司所代表的社會的總體過程和內外、上下之關系。“康定作為漢藏交接地帶的地理、族群、社會生活的特征,尤其是由此催生的鍋莊、烏拉以及多樣化的宗教信仰等現象”,以及施行于此地近七百年的土司制度(《漢藏之間的康定土司》,7頁),使得康定表現出“文化復合性格”(王銘銘)和“權威中間性面貌”。康區所具有的生態結構的二重性使其成為一個區隔與聯系并存的區域。
康區的區域地位與內部特征,使得康定的土司制度呈現出一種政治二元性,表現為政治與宗教上的雙重代表性,“拿起鈴鐺是活佛,放下鈴鐺是土司”。這也說明了,土司的權威來源遵循著一種外來者一王的模式,并且具二元性,一元來自漢地,一元來自西藏,是“世俗權威與宗教權威的結合”。康定“位于漢藏兩個權力與文化中心之問,‘土司一寺院的‘兩翼體系構成了土著社會內部的統治結構,‘政治的東向性與宗教的西向性塑造了其基本的文化特質與行為邏輯”(《化邊之困》,29頁),并且,政治二元性使得土司在左右逢源的同時,也帶來了結構上的張力,突出表現為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呈現出一種近似利奇所言的鐘擺過程。
鄭少雄以鐘擺循環來描述康定土司社會的結構,暗指土司與雙邊都發生關系,但是自身表現出相當的獨立性,而其隱含的語義則是康區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內部存在著基本的一致性。王娟對此提出批評,從對康區概觀的角度,認為康區土司社會事實上是一個高度分割的社會,政權結構大部分都呈現碎片化的狀態,土司之間存有競爭,并且其認同結構是以部落為核心的。在很大程度上,對于土司真正構成威脅的往往不是東西兩側的皇帝和喇嘛,而是其周邊相鄰的土司及其手下的頭人(《化邊之困》,114-115頁)。這樣,康區這一中間地帶的內部結構,呈現出基于內部生態和歷史傳統而形成的“土司社會”的碎片化政治格局,寺廟在其中也是參與合作并對土地、人口與利益形成競爭的行動主體。這種情形,不僅決定了內部的競爭關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其與西藏和中原交互的邏輯,集中體現在如何與“外部周旋”而借力,以實現在康區眾多土司中的權力。而中原與西藏在康區施加影響也是利用了康區土司與寺廟之間的關系,選擇性地進行扶持與打擊。
這樣,康區的內部結構與外在地位及其互動,就通過“內部競爭”與“外部周旋”相結合的基本邏輯勾連起來,康區作為中間地帶所蘊含的價值也就凸顯出來了,一個有限的區域卻容納與聯結了如此廣闊的世界。借用汪暉所提出的“跨體系社會”概念,康區這一中間地帶實際上也是一個跨體系社會,“經由文化傳播、交往、融合及并存而產生的一個社會,即一個內含著復雜體系的社會”(汪暉:《中國:跨體系的社會》)。因此,要在一個更大視野內來觀察康區,不僅是描述康區與中原、西藏之間的互動關系,而是要深入到康區的內部,發現其內部的結構性特征,這樣理解康區內部政治運作的邏輯,才能更好地認識康區與兩側之間的權力關系。
變與不變
與利奇對克欽、拉鐵摩爾對游牧與農耕的循環描述不同,康區與漢藏的互動實際上始終處于變動之中,這樣康區的歷史就具有了時間性的變遷。但是另一方面,康區的地理與生態基礎又決定了康區內部結構的穩定。正如鄭少雄指出的那樣:“土司地區消失意味著漢藏之間廣闊的歷史緩沖帶的消失。”(《漢藏之間的康定土司》,3頁)但同時“作為一種看得見的制度,土司消失了,但土司的威力似乎仍在起作用”(《漢藏之間的康定土司》,8頁),這實際上揭示了康區作為中間地帶在時間性上的變與不變。
王娟更加注重對康區歷時性變遷的討論。所謂“化邊”,就是在新的國家體制中給“邊疆”和生活在這里的“少數民族”尋找一個“合適的位置”的“改造邊疆”的過程,著眼于變化與變遷。王娟從行政體制建設、身份改革與社會控制、移風易俗、人群分類等方面討論了在時局變化的情形下,國家改造康區,使其實現內地化的過程。事實上,這種變化表現在多個方面,在人群上,土著一外來與中央一地方的交叉就形成了傳統流官、新式地方官、舊式土著精英、新式土著精英等群體,而這些群體的更新則表現了康區變化的復雜過程。
康區這一中間地帶的變化,實際上是國家加強對這一地帶控制而引發的,使其從前民族國家時代的“王朝藩籬”轉變為民族國家的“行政單元”。其中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在現代國家的原則下,它需要將‘國家的力量推進到這些原來以‘封建形式存在的邊疆社會,在統一的國家內建立同一化的行政體系。另一方面,它需要通過這些‘過渡地帶的‘內地化,加強與再外一層的外蒙古與西藏的聯系。”(《化邊之困》,8頁)但是,這并不是一個順利的過程,而是面臨著諸多曲折與反復。“‘化邊代表的是來自國家中樞的努力,它是一項白秦漢實現大一統起就開始的改造邊疆、整合邊疆的實踐,而‘困則反映了邊疆社會的自然、人文環境對上述努力的抵制。”(《化邊之困》,12頁)這實際上是貫穿于兩千年間兩個不同方向的運動,而在近代以來開始發生新的變化。
但是無論如何,經過了晚清、民國以及共和國建國初期的斗爭、改造、建設與分類,康區的面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在國家行政層面,康區被置于省州縣行政體系之下,康區的土司社會得到系統改造,人群也經由識別形成特定身份的民族,原來的內地邊疆成為民族地方。而在其中,個人命運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康定土司失去了其領地與權力,但是其權威猶存。
事實上,對于康區這一中間地帶的考察,更為重要的不是討論其在歷史過程中發生的變化,而是發現在經歷過長時段的變遷過程之后,依然沒有發生變化的那些方面。鄭少雄看到,康定土司制度雖然已經廢除,但是土司本人的權威依然在。而王娟指出,雖然“化邊”取得了極大的成效,但是其中的曲折反復以及表現出的困境,則說明了康區自身地理與生態基礎的決定意義。
即使是在今天觀之,依然也會發現,雖然經過近代以來的劇烈變遷與長期改造,康區作為中間地帶的特征依然存在,其“邊疆”形象依然清晰,而且有力地反抗著以“國家”為主導的“均質化”改造(《化邊之困》,433頁)。康區在今天依然是漢藏之間的交接地帶,依然面臨著邊疆內地一體化的任務,“治藏必先安康”的戰略依然有其適用性。而在其內部,則依然保留著經濟、文化與宗教等諸多方面的多元性,宗教、宗族勢力依然有著重要的影響,仍然存在著由于草場等資源競爭而引發的械斗,這些都說明康區這一中間地帶自身的穩定性。而這些,實際上都是由康區的外部地位與內部結構所決定的。隨著經濟發展與文化交流的頻繁,這一中間地帶將會呈現出新的變化。變與不變,是結構性與時間性的角力,但是康區作為中間地帶的基本特征不會發生變化。
價值與意義
如沃勒斯坦所言,十九世紀以來民族國家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單位,研究的空間范圍或者是國家界定的社會,或者是國家劃定的行政區域,然而在民族國家的視野之外,實際上存在著一些聯系更為有機且密切的區域空間。施堅雅擺脫行政區劃局限而以市場為基礎的區域研究理論,則呈現了這一取向的潛力,費孝通先生“藏彝走廊”歷史一民族區域的提出,也表明了這一視角的意義。對中間地帶的探究與認識,實際上體現著經驗與理論的交互,一方面對中間地帶進行深入細致的描述,可以提供這一區域的全部圖景,另一方面則是對中間地帶的區域現象進行理論上的總結與抽象化,這樣可以形成具有一定解釋力的分析視角。中間地帶不僅意味著區域與區域之間的聯系,而且也意味著國家與地方之間的連接,從而能形成對該區域以及區域之間關系的深入認識。
康區這樣的中間地帶,在實際上超越了民族國家的預設局限,揭示出更為豐富的互動關系。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其主要意義則在于更好地認識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動力與機制。其中的關鍵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不僅在于中心與邊緣的互動,而且還在于中心與邊緣之間中間地帶的連接,這一地帶實際上形成文明問連接的連續統,其內外互動與連接機制有著特殊的意義。對中間地帶的發現,實際上就是對中國歷史的再發現、再敘述。
(《漢藏之間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鄭少雄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一六年五月版;《化邊之困:二十世紀上半期川邊康區的政治、社會與族群》,王娟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一六年六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