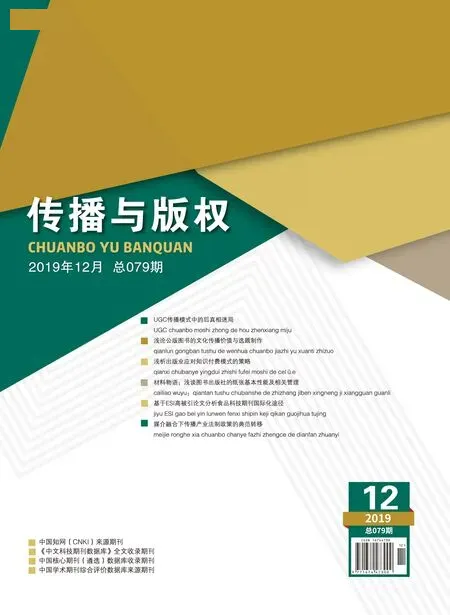從“重慶公交車墜江”事件看網絡輿情
吳怡雯
(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江蘇 南京 210000)
新媒體的迅猛發展,打破了原有的媒介生態環境,裂變式、碎片化的傳播方式改變了傳統媒體的新聞生產方式和呈現方式。最近幾年,經常會發生新聞反轉。部分媒體為了“搶先一步”報道新聞而不顧其“真實性”,然而隨著事件的發展,真相逐漸曝光,這樣的新聞反轉勢必會造成輿情反轉。這一過程,是對公眾情緒與注意力的消費,同時削弱了公眾對媒體話語的信任和敬畏,因此我們不得不去反思這一傳播現象。
一、研究問題與方法
(一)案例選擇
2018年10月28日10時,重慶市萬州區長江二橋一輛公交車與轎車相撞后,公交車沖破橋面護欄掉入江中。事故發生后,多家媒體在報道時均帶有“小轎車女司機逆行”等字眼,一時間此事件在輿論場迅速走高。當天12時,重慶警方官微@平安萬州發布事故通報。17時許,@平安萬州再次發布通報,確認系公交車在行駛中突然越過中心實線,撞擊正常行駛的小轎車后墜入江中。10月29日14時,@人民網發表微博稱,墜江公交車初步核實15人失聯,車輛位置基本確定。30日晚,據CCTV13頻道報道,潛水員在失事公交車內找到了黑匣子。31日23時,@新華視點報道10月31日晚交通運輸部門將車體打撈上來。隨后有媒體爆出救援隊副隊長周小波父親也在遇難公交車上。除此之外,大量關于遇難者的消息被報道出來,引發了又一次熱議浪潮。11月2日10時34分,@頭條新聞公布黑匣子視頻,引發了網友的新一輪熱議。
“重慶公交車墜江”事件是突發事件,主流媒體關注度高,報道迅速,事件持續了11天15小時,期間平均傳播速度為183條/小時,峰值傳播速度高達2020條/小時,但部分媒體在輿論發酵階段缺少對信源的核實,因此發布了部分不實信息。同時,微博中輿論持續發酵時間較長,范圍較大,出現了短時間內明顯的輿論“反轉”現象。
(二) 測量方法
本文采用內容分析法對搜集到的數據進行深入研究。內容分析是一種集定量和定性為一體的研究方法,適用于對大量的文本數據進行分類處理,并從中發現規律、提煉概念,進而厘清變量或主題之間的邏輯關系。[1]
以“重慶公交車墜江”作為關鍵詞在清博輿情平臺上檢索,截至11月5日20時,共檢索到相關信息88200條,其中微博59029條,網頁11120條,微信7643條,客戶端7595條,論壇2356條,報刊431條。由此可見,在媒介分布中,微博為主要陣地,其他占比相對大的還有微信、網頁、客戶端等。
該事件中,輿論的焦點經歷了“輿論審判女司機逆行”“倒戈批判主流媒體及大V”“議論吵架乘客、質疑公交司機”和“質疑其他乘客的袖手旁觀”這四個階段。本文在微博平臺進行高級搜索(關鍵詞:重慶公交;類型:熱門)得到不同階段的相關微博,根據評論數量進行排列,選取每一階段排名在前5的微博進行分析。本文對評論采取隨機抽樣、配額抽樣相結合的抽樣方式,排除無關或無實質性內容的評論,得到每階段評論樣本250條,樣本總量共1000條。
再將四階段的樣本評論導入質性分析軟件NVivo 11做進一步處理,通過詞頻分析、節點分析、關系模型等功能進行深度闡釋和理論挖掘。
二、數據分析:輿論反轉現象的呈現
該事件中輿論出現了兩個高峰。第一個高峰是在10月28日事件剛發生時,一些主流媒體發布“女司機逆行導致事故”的虛假信息,輿論對“女司機”進行道德“審判”。而在28日17時46分,@平安萬州發出官方警情通報“系公交行駛中突然越過中心實線,撞擊對向正常行駛小轎車后墜江”。此外,在29日中午,被撞小轎車后車的行車記錄儀的視頻公布,輿論開始倒戈批判發布虛假信息的“主流媒體”和“微博大V”。第二個高峰是在11月2日“乘客與司機爭執導致事故”的原因發布之后,網民開始議論吵架乘客、質疑公交司機和袖手旁觀的其他乘客。
(一)反轉前:輿論審判女司機逆行
事故發生后,各大網絡媒體迅速在微博上發聲,一時間,此事件在輿論場迅速走高。根據微博高級搜索和評論高低排名,本文抽取了這一階段排名前五位的微博及每條微博下的50條隨機評論(共250條)。統計發現,微博媒體多采用“文字+視頻”的形式,且標題均帶有“女司機”“逆行”等詞,體現了媒體對女司機的譴責態度。
在250條網民評論中,有35%的網民表示揪心難過、祈禱救援順利,發表了“心好痛”“絕望”“保佑平安”“先救人”等內容。有15%的網民提出了“護欄為什么不起作用”“突發事故怎么自救”以及其他發散式話題。而網民最集中的議題則是對女司機的討論,37%的網民發表負面評論,猛烈譴責女司機,包括對事故原因的討論猜測,比如“逆行”“高跟鞋”等,以及對女司機的輿論道德審判,帶有較強的辱罵性和諷刺性。另有13%的網民媒介素養較高,保持著理性、中立的態度,認為媒體不應有性別歧視傾向,網友也不應該以性別說事,并呼吁在突發事件面前要不傳謠、不信謠(見表1)。這一階段是事件突發不久輿論開始形成的時期,網絡媒體對于微博網民的態度和議題有顯著影響。
(二)反轉后:倒戈批判主流媒體及微博大V
28日當天17時46分,@平安萬州發出官方警情通報“系公交行駛中突然越過中心實線,撞擊對向正常行駛小轎車后墜江”,網友對女司機的態度開始搖擺、轉變。29日中午12時17分,被撞小轎車后車的行車記錄儀的視頻公布,網上一片嘩然,輿論開始倒戈批判發布虛假信息的“主流媒體”和“微博大V”。這一階段,微博媒體多采用“文字+視頻/圖片”的形式,部分媒體的內容關鍵詞是“小轎車正常行駛,車上共10多人”,既傳達了關于墜江車輛的信息,也對事故原因做了澄清,但也有媒體對“女司機”只字未提。事實真相發生反轉后,輿論集中在對女司機的道歉和對事故原因的追問兩方面。在250條網民評論中,40%的網民向女司機表示同情與歉意,有少數是為自己之前譴責女司機的行為而自我反思;而更多的是要求媒體道歉和譴責網絡暴力,網友認為媒體傳播了錯誤信息,導致小轎車司機被冤枉了一天,小轎車司機不僅是車禍事故的受害者,還是可怕的網絡暴力的無辜承受者。
當確定小轎車司機不是肇事者后,網友的一部分注意力逐漸轉向事實真相上,開始詢問事故原因,表示“想要現場視頻”“想知道車內發生了什么”。與此同時,還有14%的網友仍是祈平安,評論數量較上一階段有所減少,而且出現了諸如“大海撈針”“希望渺茫”“逝者安息”等消極態度。此外,還有少數其他評論,如“護欄沒起作用”“沒有隔離欄”以及其他發散式話題(見表2)。

表1 反轉前網民的評論

表2 反轉后網民的評論
短短十幾個小時,輿論就出現了急劇的反轉。這種輿論極端化逆轉與網絡媒體態度傾向的轉變密不可分。
(三)議論吵架乘客、質疑公交司機
11月2日10時34分,被打撈起來的黑匣子的視頻公布,曝出公交車墜江原因:乘客與司機爭執互毆致車輛失控,這引發了網友的新一輪熱議。這一階段,微博媒體仍采用“文字+視頻/圖片”的形式,議題較為統一,是重慶公交車墜江調查的公布。
監控被公布后,網民的討論集中在“誰來承擔事故責任”這一議題上。有41%的網民認為公交車司機應承擔主要責任,提出“為什么不停車”“為什么急打方向”等質疑,甚至有人猜測是“想同歸于盡”“想嚇一嚇乘客”;有11%的網民認為打人乘客應承擔主要責任,并作出“沖動是魔鬼”“作死”“撒潑”等評價,并回憶以往同類事件,宣泄不滿與譴責。
其他的評論話題較為零散,有對事故遇難者表達哀悼之情的,有對事故防范提出建議的,有討論法律、規則缺失的,也有仍在提及小轎車女司機的……此時,事故真相已查明,信息傳播主體開始多元化、網絡化,媒體議程對于網民議程仍有影響,但相關性比前兩個階段弱了不少,網友的討論更多的是從情感認識角度出發,呈現出個性化、失控化趨勢。
(四)質疑其他乘客的袖手旁觀
當到“到底是公交司機的問題還是打人乘客的責任”的討論逐漸冷卻時,質疑其他乘客袖手旁觀的聲音開始出現。不少網友認為車內不阻攔不作為的乘客也有一定責任,“雪崩之下,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如果有人上前攔一下,或許悲劇就不會發生。但也有網友表示,事故已經發生,愿逝者安息生者警醒,當下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實質性地減少這類事件的發生,如何在突發事故中自救逃生。
這一階段,傳統媒體的議題較多,有對事故救援的后續報道,有對整個事件的回顧,還有對自救知識的梳理等。自媒體或者微博大V則是集中討論事故原因、責任承擔、法律適用等。無論是網民還是媒體,情緒化聲音慢慢消散,理性開始回歸。
三、輿論反轉的因素討論
(一)新聞生產:話語競爭與議題驅動
有學者指出“傳統媒介的典型特點在于:信息傳輸的起始點決定一切”[2],因為“信息傳播者憑借其強勢的話語權,能夠依據社會發展的需要有效設置議題和引導輿論”[3]。但是,很多記者為了搶新聞而不顧事件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就將信息傳播出去,里面充斥著記者情緒化的判斷,包含著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來源。“技術革新讓新聞事業的傳播速度更快和傳播渠道更加便捷,但新聞與生俱來的兩大特點‘真實’與‘新鮮’之間的矛盾卻明顯加劇。”[4]“重慶公交車墜江”事件中,在@平安萬州發布政府官方消息之前,各大網絡媒體搶發不實報道,引發了網民對“女司機”先入為主的譴責與咒罵。
在新聞反轉之前,“女司機逆行”之所以能引起大規模的網民討論,在于該議題背后存在著較為深層的社會問題。有學者提出“女司機逆行議題涉及女司機這一日常生活中飽受詬病的群體,事關駕駛安全、駕駛文明這樣的公共話題,容易引爆網民尤其是男性網民的某種社會情緒”[5]。因此,在行車記錄儀曝光之后,原本飽受譴責的“女司機”立即獲得輿論的“無罪釋放”,公眾積壓的對“女司機”的批判迅速轉移到對媒體的不滿。
(二)新聞傳播:媒介共鳴與輿論領袖
有學者提出“當多數傳播媒介報道內容類似,同類信息連續和重復傳播時,媒介之間就會產生共鳴效果”[6]。“共鳴效果是指主流媒體在新聞報道時充當了意見領袖作用,其他媒體根據主流媒體的話語指向進行轉發或后續報道。主流媒體在信息傳播中的主導地位決定了媒體報道容易產生連鎖反應。”[7]在這一事件中,@新京報@華西都市報等權威傳統媒體發揮了主要作用,其他主流媒體如@新浪新聞@騰訊新聞等跟風報道,并引發了非主流媒體、微博大v等的大量轉發。
此外,作為二級傳播節點的輿論領袖,憑借較大的受眾群和社會影響力,通過對網絡媒體報道的評論、轉發等“二次傳播”,影響社群受眾的態度傾向,帶動更多的人參與事件之中,將事件迅速推至高潮。比如第一階段中,@老徐時評論在事故發生后的兩小時就發表了“女司機逆行致車禍”的言論,其下有3000多條評論,網民評論與其情感態度較為一致。
(三)新聞接收:刻板印象與網絡暴力
有學者提到“戈夫曼提出的框架理論指的是人們用來認識和解釋社會生活經驗的一種認知結構,這種框架預設能夠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確定和命名那些看似無窮多的具體事實”[8]。在大眾的印象中“女司機”是一個污名化的標簽,一旦路上遇到不按規矩行車的司機,便將其貼以“女司機”的標簽。根據阿爾塞爾羅德的基模理論,新的信息若與某些舊描述相吻合,則會強化原有基膜的作用[9],且這種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不受現實中實際數據的影響。
這種對“女司機”的不滿情緒不斷累積,從個人情緒演變成社會情緒,任何一個關于“女司機”的負面報道都會成為這一社會情緒爆發的導火索,而“重慶公交車墜江”這一突發事件便成了社會情緒宣泄口。

圖1 輿論反轉過程
四、應對與調控措施
第一,堅守原則,將新聞真實性放在首位。有學者提到“美國新聞從業人員譽為職業圣經的《新聞的十大基本原則》一書中,開門見山第一條原則便是:新聞工作首先要對真實負責”[10];在國內新聞教育的傳統中,我們也重視真相與細節,因為“真實是新聞的生命”[11]。所以,媒體的首發信息要確保真實全面,不能為了搶一時風頭而片面設置議程。
第二,媒體自凈,主動糾偏監督網民輿論。在熱點事件發生后,媒體不應輕信所謂的權威媒體而不加核實地轉載、引用,這種消極態度的媒介共鳴是新聞傳播者的失責。網絡媒體應該持續關注事件進展,從多方信源核實信息,主動打擊網絡謠言、糾正錯誤信息。
第三,理性社交,網民自我提升媒介素養。在高速發展的數字互聯網時代,社會輿論場擴展了前所未有的表達主體和多元化意見,公民意識不斷覺醒。每個人都有發聲的渠道,但網上所展現的媒介素養是參差不齊的。這就要求受眾需要提高自身的媒介素養,不偏聽小道消息,不盲信網絡謠言,不傳播未經證實的言論。
雖然有人提出“數字鴻溝”在這個時代似乎是逐漸擴大的,但我們仍然能看到,在一次次輿論反轉的過程中,在信息與觀點表達所帶來的沖擊下,參與者或是旁觀者在無形中接受了網絡傳播素養的自我教育,媒介素養得到一定程度的培育、鍛煉與提升。
“重慶公交車墜江”事件的輿情一波三折,其新聞報道與輿情反轉,都遠超人們想象與控制。“輿情反轉”現象背后被消費的是新聞機構的公信力,因此,媒體必須在新聞事件中,尤其是輿論熱點事件中平衡好“真實性”與“時效性”,進行積極適當的引導,努力構建有序的輿論場和報道機制。同時,網民也應不斷自我提升媒介素養,不偏聽、不盲信、不傳謠,保持理性,不當“烏合之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