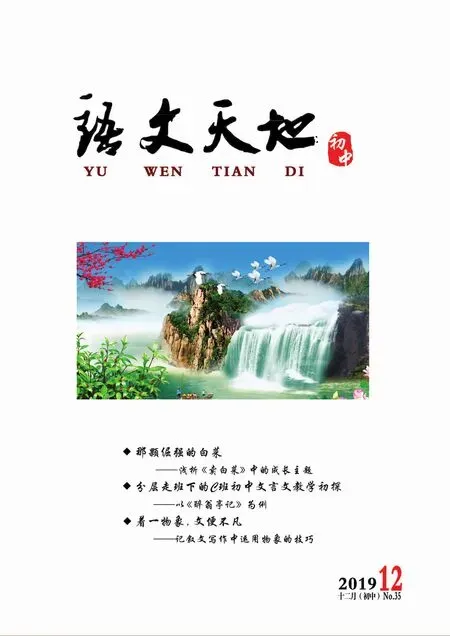單向度閱讀教學糾偏
所謂單向度閱讀教學是指在閱讀教學過程中,只是圍繞文本開展單一、呆板的閱讀教學,往往有以下一些表現:只有積累,沒有思考;只有吸收,沒有傾吐;只有理性的分析,沒有情感的熏陶;只有贊美,沒有質疑和思辯;只有呆讀,沒有以讀導寫;只有唯一,沒有舉一反三的聯想和印證。
這樣的教學往往造成低效的閱讀教學,學生會漸漸喪失閱讀興趣,語文素養缺失等問題。那么,如何避免出現這樣的閱讀教學行為呢?
“不立則不破”,我們應該建立正確的閱讀教學觀,形成正確的閱讀教學行為。
一、關注興趣、尊重獨特
《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指出:“閱讀是學生的個性化行為……要珍視學生獨特的感受、體驗和理解”,這體現了在教學中要以學生為本的教育思想。其中“珍視”二字體現了課程標準對學生獨特的感受、體驗,理解的重視程度。“珍視”是珍惜重視之意,不是一般地看待,不能忽視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一閃而過的靈感,更不能用簡單的參考答案去匡正、壓制學生的不同見解。“獨特”,即獨有的,特別的,它強調了個性化,是學生個體的生活經驗、知識積累和價值取向,教師切忌用教參的分析、結論來代替學生的閱讀體驗,削弱學生的主體地位。語文教學應注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事物的感受、對作者及作品中人物的情感體驗,密切聯系現實生活和自身的切實體驗。
讀書,特別是讀文學的書,最重要的是要有興趣,甚至可以說,需要一種兒童的好奇心,因為每一篇文學作品都會給你打開一個新的天地。或者是你完全陌生的,或者就在你習以為常的生活中突然有新的發現與開掘。在這個意義上,讀一本本、—篇篇的文學作品,就是一次次的精神探險。
閱讀教學要求學生們要懷著強烈的期待感,甚至是某種神秘感,走進課堂,渴望著與教師一起,闖入一片片文學“新大陸”,解開一個個文學奧秘。這樣,就會由“要我學”變成“我要學”,由被動的學習變成主動的學習”。當然,學習語文自然還有其艱苦的一面,準確地說,語文學習的樂趣正是在克服一個又一個困難,即所謂攀登一個個知識“高峰”的過程中實現與體味的。
教師的責任就在于以自己的人生體驗喚起青年學生的生命熱情體驗,用飽含情感和富有啟發性的語言,溝通兩條渠道:一條通向心靈,一條通向生活。心靈上相呼應,感情上能共鳴。
教學過程中,我總愛引用易卜生的話,“你的最大責任是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既然每個人都是宇宙中獨一無二的那一個,那么,你知道自己是最大的財富嗎?你知道任何礦產的資源都是有限的,惟有自己的財富是值得你終生開發,遠無止境的嗎?那么,不要害怕閱讀,不要只為了考試或者應付而閱讀,閱讀并快樂著,生活并快樂著。
二、熟讀精思、虛心涵泳
朱熹認為只有熟讀精思,才能對文章把握得深透,才能準確牢固地記憶。“大抵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之于吾之口;繼之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之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
“大凡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熟,精熟后理見自得。如吃果子一般,劈頭方咬開,未見滋味便吃了;須是細嚼嚼爛,則滋味自出,方始識得這個是甜、是苦、是辛,始為知味。”
朱熹不僅要求讀書要“成誦”,而且在成誦的基礎上還要反復誦讀,遍數越多越好。有研究者批評他的這種“讀書千遍,其義自見”的機械的讀書方法,但是,我們常說的語文學習“要死要活”,在精讀方面尤其是在中小學階段的確非常需要這種“死”,這樣才能積累豐富的語料。目前我們的語文教學中的“半死不活”“走馬觀花”的讀書方法是不利于語文學習的。潘鳳湘教師的教學,經常用七八課時學習一篇課文,效果很好。
語文教學需要處理好快與慢、死與活的關系。葉圣陶先生說:“一目十行地囫圇吞棗地讀下去,至多只能增進一些知識和經驗,并不能領會寫作的技術。要在寫作上得益處,非慢慢咬嚼不可。”
朱熹認為閱讀文章時要保持客觀的態度,以他說觀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已觀物,不能先入為主、穿鑿附會,以自己的主觀愿望去憑空猜測。在有疑時,更要虛心靜慮,不匆忙取舍。他說“讀書須是虛心,方得圣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前賢與諸家說便了。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個意思了,卻將圣賢言語來湊他的意思,其有不合,便穿鑿之使之合。”“至于文意有疑,眾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于其間。”
涵泳,就是要反復咀嚼,細心玩味,深刻體會書中的意趣。“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卒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目誦圣賢之書,而不識圣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杜撰成耳,如此豈復有長進?”
三、舉一反三、勇于批判
教是為了不教,閱讀教學是為了培養學生的自主閱讀能力。在課堂閱讀的同時,或者課外,可以引進一些與課文相關的文章的比較閱讀,一方面放手讓學生自主閱讀,起到歷練方法的功用,另一方面也可以拓展學生的眼界。
比如,讀了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狼三則》中的一則,就可以讀一讀其他兩則。其中《牧豎》篇引人深思、耐人尋味。
“兩牧豎入山至狼穴,穴有小狼二,謀分捉之。各登一樹,相去數十步。少頃大狼至,入穴失子,意甚倉皇。豎于樹上扭小狼蹄耳故令嗥;大狼聞聲仰視,怒奔樹下,號且爬抓。其一豎又在彼樹致小狼鳴急;狼輟聲四顧,始望見之,乃舍此趨彼,跑號如前狀。前樹又鳴,又轉奔之。口無停聲,足無停趾,數十往復,奔漸遲,聲漸弱;既而奄奄僵臥,久之不動。豎下視之,氣已絕矣。今有豪強子,怒目按劍,若將搏噬;為所怒者,乃闔扇去。豪力盡聲嘶,更無敵者,豈不暢然自雄?不知此禽獸之威,人故弄之以為戲耳。”
這樣的文章可以先引導學生理解語句的含義,以及文章的主旨。同時還可以進一步讓學生來批評。通過思辯和討論,同學們能夠發現,狼作為一種動物,似乎已經不是很純粹的動物,這個詞語被賦予了太多的罪惡,所以該文有一種思維的定勢,一種習以為常、不以為怪的惰性思維。同時,去掉狼的比喻意義,去掉這篇文章以狼喻惡的言外之意,當代中學生對于蒲松齡先生的冷漠感到的是一種震驚。牧豎得狼子,并且以此作為要挾母狼的王牌,“扭小狼蹄耳故令嗥”,這樣高明的方法足顯得人類這一靈長類的杰出才能。這樣的才能是什么呢?
恃強凌弱、陰險狡詐、冷酷殘忍,這些狼的一般習性在人的身上表現無遺。而這些在文章中卻被視為美德,作為大智大勇而受到贊頌。當然,現代人不能對古人過多的求全責備。但是,通過這一文章的比較閱讀,我們對于蒲松齡時代的社會思潮,對于人和自然的關系的認識應該有更多的思考和理解。
四、切已體察、學以致用
愛默生認為,創造性閱讀的本質應該是把自己的生活當作正文,把書籍當作注解,以活躍的靈魂為獲得靈感而讀書。在語文閱讀教學的所有習慣中,我們要高揚起“我認為”的大旗,讀經典名著。
語文學習必須避免讀死書,只在紙面上做功夫,要切已體察,學以致用。語文學習要密切聯系生活。這里包含兩層意思。首先,閱讀理解必須聯系自己的社會生活經驗,才能達到深刻的理解。朱熹說:“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后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
其次,語文學習要將所學廣泛應用于社會實踐,在實踐中進一步深入理解,將知識轉化為能力,養成運用語文的良好習慣。“學者讀書,須要將圣賢語言,體之于身。如克已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復:我實能克已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因此語文學習應當“從容乎文義句讀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后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是誦五車,亦奚益于學哉!”
反對單向度閱讀教學,倡導多向度的、關注個體的閱讀,這樣的閱讀既注重經典,也關注時尚,這樣的閱讀是一種推陳出新,是一種與時俱進;這樣的閱讀既關注文本,也關注自我,這樣的閱讀是一種學習,又是一種批評;這樣的閱讀既關注吸收,又關注傾吐,這樣的閱讀既是一種繼承,又是一種創新。
從知識到能力的轉化需要一個反復實踐的過程,主體借助已有的知識去獲取新的知識,新的知識只有納入主體的舊有的知識才能夠轉化為自身的血肉。
這樣的閱讀教學所倡導的方法,可以給學生很多的思考。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我們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遠,而不是躲在偉人的腋下、趴在巨人的腳下唯唯諾諾、人云亦云。我們要培養的一代人應該是智慧的、富于情感的、善于思考的、站直了的當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