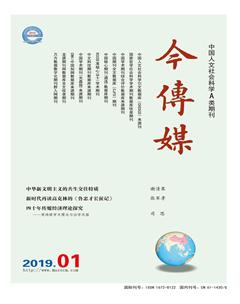基于符號學維度論電影改編創作研究
臺雪純
摘要:電影改編在符號學維度論中通過藝術現象進行傳播,通過電影思維進行二次創作先導多樣化的特點與規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許多學者一直從內容主題出發,關注著電影改編研究中所表達的忠實,甚至是有關原創問題。但是卻忽略了從文學作品改編到電影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在適應過程中電影和文學媒體所表現出來的差異。本文從結構主義符號學的角度,探討從小說改編到電影過程中涉及的媒體差異。
關鍵詞:電影改編;小說;結構主義;敘事;語言
中圖分類號:J90文獻標識碼:A[KG1.5mm]文章編號:1672-8122(2019)01-0119-02
所謂電影改編是指遵循電影藝術的規律和特點、利用電影思維,將作品以文學形式塑造成電影的藝術現象。電影改編占據了世界各國電影制作的很大比例,并一直是電影的重要來源。它實際上是發展自己的藝術表現形式的使命以肩負著推廣文學經典、擴大電影主題為要求。然而長期以來,許多學者均集中注意力于電影改編研究中的原創性問題上,并且主要側重于內容主題,而忽略了電影改編中的基本問題在適應過程中電影和文學媒體所表現出來的差異性。
一、結構主義理論與媒介傳播的引導
小說和電影是一種敘事作品,這種無休止的分析結構看起來缺乏連貫性與統一性,組織交流起來不太連貫完整[1]。但是根據現有條件分析,構建語言符號學框架,利用電影作品進行分析營造區塊模型的事例是最為合理的。每個系統均有一個組織結構。托多羅夫用俄羅斯形式主義方法來區分研究中的兩個主要水平,一個是故事(內容),包括行動、邏輯和角色的“語法”;第二個是話語,包括敘事的時間,身體和風格。了解電影敘事脈絡把握故事主題情節發展,識別層次化故事體系,連接各條線索與空間軸線進行突出展示,近而突顯幾大層次。巴特主張將敘事作品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是功能層,功能單詞使用Propp的含義;第二個是動作層,動作使用了Greimas的含義; 第三個是敘事層,類似于托多羅夫所說的話語層。這三層以逐步的方式相互連接:只有當一個函數在一個actor的整體動作中占據一個位置時,它才有意義,并且演員的所有動作最終都通過被敘述并成為話語的一部分來實現。而話語則有自己的代碼。敘事根據語言層面理論一般存在兩個層面的關系:一是分布關系,即關系處在同一層次上;二是結合關系,即關系是跨層次的。前者相當于Propp的功能,即為一個水平組合;后者相當于標志,如人物標志,身份,氣氛標志等,是垂直聚合。該函數包含一個隱喻關系,徽標包含一個隱喻關系;前者與行為的功能一致,后者與存在的功能一致。功能又可劃分基本功能(或核心)和催化功能,兩者之間相互支持。一系列邏輯組合核心形成一個序列,最終將幾個序列組合成一個敘述。但巴特的行動層是格雷馬斯提出的三個二元對立行為者,即主體和客體,施益人和受益人以及輔助和反對者。我們主張,當小說改編成電影時,無論是對原作的忠誠,還是將章脫離背景,都有必要分析小說的故事內容。對功能和動作進行分析,有助于全面掌握小說的內容。而小說和電影中所共享的內容可以直接移動。
小說和電影的敘事方式由于媒體的不同存在差異。根據結構主義理論,小說和電影作為敘述者,而這種虛擬敘述者不等同于作者。作為現實世界的作者,他們確保讀者或觀眾在欣賞故事時能夠相信故事世界的邏輯和合理性,并且能沉浸于虛構的故事世界中,才規定建立了小說和電影中虛構故事的各種情境和規則。但電影敘述者仍然不同于小說敘述者,電影敘述者的第一個敘事層面是戲劇的敘述者,尤其是電影中人類作為敘述者使用的畫外音。配音者訴說故事控制情感很有格局的把握各式各樣的與心理架構不同聯系的各種電影層次。場外與場內的聯系情感突出豐富化視覺化的感官表現,但在劇中人物敘述者的層面上仍存在更高層次的敘述者,即Genette所說的講故事敘述者,故事之外的同一故事敘述者屬于電影中同一故事的敘述者[2]。電影故事的敘述是電影媒體本身的敘事或言語行為,描述整部電影并控制與整部電影相關的所有電影符號和表演頻道進而確定戲劇中人物敘事的可靠性。關于這個級別的外部非個性化電影解說員,許多學者都有不同稱謂,如相機敘述者、基本敘述者、基本敘述者和第一敘述者等,電影基礎敘事結構把時間空間聯系起來,利用虛擬現實感官體驗創造豐富的內涵,設置最基本和直接的代理表達。可以將故事信息直接傳達給觀眾。它高于戲劇敘述者的代理人水平,其敘事比戲劇的敘述者更具權威性和可信度。同樣地,電影基本敘述者的配音也比戲劇敘述者的配音更具權威性和可信度。這樣使得結構主義理論與媒介傳播的引導更為寬廣時效。
二、維度論電影改編研究的符號學特征
符號學中對于小說和電影的表象特征是不同的。語言的行為特征不光體現在電影故事情節中的鋪敘,更是在小說電影文本媒體形式中的多種宣傳手段。這種特殊符號的體現諸如強調、重復、延遲等都會對電影敘述環境的指向性加以導向闡述,配以行為注明使得電影改編的形式感更強烈。小說的語言可認為是一種文本符號,而電影的語言是一種多模態的語言,其中包括運動圖像、圖像的圖形表示、人的聲音和音樂[3]。無論電影的多模態如何,我們在比較文本和圖像時都會發現許多不同之處。對此,麥茨曾有過精辟的論述。1.電影具有無限圖像的數量,而自然語言中的單詞原則上是有限的;2.電影中的圖像是導演的創作,而言語中的單詞僅是成語的衍生物;3.圖像呈現一個難以被消耗的未定義消息,同時定義了單詞;4.作為一個備注單位的圖像包含“即時性”(此刻),而單詞純粹是一個潛在的詞匯單位。“房子”這個單詞在小說中可以讓人幻想成任何一種房子,但電影鏡頭中的房子并不代表“房子”,而是“有一個特定尺寸和特定形狀的房間,從特定鏡頭以特定角度拍攝的場景”;5.電影組合片段中每個鏡片的替代方案是無限的,并且鏡片不會在組合片段中與可能的鏡片產生聚合關系以產生意義,而用自然語言替代片段上的單詞是有限的。換句話說,電影在圖像級別是沒有聚合關系的,小說文本可以給人們一個無限的空間來想象,但電影的形象一旦呈現給觀眾就變成剝奪想象力的殺手[4]。文獻的“信息”絕不是直接的,電影所呈現出來的觀測點反應事物的客觀存在運用不同表現方式方法,抽象化的體現的淋漓盡致。電影作為傳媒媒介所充實的行為要素下各種不同狀態與方式方法,形成相同事物不同類型特征,體現事物本質的多元化體現引導每個受眾群體的多樣化思維反射。這種思維反射不可能滿足每個人大腦的活躍度,電影的多層次改編不同符號化傳播也不可能滿足每個受眾心理需要。
另外,在電影改編過程中重構電影劇本,必須充分迎合電影環境之外的形象化符號,通常包含:1.語言符號,這里的語言主要是綜合語言方言、語調和時代的社會特征;2.視覺符號,這包括構圖形式、操作方式和觀眾閱讀方法;3.文化符號,主要指不同國家的文化背景。
三、結語
事實上,通過符號學將維度論電影改編創作研究。在實際運用中小說語言與電影多模式語言還需要進一步比較研究。通過結構主義理論與媒介傳播的引導,將維度論電影改編研究的符號學特征通過各種形式展示出來,讓大眾進行喜聞樂見的傳播佐證,豐富多層次視覺感官[5]。這種方法與創新形式值得推崇與借鑒,可以廣泛應用到電影電視改編創作過程中。
參考文獻:
[1]姚源.2012中國電影:論文學作品的改編[J].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3(4).
[2]劉景景.《白鹿原》電影對小說的再現和改編[J].旅游縱覽(下半月),2013(9).
[3]孫宜君,高涵.從《白鹿原》改編看電影與文學的非良性互動[J].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1).
[4]周勇.當意象解構為影像――關于電影《白鹿原》的改編得失[J].大眾文藝,2014(10).
[5]電影藝術詞典[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104.
[責任編輯:張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