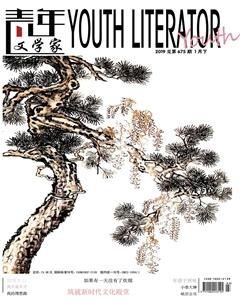以玉比德:從《論語》中的“玉”看玉文化發展
摘 要:儒家“以玉比德”的玉德觀念對我國的文化發展有著深遠影響,《論語》中也有很多利用“玉”的人格化闡發的觀點。對玉文化的來由,有人從玉的物理屬性出發分析其形態與君子品行高潔的相似性,也有人將儒家對玉文化的推崇與原始的玉崇拜聯系起來。人們對于玉,從膜拜其“神性”到崇敬其“人性”再到看重其“物性”,這其中不僅有線性的歷史發展因素,也包含了不同文化形態的社會對神、人、物之間關系的思考。
關鍵詞:拜物;儒家;玉文化;比德于玉
作者簡介:韓鈺(1994-),女,漢族,山西太原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在讀,研究方向:文學人類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3-0-02
寒梅傲雪、松柏不凋、杜鵑啼血……自古以來,我國便有借助自然物象以比喻、象征等方式闡發思想、彰顯價值及高尚道德品格的文學傳統。《周易略例·明象》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1]”便是對“意”、“象”、“言”三者的關系進行梳理概括。玉是承載傳統文化諸多意象的代表之一。
一、緣起:為何以玉比德?
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首次對“玉”做解,認為玉是“石之美”也,其中蘊含“五德”。《說文》對玉的釋義顯示它被主觀認定為“美”的事物,對它的屬性辨析以人的德性為參照。因此,古代的玉不僅是礦屬分類中物的概念,它從為人所用時就具有了文化屬性加成。王銘銘《“君子比德于玉”》中對中華文明與玉器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簡單的概括。他認為“并非所有民族都像我們這樣好玉,賦予玉器非物質的精神價值,實在可謂是中華文明的古老特征之一”。
“玉器是屬于石器的一部分,不過它是美的石頭。這些美的石頭——美玉,從普通的石器發展成為玉器之后,這些器物本身就不再是普通的工具了,它被注入了更高一級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2]在商代,玉器的制作技術趨于成熟,玉器的社會功能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到了西周,玉器更是成為了“禮”的載體,成為社會各階層身份標定的象征,也承載了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價值判斷。
古典文獻有關于巫儺佩玉的描寫。如《詩經·衛風·竹竿》:“巧笑之瑳,佩玉之儺。”學者葉舒憲從人類學的角度出發,認為我國古代存在原始拜物教的“玉崇拜”傳統,在早期文化中,巫-玉-神“三位一體”,玉被認為具有“靈媒”功能。《孔傳》中有“修吉兇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即璜、璧、璋、珪、琮五種玉器)”之說,這是對我國古代將玉作為禮器對諸侯的政治等級進行劃分,并以玉為象征對封建禮制作出規定的文字佐證。而儒家的“玉德說”便是在傳統的“玉崇拜”和以玉為禮器的基礎上對玉文化進行倫理化和道德化的改造,使其成為君子高尚德行的象征。
二、確立:《論語》中玉的出現及內涵
周代以前,玉主要作為祭祀用品和禮器使用,有學者認為,周朝統治者吸取前朝因巫卜泛濫而衰敗的教訓,對玉進行了“去宗教化”和“去神圣化”的處理。他們弱化了玉通巫神之能,轉而強調其質地堅硬溫潤、表里通透如一的外觀,將玉的外在屬性和人的道德修養相聯系。這樣玉便從神壇跌落人間,雖然在民間儀式和一些文學作品中仍然有玉通靈的傳說,但主流文化把玉與“人德”之間的對應關系固定了下來。
玉的人格化在中國古代早期的文學作品中有大量體現。如《詩經》中有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3]等句,均以玉的溫潤無暇來比擬君子高潔。春秋戰國時期,人們也將玉作為美德、才學的象征,如《道德經》中“圣人被褐懷玉”的說法便是形容懷才不遇的寒士處境。
儒家學派對“以玉比德”的文化現象進行了一定的總結和闡發。在《禮記·聘義》中,孔子和他的學生子貢之間有這樣一段對話: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 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 廉而不劌,義也; 垂之如隊,禮也; 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 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 孚尹傍達,信也; 氣如白虹,天也; 精神見于山川,地也; 圭璋特達,德也; 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4]
這段話是對玉的人格化全面而精煉的表述。孔子先表明之所以“貴玉賤珉”并非因為玉石貴重而稀有,而是因為玉之德。他分別從玉的外觀、觸感、敲擊形成的聲音、產地、人們對它的看法等角度出發,把玉的品德概括為仁、知、義、禮、樂、忠、信、天、地、德、道十一個方面,從而徹底將玉作為道德和人格的象征地位確定了下來。
《論語》中所記載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表達了他們追求高尚人格的崇高理想,他們像打磨玉石一樣時時雕琢自己,反復修煉以達到這一境界。玉石在這里以“不琢磨,不成器”的形象出現,正是儒家以玉自比,達到“天下莫不貴者”狀態的美好愿望以及自我磨礪的堅韌品質的體現。
《論語·公冶長》云: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 子曰:“女器也。”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子貢詢問老師對自己的看法,孔子說:“你就好比是宗廟里成黍稷的瑚璉之器。”瑚璉是一種玉做的祭祀用的禮器,外形華麗并以白金飾口,在宗廟祭祀中作用重大,是“器之貴者”。有人認為這是孔子以瑚璉比贊子貢,夸他堪為大用。但如果細究瑚璉之用,或可對孔子的話做出其他解讀。在《論語·為政》篇中孔子有“君子不器”之說,而瑚璉雖貴,卻終究淪為器用,這遠不是孔子期望自己的弟子達到的境界。無論是名貴的玉器還是石制的工具,都因做為“器”的工具性限制了自己的發展,這是君子需要避免的。瑚璉之“器”即使稀有,卻不是孔子期待的君子模樣。這也側面印證了孔子所謂“君子貴玉”并非因為“玉之寡”,而是看重玉石的精神內涵。
《論語·子罕》中有:
子貢曰:“有美玉于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這里“美玉”的用法類似老子所說的“被褐懷玉”,側重指滿腹經綸與才華。孔子及其弟子自比美玉,待價而沽,期待知人善任的明主像“善賈”一樣識貨,期待有朝一日可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韞”指隱匿、隱藏,這段對話雖然表達了一展宏圖的志氣,但也有亂世不求聞達的隱居之意。
《論語》中“玉”的用法顯示,隨著原始玉崇拜的消亡和分封制的沒落,玉石的神性、靈性和作為禮器的作用被剝離,關涉世俗生活的人的美好品格及才華等的象征性被固定,并在之后中華文明發展的進程中不斷發揮作用。
三、變化:玉文化的發展和演變
甲骨文中的“玉”是用一條繩索串著的三塊玉石。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將“玉”解釋為帝王的“王”,并說它乃“天下所歸往者”。根據玉早期的通神特質,我們可以對“玉”和“王”的聯系作出解釋,玉與王相生相映,兩者俱靈氣十足,可通天地人,可掌天下事。后來隨著華夏文明的發展和王權的進一步演化,玉也被制度化為禮的代表,成為君子高義的象征。
在華夏文明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比德于玉”的價值觀為社會倫理的構建起到了積極而正面的作用,也奠定了傳統文化中玉與君子形象相關的文化基礎。這一形象構建也將“玉”道德化、世俗化、實用化,使玉的品格逐漸與人的品格融合,玉的特點和人的才華相掛鉤。這不僅是將人“玉化”,更是使玉“人化”并褪去了其神性色彩。
玉作為宗教神話體系的象征有著豐富的文化衍生功能,對玉的推崇以物神崇拜的形式伴隨我國早期文明發展。葉舒憲認為儒家崇玉學說和佩玉制度的文化和信仰來源便是早期文明中的玉崇拜。[5]同時也人認為是儒家倫理觀將玉從原始宗教的束縛下解脫出來,“比德于玉”觀反映的是人們思想的進步和理性的發展,這一觀點使得原始的玉崇拜和儒家的玉文化說全然割裂來看,因此很多人提起“玉”與君子和道德關系,往往只會聯想起玉光滑剔透的質地而忽視其背后深層的文化土壤。我們不能用純粹的文化進化論觀點解釋玉文化,應辯證看待玉的原始文化功能及其對后來文化發展的影響。
商品經濟的發展使玉的神圣化功能衰退,它對君子高潔品格的代表作用也在被商品價值沖淡。進入市場流通領域之后,玉的物理屬性成為了其經濟價值的判斷標準,越來越多地成為了有經濟利益的商品,成為了彰顯玉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物。正如數千年前玉的“人性”取代了“神性”一樣,后來玉的“物性”也取代了“人性”,以更世俗化的面目出現在如今的社會生活中。
注釋:
[1]摘自王弼:《周易略例》,轉引自葉舒憲:《儒家神話的再認識》,《百色學院學報》,2011年6月.
[2]費孝通:《費孝通論文化與文化自覺》第343頁,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
[3]摘自《詩經·秦風·小戎》,轉引自張連舉:《論玉在<詩經>中的意象建構》,《徐州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1月.
[4]摘自《禮記·聘義》,轉引自葉舒憲:《儒家神話的再認識》,《百色學院學報》,2011年6月.
[5]觀點引自葉舒憲《從玉教到儒教和道教——從大傳統的信仰神話看華夏思想的原型》,《社會科學家》,2017年1月.
參考文獻:
[1]程樹德. 論語集釋[M]. 中華書局, 1990.
[2]費孝通. 費孝通論文化與文化自覺[M]. 群言出版社, 2007.
[3]楊伯峻. 論語譯注[M]. 中華書局, 1980.
[4]王銘銘. “君子比德于玉”[J]. 西北民族研究, 2006(2):167-175.
[5]葉舒憲. 從玉教到儒教和道教——從大傳統的信仰神話看華夏思想的原型[J]. 社會科學家, 2017(1):137-142.
[6]葉舒憲. 儒家神話的再認識[J]. 百色學院學報, 2011, 24(3):1-11.
[7]張連舉.論玉在<詩經>中的意象建構[J].徐州師范大學學報,2012(1):47-50
[8]李云霞. 玉與先秦秦漢時期的禮俗文化[D]. 山東師范大學,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