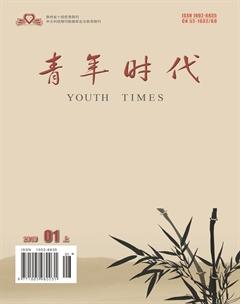金圣嘆的“才子觀”
齊星
摘 要:金圣嘆批刻六才子書,亦有《天下才子必讀古文》。“才子”對于金圣嘆之重要可就其使用頻率中可窺一二。對于金圣嘆所說的“才子”,本文將從三個方面進行論述。首先,厘清“才子”這一詞匯的基本來源和意義的演變過程,其次,以《第五才子書水滸傳》評點理論為中心,探析金圣嘆的“才子”觀念與具體體現;最后,分析金圣嘆“才子”觀的影響。
關鍵詞:才子;才子之才;意義
一、“才子”的源起與流變
“才子”這一概念,絕非橫空出現在金圣嘆所處的明清時期,立足于傳統文化的大時代背景下,植根于前代的文化土壤中,對于“才子”概念考境源流是為必要。
春秋時代,“才子”詞語的產生。 “才子”一詞可追溯到《左傳》。《左傳·文公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敱、梼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圣、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1]這里的“才子”指具有一定的政治才能與高尚品質的人。
魏晉南北朝時期,不管是正史還是各類文學作品之中,“才子”一詞開始大量出現,無疑與這一時代文學的進一步自覺乃至獨立,密切相關。
《南史》記費昶(生卒年不詳):王子云,太原人,及江夏費昶,并為閭里才子。昶善為樂府,又作鼓吹曲。” [2]
這一時期的“才子”指詩才。鐘嶸《詩品》中亦言:“預宗此流者,便稱才子”,將才子這一概念納入其詩學批評體系。魏晉南北朝時代,“才子”一詞逐漸固定,形成了成熟的才子概念,指才高詞贍的詩人或作詩者。
進入唐代,出現“大歷十才子”這樣的以“才子”命名的詩學集團,據《唐才子傳》的相關記載,此十人俱是詩才俊雅之人。另外,如元稹與杜牧之類的風流才子,他們風流多情,流連于風月場所,但因其寫得一手好詩,便被時人解釋為才情的體現。這一時期,才子除了指詩才高超的詩人,亦指風流蘊藉的詩人。
宋元時期,唐代“元才子”所開辟風流蘊藉的才子概念由柳永所接續,伴隨著對柳詞“才子詞人”的誤讀,產生了“風流才子”這一“才子”下位概念,形成了主要基于儀表、情愛而非詩才、辭才的市俗化風流才子形象。另一方面出現以“才子”命名的詩史專書《唐才子傳》傳統才子概念(詩人)在詩學及詩史領域的使用日趨成熟。
明清時期,詩壇“北郭十才子”、“江東三才子”“吳中四才子”等才子詩群輩出,縱橫恣肆,狂傲放誕,才子概念也因此刻畫上了鮮明的時代特質。才子不再為詩學、詩史所獨有,又與風流才子的概念漸次合流混同,前代才子概念的文體界限、雅俗差別都消融殆盡。不再單指文學才能出色的人,普通人也可稱為才子。總而言之,才子概念在明代,完成了文藝、文類、雅俗、性別的全面盛極與擴張過程。
二、金圣嘆的“才子”觀念
金圣嘆在評點之中多次強調才子,以評點才子書作為自己顯示才華的方式。
金圣嘆的“才子”觀念滲透在其全部作品中,他認為“圣人之作書也以德,古人之作書也以才”[3]明確的把‘才與‘德作為獨立的概念提出。他通過評點古人之書明示古人之才,這里更多的是關注到作者的文學創作才能。他認為:“若《水滸》固自為讀一切書之法”。[4]本文特以《水滸傳》評點為例,分析金圣嘆所認為的小說家之才所具備的文學品質與才能。
“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才之為言,材也。凌云蔽日之姿,其初本于破荄分莢;于破荄分莢之時,具有凌云蔽日之勢;于凌云蔽日之時,不出破核分莢之勢,此所謂“材”之說也。又才之為言,裁也。有全錦在手,無全錦在目;無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見其領,知其袖;見其襟,知其帔也。夫領則非袖,而襟則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后相合,離然各異,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謂“裁”之說也。”[5]金圣嘆的才學理論,首先講究才學個體的獨特性,作家因個人氣力不同,所進行的創作也有著極強的個性色彩。“既不能前后傳承,也不能左右假借,即所謂的‘世不相延,‘人不相及”。[6]其次,需要有一定的天賦,用“材”比“才”,強調先天稟賦對于創作才華的決定性影響。以樹木成長為例,強調種子的基因在“破荄分莢”之時,應該具有“凌云蔽日”的能力。以此比之于人,一個人是否具有足夠的創作能力,與先天自然所具備的天賦密不可分。同時也指出:“故依世人之所謂才,則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謂才,則必文成于難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說,則是迅疾揮掃,神氣揚揚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難之說,則必心絕氣盡,面猶死人者,才子也。故若莊周、屈平、馬遷、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書,是皆所謂心絕氣盡,面猶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繚繞,得成一書者也”。[7] “文成于難”之說,可見除了足夠的天賦以外,才子的“才”還與后天的艱苦努力緊密相連。再次,“才”與“裁”,金圣嘆強調對文料進行裁剪,加工,處理的本領和才能,認為創作主體在創作之時,除了整體的全局的觀念,局部的細節的意識必不可少,即謀篇布局的才能至關重要。最后,創作者將自己的才情自如的運用到構思、布局、煉字、琢句等各方面,而且能夠按照自己的意識隨時更改,通過細心地裁剪將已有在胸的全局觀念體現出來,反映在創作作品中即為渾然天成。此外,“才”在描寫手法上,他指出:“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構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構思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立局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琢句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安字以后:此茍且與慎重之辯也。言有才始能構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外未嘗矜式于珠玉,內未嘗經營于慘淡,隤然放筆,自以為是。而不知彼之所為才,實非古人之所為才,正是無法于手而又又無恥于心之事也。”[8] “金圣嘆極口否認有才始能構立琢安,而認為古人之才繞乎其前后左右,這就是所謂的‘筆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筆不安換右筆,用右筆不安換左筆。用正墨不現換反墨,用反墨不現換正墨可見真正的才是在于手法上的千變萬化。”[9]
同時才子因創作才情不同,亦有高下之分,見之金圣嘆“三境論”:“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10]即“心”與“手”之間的關系,“心”指作者的思想感情,“手”則指作者的“秉筆屬文”,創作者手中之筆對于創作者之內“心”的表達程度,能否到達化境,取決于創作者的用筆能力。創作者的才情不一,創作的文學作品有所區別。在《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中提到:“吾嘗遍觀古今人之文矣,有用筆而筆不到者,有用筆而其筆到者,有用筆而其筆之前、筆之后、不用筆之處無不到者。有用筆而其筆之前、筆之后、不用筆之處無不到者”與“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的“神境”與“化境”相契合。強調創作主體的自身才情決定了文學作品的深淺不一。“用筆而筆到者”,是創作者的基本素養,符合第一境界“圣境”;而筆達意或是表達自己的意外之想則符合第二種境界“神境”,如若創作者在行文之中汪洋恣肆,游刃有余,達到忘我的境界,則是“化境”了。
金圣嘆將施耐庵作為小說家才子的代表,通過對《水滸傳》的評點反復贊嘆施耐庵的才情,認為《水滸傳》體現了施耐庵杰出的文學創作才華與藝術才能。“不讀水滸,不知天下之奇,嗚呼!耐庵之才,其又豈可以斗石計之乎哉!”[11]下文將通過金圣嘆對《水滸傳》的評點,分析金圣嘆所認為的施耐庵在文學創作層面的獨特才華。
首先是關于其在作品中呈現的“格物”的能力。關于“格物”在小說理論方面的體現,金圣嘆有一段較為集中的論述。
“格物之法,以忠恕為門。……夫然后格物,夫然后能盡人之性,而可以贊化育,參天地。今世之人,吾知之,是先不知因緣生法,不知因緣生法,則不知忠,不知忠,烏知恕哉!”[12]金圣嘆的格物,關涉到很多藝術創作中的問題,試舉其中幾例。“一心所運”,是其總體特征,“忠恕為門”,和“因緣生法”是其兩條必經途徑。“突出強調‘心在創作中的權威地位”,金圣嘆強調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將自己內心對社會生活的認知,躍然于紙上,呈現出具體的文學成果。具體表現在施耐庵身上,則是其描寫人物的能力,一百八人,各有特色,形象鮮明;”[13]
小說與傳統的史學的區別在于小說可以虛構,而他認為《水滸傳》中的許多事跡都是作者虛構而來:“七十回中許多事跡,須知都是作書人憑空造謊出來”[14],“一百八人,七十卷書都無實事”[15],小說家才子通過虛構和想象構筑出一百八人鮮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圍繞人物的具體事件,這無疑是小說家才子才華的一個具體體現。
“若夫耐庵之非淫婦、偷兒,短短然也。[16]強調“動心”的重要性,指作家在進行創作之時,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轉換角度,設身處地的想所寫人物之所想,在創作之時要忘掉自身,這也不難理解金圣嘆的“文成于難”之說,正是因為這樣的盡力和努力,才會“心絕氣盡,面猶死人”。“十年格物,一朝物格”,突出“動心”的能力與作者格物之間的關系。
“格物”,虛構和“動心”,金圣嘆在評點《水滸傳》時充分注意到施耐庵的這些能力,而這些也是金圣嘆所認為的施耐庵的才子之才。
三、金圣嘆“才子”說的意義
金圣嘆通過遴選才子書,進行評點,展現創作者才情的同時亦表現自己的才情,“立言”揚才以傳不朽。金圣嘆曾感慨道:“為兒時,自負大才,不勝侘傺,恰似自古及今,止我一人是大才,止我一人無沉屈者,后來頗頗見有此事,始知古來淹沒豪杰,萬萬千千,知有何限!青史所紀,磊磊百十得時肆志人,若取來與淹殺者比較,烏知誰強誰弱?嗟哉痛乎!此先生《黃魚》詩所以始之以‘日見二字,哭殺天下才子也!”[17]意識到時間的可逝性,在有限的時間里,通過評點表揚古人之才,亦可揚自己之才。
金圣嘆通過批刻“才子書”,提出“才子”說,一方面強調才子“文成于難”,有利于糾正世人對“才子”的誤解,指出才子與“不才”之間的差距與區別,糾正當時世情與艷情小說滋生蔓延的不正之風,通過篩選批刻經典,提高文人的精神境界和品位,同時喚醒人們對真正“才子”的勞動成果的尊重。
另一方面,通過評點的方式傳授讀書的方法,有利于提高讀者的鑒賞水平,“觀鴛鴦而知金針,讀古今之書而能識其經營”[18],“舊時《水滸傳》,子弟讀了, “舊時《水滸傳》,子弟讀了,便曉得許多閑事。此本雖是點閱得粗略,子弟讀了,便曉得許多文法;不惟曉得《水滸傳》中許多文法,他便將《國策》《史記》等書,中間但有若干文法,也都看得出來……《水滸傳》到底只是小說,子弟極要看,及至看了時,卻憑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 后輩通過學習才子作書之法,成為有才情的讀書人和創作者,使才子書流傳于后世。除此之外,金圣嘆本人也通過評點六“才子書”揚名于后世了。
參考文獻:
[1]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36~637頁.
[2]《南史·列傳第六二》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783頁.
[3][4][5][7][8][9][10][11][12][14][15][16][17] [清]金圣嘆:《貫華堂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序·序一》,《金圣嘆全集》(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10、5、5、5、5、395、395、10、19、222、222、676頁.
[6][13]陳飛.《文學與文人——論金圣嘆及其他》,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341,324頁.
[18]《金圣嘆全集》(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