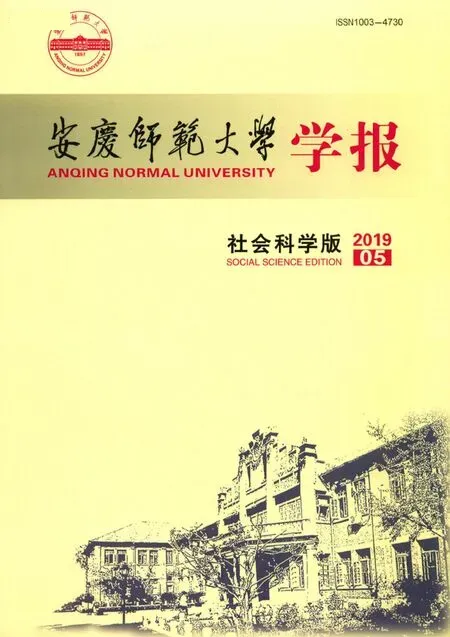“瑪麗蘇”現象背后的女性意識
李亞芝
(陜西理工大學文學院,陜西漢中723001)
“瑪麗蘇”應該是一位不凡的姑娘,集美貌、善良、智慧于一體,正是這樣一位姑娘贏得了所有人的喜歡。“瑪麗蘇”所指的不是具體的一個人,而是指擁有這種特征的所有姑娘。
“瑪麗蘇”是英文“Mary Sue”的音譯,原出自保拉·斯密斯(Paul Smith)的科幻小說《A Trekkie’s Tale》。“Mary Sue最先是耀眼而年輕美麗的星艦長官,加入核心集團成為焦點受到矚目,無所不能,博得某個重要角色的芳心,最后戲劇性地死在某個人的臂彎里,估計你也可以運用你讀書的經驗照此推斷出類似的劇情來。Mary Sue存在于幾乎所有讀者心里”[1]。“瑪麗蘇”一詞在英文維基百科是這樣定義的:“瑪麗蘇(有時簡稱為蘇’)是文學批評中,尤其是同人文中的概念,特指一種過度理想化的,行為模式老套的小說人物,她們身上沒有值得一提的缺點,其主要功能就是充當作者或讀者的完美想象的化身。她們的優點掩蓋了個性,通常也被認為是一種單向度的人物形象。”[2]“瑪麗蘇”為人們所熟知是由于同人小說的出現。同人小說是指套用在原有的小說背景基礎上,創造一個自己構想的全新的人物,并且使這個人物取代原來的主人公而成為小說的線索中心。這個主人公的設置多是集美貌與智慧于一身的少女,和小說中一位或多位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情感糾纏。在網絡小說中,作者出于自己的自戀心態或滿足讀者對浪漫愛情的期待,塑造了一個又一個完美的女主形象。隨之,“瑪麗蘇”不再是同人小說中獨有的名詞,也指原創文中塑造的具有“瑪麗蘇”形象特征的所有女性形象。由于單一化、套路化創作模式的泛濫,這種形象很快的被讀者熟知,在很多小說創造中都有體現,就逐漸地發展成為一種“瑪麗蘇”現象。
“瑪麗蘇”現象雖然因同人小說而命名,在網絡言情小說的推動下被讀者所了解,但國內“瑪麗蘇”現象卻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涌現的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說。這類小說中的情節設定為才子在外出訪學的過程中偶遇才貌雙全的佳人,并一見鐘情,然后寫詩寄情,經由梅香撮合,二人私定終身。但是因權豪構陷,或有小人從中作梗,或為政治犧牲,佳人被迫要嫁作他人婦,才子遭遇各種磨難。最后,因才子中了高科,明君主持正義,終是“有情人終成眷屬”。才子佳人小說的人物塑造上,較成功的塑造了一群新型且頗典型的女性形象。如《玉嬌梨》的白紅玉、盧夢梨,《平山冷燕》中的山黛、冷絳雪,《西廂記》中的崔鶯鶯等。她們盡態極妍,明眸皓齒,有才氣也敢于打破禮教束縛勇敢地追求。才子佳人小說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最終走向了模式化,這種固定模式分為三個階段,一見鐘情—姻緣阻隔—終得團圓。當然,這種模式化情節,也是其走向衰敗的原因。
到了現代文學中,“瑪麗蘇”形象在十七年文學中也有所體現,最為典型的是楊沫的《青春之歌》中林道靜的人物形象塑造。林道靜是20世紀30年代革命斗爭中覺醒并成長的革命知識女性,楊沫在人物塑造過程中,不自覺地將其“瑪麗蘇”化。林道靜的出場這樣寫道:“這女學生穿著白洋布短旗袍、白線襪、白運動鞋,手里捏著一條素白的手絹,渾身上下全是白色。”[3]作者在悄然中將林道靜的人物形象超脫世俗,不染塵世。而接下來在敘述林道靜與于永澤、盧嘉川、江華的感情線時也帶有一種傳奇色彩,是一種不露痕跡的“瑪麗蘇”,林道靜的成長歷程依靠的是男性不斷地喚醒與改造。
當代文學發展中,“瑪麗蘇”最早可以追溯到瓊瑤小說,瓊瑤小說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被翻拍為電視劇的《還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一簾幽夢》這幾部小說,其中小燕子、紫薇、依萍、如萍、紫菱、綠萍等女性形象的塑造最為典型。瓊瑤筆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大多沒有很高的學識文憑,但能詩會賦,溫柔嫻淑,有傳統的婦德。情節主要圍繞傳奇的浪漫的愛情故事展開,“愛情”是小說的主題,雖然小說并未寫出深刻性,但也滿足了一大批女性對浪漫愛情追求的幻想與向往。其后在安妮寶貝《告別微安》《八月未央》等描寫女孩青春苦語的小說中也有所體現。
在現代網絡言情小說中,“瑪麗蘇”形象更是層出不窮,晉江文學網、起點中文網還有紅袖添香等網站中,言情小說中塑造的“瑪麗蘇”形象層出不窮。“霸道總裁文”“灰姑娘型”“穿越文”等“瑪麗蘇”愛情故事屢見不鮮。《步步驚心》中穿越到清朝的馬爾泰若曦,幾位王爺或成為她的知心朋友或成為了追求她的人,《冰淚之櫻》于2011年被評為“最瑪麗蘇文”。因電視劇的拍攝而被熟知的小說,如《泡沫之夏》《甄嬛傳》《那年花開月正圓》等等,更使“瑪麗蘇”不再僅僅是一種形象而是成為文學現象。
一、“瑪麗蘇”現象塑造模式
“瑪麗蘇”的愛情際遇是理想配對的極致,郎才女貌是必備條件,并且往往是多位男士追求一位女性,只為顯示“瑪麗蘇”形象的與眾不同。
(一)“瑪麗蘇”形象的共有特征
“瑪麗蘇”形象主要出現在同人小說、言情小說、穿越小說、大女主小說等類型中,而在這些看似不同的文本類型中,卻也有著某些共性的特征。
1.人物形象:女主人公花容月貌,傾城傾國,即使沒有絕世美顏也必定有一種獨有的氣質,讓很多男性為其著迷。在《泡沫之夏》中的夏沫有著海藻般濃密的長發,微微卷曲,眼睛像海水一樣,皮膚很白。作者運用了色彩鮮明的詞語,在極其具有畫面感的語言渲染下,讓讀者很容易感受到夏沫的美麗。
2.人物名字:每個人物都有一個很美的名字,也不會考慮名字的長短,只是將所有美的字眼相加。偏愛的一些字如冰、靈、幻、月、雪、櫻、白、冷等。如在《步步驚心》女主叫馬爾泰若曦;《魅惑洪荒》的女主是紫韻,《泡沫之夏》中的尹夏沫。還有在《傾世皇妃》《雙世寵妃》中都有叫做連城的男主。這些名字很少考慮是否符合常理,更多情況下是華麗字詞的疊加。
3.人物才能:多數女主會多樣才能,吟詩寫賦,唱歌彈琴,能說會道,天賦異稟,精通各方面知識,上得了沙場下得了廚房,除得了妖怪,還能應對了心計。即使從來沒有接觸的東西,也能很快地掌握并運用自如。《傾世皇妃》的馬馥雅可以只身闖軍隊;《泡沫之夏》中的尹夏沫并沒有經過后天的唱歌培訓,僅僅幾天的學習,上場唱歌,全場就被她的歌聲所感動震驚;《步步驚心》中的若曦在穿越之前是一位熟知清朝歷史的高級現代女性。
4.人物身份:一般為富豪千金,王侯將相之女,公主或郡主之類,有權有勢。即使是出身較為低賤一點的,也必有一位或多位有錢有勢的男主在她身邊。她們有著高貴的血統,比如血族,巫師、神、花仙等。《泡沫之夏》中的尹夏沫有歐辰的保護;《傾世皇妃》中馬馥雅為夏國的公主,又有幾位王爺的傾心保護。《羋月傳》的羋月身份較低,作為羋姝的陪嫁女,從名分上說也是一位公主。《雙世寵妃》中的墨連城與曲檀兒都懷胎十三個月出生并且都是其家族的高貴血統。
5.人物性格:善解人意,平易近人,公平正直,愛憎分明,不慕名利,忠貞于愛情等所有美好品質集于一身。《傾世皇妃》中的馬馥雅為了天下蒼生大義放下了仇恨;《泡沫之夏》中夏沫為了弟弟的身體而選擇放棄愛情,被同窗姐妹陷害之后不計前嫌,選擇了原諒。《后宮·甄嬛傳》中的甄嬛不忍于素不相識的安陵容被奚落而出手相助等等。大部分女主都通過愛和以德報怨來感化敵人,展現了她們善良的天性。
6.故事構造:一言蔽之,人人都愛我,我只愛一人。女主必定與文中多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夏沫與歐辰、洛熙的感情糾葛;甄嬛與皇上和十七王爺的愛情;馬馥雅徘徊于祁佑與連城之間,還與其他王爺存在潛在的關系。在故事的開頭,或者是男女主人公一見傾心,或者是彼此厭惡在陰差陽錯的相處中擦出愛情的“火花”。“瑪麗蘇”主要圍繞“情”來推動故事情節,故事中必然安排一個心腸狠毒的女性,來襯托女主人公的善良,還有一個對女主愛得深沉而不得的追求者。
(二)“瑪麗蘇”形象的不同類型
“瑪麗蘇”形象也有不同的類型。從“所有男人都愛我,所有女人都恨我”的傻白甜到“王侯將相都愛我,歷史因我而轉動”,這是“瑪麗蘇”形象的一個變化。
1.白蓮花型
在最初的人物形象塑造中,擁有姣好面容的女主自始至終都保持著天真、善良、純潔,沒有心機。這也吸引不同類型的男性對她癡迷并保護著她,而且對她一往情深。而瓊瑤《還珠格格》中的紫薇是最為典型的白蓮花的“瑪麗蘇”;《泡沫之夏》中尹夏沫雖然表面上孤高冷傲,實則內心溫柔,待人寬容,以德報怨,為了別人犧牲自己的利益也不在乎。白蓮花型的女主大多以“灰姑娘”為主,被“王子”賞識喜歡。
2.大女主型
“大女主”文是指通過嫁接到歷史人物身上,以女性主義視角為主線,著重描寫女性傳奇勵志的一生。女主人公是小說的核心人物,她占有了小說的絕大部分篇幅,其魅力也超過了小說中男主人公。以流瀲紫的《甄嬛傳》,蔣勝男的《羋月傳》,悠悠魚兒的《那年花開月正圓》,瀟湘冬兒的《楚喬傳》為代表。甄嬛最初無意爭寵,只想安靜地度過一生,然而后宮的復雜使她不得不采取計謀以求自保。在大女主文中,女主成為一個懂得謀略的女子,性格逐漸變得剛強,最后利用各種手段取得成功。大女主的轉變并不是為了迫害他人,而是為了讓自己擺脫強權的擺布,可以自由地主宰命運。
3.全能型
“瑪麗蘇”在發展的過程逐漸擺脫了毫無生氣的單純的形象設定,而是賦予女主人公各種技能,不僅僅局限于美麗的容顏,還有過人的智慧,古靈精怪,情商很高,有很高的人緣。《宮鎖心玉》中的晴川在穿越到清朝之后利用現代知識而獲得多數人的稱贊與喜愛。由顧漫創作的《微微一笑很傾城》中塑造的貝微微是一位計算機系的系花兼學霸。《綰青絲》的葉海華根據前世的經驗,利用商業知識在天朝成為了富商。全能型的“瑪麗蘇”有的過于夸張,完美到將其神化。
二、“瑪麗蘇”現象折射出的社會心態
(一)對現實的焦慮
“瑪麗蘇”即使因其千篇一律的劇情模式不被批評者所重視,但是在網絡文學中依舊保持著很大的熱情,網絡寫手們樂此不疲地寫著各種“瑪麗蘇”劇情,有著大量的讀者群,大部分以少女年輕女性為主。在網絡媒介虛擬性的遮掩下,網絡寫手們可以忘記現實世界而天馬行空的幻想。如同熱衷英雄情結的男性一樣,“瑪麗蘇”情結則是屬于女性的白日夢。通過閱讀或者書寫,女性在這一過程中釋放壓抑的自我,獲得自我認同,進而沉溺在自我完美的假象中,迷失自我的同時也迷失在現實中。一部分理性的讀者認為,“瑪麗蘇”現象在某種層面上其實是個人欲望的釋放,“自戀在自我與外界建立邊界時起到了阻礙的作用,自戀是把自我的需要和欲望同外部事情聯系起來,它只是注重‘這對我意味著什么’。”[4]“瑪麗蘇”世界的自我狂歡很大的原因是來自于對現實世界的焦慮。在快節奏的生活高壓下,時代的更新速度讓人應接不暇,五光十色的世界里,個性極度張揚,作為單獨的個體很容易被發現也很容易被淹沒。在這個呼喚自我主體意識的時代,人人都想被關注、被認同、做主角。而網絡文學媒介的虛擬性、便捷性,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讓處在迷茫時期的年輕少女得到了自我宣泄和自我滿足的機會。網絡寫手筆下“瑪麗蘇”的意義就不僅僅是創作那么簡單了,而更多地是一種自我理想的宣泄,是自己完美形象的構想。“瑪麗蘇”寫手們通過沉溺在自己的“完美世界”中,借此來擺脫自己在現實世界的不得志。她們在塑造別人的故事中,很自然的將自己代入,這是一種對現實外界焦慮的心理補償。她們可以無視批評者的抨擊,從創作者來說,“瑪麗蘇”能最大限度地表達自己內心,真正地貼近自己期待與愿望的。正如“理想是失去的童年自戀的替代物,童年時,她的理想就是自己”[5]。
物質世界的極大豐富,人們越來越沉迷于物欲中,而精神世界卻沒有得到相應的轉變。在西方,從尼采大呼“上帝已死”到世界戰爭對人們精神世界的瓦解,還有德里達的解構“邏各斯中心”,宗教信仰對人們的精神世界的控制力逐漸淡化。在東方,中國傳統文化被現代物質文明所沖擊。人成為了絕對的主體,世界被對象化。“世界的圖像化深刻的改變了人的存在,把一種身體體驗關系轉變成了一種視覺形式關系”[6]“物化”了的社會充斥著欲望與浮躁,從西方到東方都還沒有及時建構起相應系統化的精神體系。人們處于一種緊張、慌亂、無序、沒有信仰的狀態中,這種焦慮感包圍著年輕一代,他們在自我確認與自我尋找中迷失。社會的變化太快,他們面對現代性的時代焦慮,無論是逃避現實還是在尋找自己,“瑪麗蘇”無疑成為網絡寫手和喜歡她們小說讀者的港灣或者一個造夢空間,更是他們對現代性焦慮的抵抗。“數字世界為他們開啟了挑戰社會規范、探索趣味、發展技能、實驗自我表達方式的可能性。這些活動讓十幾歲的孩子們著迷,因為他們提供的場所意味著社交世界的延展、自我導向的學習、獨立。”[7]即使得不到外界的承認與贊賞,在自己的網絡空間中,自己就是唯一的主角。這是屬于自我的狂歡,也是屬于她們的成長。
(二)價值感的缺失
“瑪麗蘇”現象明顯是少女在自我欲望下的白日夢,游離在現實世界之外,網絡世界的虛擬性將惡與善一起釋放在人們面前,娛樂至死的時代,精神的空虛,含蓄的審美不足以引起人們的興趣,需要直接的刺激才能得到關注。“在文學低俗化傾向中,既不關心作品的精神內涵,也不關注倫理道德;既沒有理想的追求,也不作善惡的判斷,只要有趣、只要娛樂、只要奪人眼球。”[8]“瑪麗蘇”形象的美貌依舊擺脫不了“看”與“被看”的局面,女性依舊只是男性賞玩的對象。創作者不再將體現真、善、美作為他們文學創作的標準,功利化的寫作目的之下,媚俗的寫出畸形的多角戀,更有大量的性愛描寫,“瑪麗蘇”小說越來越走向了低俗,甚至是惡俗。“瑪麗蘇”類型化小說在敘述的時候往往加入直接的感官刺激,而單一的欲望化敘事模式刺激著大眾的感官神經,以自我為中心的寫作將文學承擔的社會價值退化。感官上引起的愉悅“不是神圣的迷狂和欣悅,而是一種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環境中的日常經驗和體驗,它往往自覺不自覺地遠離精英文化的批判性意蘊,放棄精英文化的那種‘賜予’的姿態,將‘生產快樂’(而不是‘生產意義’)作為主要的制作原則。”[9]無論是面對文學經典還是哲學的深刻,網絡文學在消解傳統文學的教化功能與審美功能的過程中愈來愈走向了娛樂化與膚淺化,這一過程在某種程度上縮短了大眾與文化之間的距離,但是在迎合大眾文化的審美中,大眾文化在不斷地朝著低俗化與直接的感官刺激發展。為了娛樂、游戲的創作態度折射出了整個社會體系價值的缺失。在物欲的籠罩下,社會處在一種隨時可能被時代拋棄的緊迫感與強壓之下,變化節奏之快,沒有質實感,虛無與迷茫成為年輕一代的專屬形容詞。“瑪麗蘇”更在傳達著只有保持善良,守住初心才能贏得真愛。自我欲望的無限膨脹,沉迷于虛妄的快感中,在逃避現實的過程中也漸漸迷失了自己。自戀演化成了自私,個人視界變得狹窄,容易造成一種極端個人主義。網絡世界在信息傳遞方面的開放性,全球性的巨大效果并沒有在人際交往中得到預期的美好圖景。
三、“瑪麗蘇”現象折射出的女性意識
“瑪麗蘇”小說主要以少女為主,而且閱讀群體也以年輕的女性居多,隨著近年來網絡小說被翻拍成為電視劇,也吸引了一部分居家婦女群體的追捧。“瑪麗蘇”現象又在何種程度上映射了女性意識覺醒?
女性主義既是指女性主義理論,也指女性主義運動,兩者經過不同過程的發展,在追求女性的權利和性別的平等、消除妨礙女性作為個人獲得完全發展的一切障礙、爭取男女平等權利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西方女性主義者通過不同的方法、視角和框架闡釋多種不同的派別,對這些流派的研究整合梳理了女性主義的發展流程和脈絡,有助于對女性主義理論系統化理論化的研究。女性主義開創階段是從19、20世紀之交的英國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和法國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等女性作家而萌芽的。19世紀60年代之后,女性主義隨著女性解放運動的發展而進入了第二階段,對男性文化潛在規定下的女性氣質提出質疑與反思。進入20世紀,后現代思潮中解構主義對“邏各斯中心”的顛覆也引發了女性主義對男性中心話語權利的解構,由此來進行對女性自身的肯定與自我理解。
如今,女性主義的發展經歷了從女性的發現,開始對兩性的差異探討到對女性政治權利不平等而展開的女性主體意識的探討。女性主義理論的建構從些許的想法到深思之后系統的理論發展,而現在的女性主義的發展在發現了問題的真相然而卻沒有確鑿的證據來證明自己的推理。沒有嚴謹的話語理論體系支撐下女性主義者在理性的哲學體系中被孤立,畢竟女性主義理論文本大部分還停留在個人經驗的推想階段,不加個人感情色彩的,經過層層嚴密的推理的文論并沒有真正出現。女性主義者在受到福柯的“話語權利”的影響,想要構建屬于女性自己的語言體系,通過用自己的語言體系來塑造自身的形象,以此來反抗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然而在這一過程中意識到:在父權制掌握下的語言權力系統中,很難找到一種語言系統可以從根源上反抗。現有的語言體系已經深深的打上了男權社會的印記,而女性主義者想要構建的語言體系仍然擺脫不了正在使用的男性言語體系。女性主義由于歷史、地域、種族、文化差異等也并沒真正的有組織的致力于女性這一群體,不管是英美學派還是法國學派,都只是零零散散的進行著分散的戰斗,沒有形成統一的學理體系。
如何來定義女性意識?在筆者看來,女性意識是指女性自身在歷史與社會的發展進程中逐漸萌發出的對自身作為女性存在的生命體驗和心理層面的體認。如同對女人定義是“同男人相對”一樣,女性意識是相對于男性意識的。這一個詞本身就帶有性別歧視的色彩。這里的女性意識并不是指簡單的說女性的生理方面的意識,而我們現在所說的女性意識更應該稱作女性的意識,這是屬于女性這一群體的共有意識,強調女性擺脫對男性的依附,作為主體的意識覺醒和認知。這無疑是社會的進步,但是卻也為女性長久的被男權思想的控制,將男性作為中心,自我的主體意識被忽視而悲哀。
以敘述女性一生生活的網絡小說大量出現并逐漸受到追捧,在文中塑造了堅強、積極、向上的,不甘命運的安排而要自己做主的女主形象,在國內又掀起了“女權”的呼聲。“瑪麗蘇”文以女性作為主要創作者和接受主體,《甄嬛傳》《羋月傳》《如懿傳》中甄嬛、羋月、如懿等女性形象擺脫了以往千篇一律的唯唯諾諾的女性形象,“在情愛失去其可靠性的同時,是女性對“以夫為天”的“天理”的顛覆以及對“情”的重新定義,個人能力、姐妹之情、朋友之誼等全面參與到情感的知識譜系中去,成為女性立足的重要資本。”[10]她們在自己的成長的道路上對所處環境的反抗,想要打破男權社會對自己的束縛,做自己命運的主人愿望和努力體現了一定的女性意識。但是網絡小說發展的類型化問題,反映在“瑪麗蘇”文中表現為文本情節的模式化和公式化,人物符號化。而女性形象成功反轉命運最重要的原因還是依靠男性的賞識,而男性身份的設定不是“官二代”就是“富二代”,女性命運的轉變還是依靠男性權利,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瑪麗蘇”女性寫手在依舊不能擺脫固有的以男性為中心的言語體系。“卡倫·阿姆斯特朗認為,現代神話就是通過一套套的虛擬游戲,幫助我們在破碎的悲慘的世界前看到新的可能性”[11]網絡創作對于大多女性來說,并不是為了改造社會或者重建自身社會地位,只是借用網絡這個虛擬的空間中轉換一種身份,享受一種屬于自身體驗的快感,這個空間是個人化的,傾訴自己的心聲,宣泄著自己的情緒。女性寫手在自己創造的“瑪麗蘇”神話中想要得到自愈以及達到與現實世界的和解。無疑,女性創作是私語化與內心化的,而女性創作多以“情”展開,社會教化意義虛化,女性寫作視域受限,成為了當代女性意識表達不足的主要原因。
而西方女性主義的發展如今也裹足不前,沒有找到出路,“瑪麗蘇”現象在表面上是女性意識的覺醒,實則仍是在男性話語權利漩渦中得不到突破,更為甚者是一種倒退,潛意識層面下的對男性的歸順,依舊沒有脫離男性為第一性的局面。
四、結 論
“瑪麗蘇”現象并不是隨著網絡小說的發展才出現的,從人們對完美形象的追求可以從古代的才子佳人小說來追溯,而“情”“美”的主題更是千年不衰。這是人類永恒的追求,但在文學創作中,卻是以女性居多。男性依舊站在政治權利的制高點,擁有絕對的話語權。“瑪麗蘇”小說在受到評論界詬病的同時依舊有很多的作品騰空而出,而閱讀率也依舊高漲。不得不承認,“瑪麗蘇”現象在某種程度上契合一些社會群體的需要。從創作者以女性群體來說,這是屬于其完美個人理想的寄托,個人化的敘述更是充分的自由的暢快的表達自己的情緒。而對于接受群體來說,這是一場釋放壓力與逃避現實的港灣,在快速發展的現在,自我意識加強,個人欲望得不到滿足。“瑪麗蘇”也是一場關于欲望的白日夢,“瑪麗蘇”就是對現實世界的一種心理補償。而“瑪麗蘇”現象中無論是以少女為主的創作者或受眾,還是故事中塑造的女性形象都自覺不自覺地體現了一定的女性意識。隨著西方女性主義的發展與傳播,國內女性主義也有所發展,女性文學也在慢慢地完善。網絡文學中“瑪麗蘇”小說是否屬于女性文學還有待商榷,但是其中所透露出的某種女性意識是明確的,不管是從積極的一面還是消極的一面,能夠引起社會對女性生存地位的反思,都可以稱得上是一種進步,這是社會的進步。女性主義與女性文學,應該怎么走出困境,女性又該如何表達應有的權利等問題,這是需要整個社會一起來努力達到的理想境界,不僅僅是女性群體,而且男性也應該為創造一個真正平等的社會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