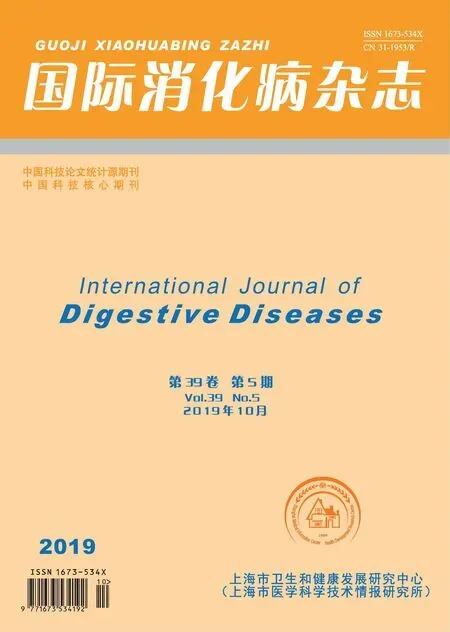藥物性肝損傷體外檢測平臺的研究進展
藥物性肝損傷(DILI)是指由各類處方或非處方的化學藥物、生物制劑、傳統中藥、天然藥物、保健品、膳食補充劑及其代謝產物乃至輔料等所誘發的肝損傷。在中國成年人中,有10%~50%的丙氨酸氨基轉移酶升高是由藥物引起的。DILI也是導致藥物研發終止和撤藥的常見原因。DILI根據發病機制分為固有型DILI(InDILI)和特異質型DILI(IDILI)兩種,前者是可預測的,個體差異不顯著,而后者與個體對DILI的敏感度有關,個體差異顯著,是不可預測的。如何在藥物上市前預測該藥的肝毒性,如何在個體用藥前評估其發生IDILI的風險,從而指導個體精準用藥,是目前關于DILI的研究熱點。本文結合藥物在肝臟內的代謝過程,就IDILI體外檢測平臺的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1 藥物在肝臟內的代謝過程及IDILI的發病機制
1.1 第Ⅰ相反應
在肝細胞內,非極性藥物在Ⅰ相藥物代謝酶(ⅠDME)的作用下,通過氧化、還原和水解等反應,轉化為活性形式發揮作用。ⅠDME屬于細胞色素P450(CYP450)氧化酶家族。CYP450對藥物的代謝具有雙向性,主要代謝途徑是對藥物原型進行滅活或脫毒,而次要代謝途徑則可能使原型化合物進行致毒或致癌活化等。由于CYP450存在基因多態性,部分個體在代謝過程中會積蓄有毒或致癌物質,造成肝損傷;或原本沒有抗原性的藥物經肝臟轉化成具有抗原性的代謝產物,引起免疫性肝損傷。有研究報道,來氟米特介導的肝毒性與CYP2C9*3基因型相關[1]。
1.2 第Ⅱ相反應
肝細胞內,藥物分子的極性基團(大部分是經ⅠDME代謝產生的)在Ⅱ相藥物代謝酶(ⅡDME)的作用下,與內源性化合物經共價鍵結合,生成極性大、水溶性高的化合物,經膽汁排泄。部分藥物通過ⅡDME解毒,如果ⅡDME基因突變,ⅡDME的活性下降,將會導致IDILI。葡萄糖醛酸轉移酶1A1(UGT1A1)是體內催化葡萄糖醛酸與底物結合的重要的ⅡDME。UGT1A1基因啟動子TATA盒區域TA重復序列的基因多態性,導致隨著TA重復序列的增加,酶的表達及活性下降,影響相關藥物的代謝,其中典型的是尼洛替尼。研究發現,應用尼洛替尼治療的患者中,含7個TA重復序列的純合子TA(7)TA(7)(即UGT1A1*28)基因型發生高膽紅素血癥的概率明顯高于含6個TA重復序列的純合子TA(6)TA(6)基因型和雜合子TA(6)TA(7)基因型,提示臨床上對于UGT1A1*28等位基因患者應慎用尼洛替尼,防止出現高膽紅素血癥[2]。
1.3 第Ⅲ相反應
藥物或代謝產物經由藥物跨膜轉運體排至膽汁或血液循環中。藥物轉運體位于肝細胞頂端或肝小管膜上,藥物經由它的轉運出入肝細胞。轉運體蛋白的基因變異可導致肝臟疾病,其功能障礙還會引起藥物在體內蓄積,這也是IDILI的發生機制之一。檢測這些藥物跨膜轉運蛋白的活性對于預測個體對藥物的易感性具有重大意義。
1.4 脂質過氧化損傷
肝細胞的脂質過氧化損傷是IDILI的重要發病機制之一。脂質過氧化反應產生的活性氧能造成肝細胞損傷。細胞線粒體中存在多種抗氧化酶,能拮抗活性氧引起的脂質過氧化損傷,比如超氧化物歧化酶2,其基因變異可增加肝臟對抗結核藥物的易感性,導致藥物在肝臟內蓄積,引起肝內膽汁淤積[3]。
1.5 免疫反應
第Ⅰ相反應生成的中間代謝產物作為半抗原,能被肝內淋巴細胞識別,啟動針對該半抗原及肝細胞的炎性反應,導致急性肝損傷和藥物誘導的自身免疫性肝炎。另外,肝內吞噬細胞能吞噬壞死或凋亡的肝細胞,將其作為抗原遞呈給主要組織相溶性復合體(MHC),后者再通過T淋巴細胞啟動免疫反應,釋放多種細胞因子,包括炎性細胞因子[如γ-干擾素(γ-IFN)、白細胞介素-1α(IL-1α)等],以及具有抗炎作用的細胞因子(如IL-4、IL-10等),當兩種細胞因子作用失衡,就會導致DILI。在對乙酰氨基酚引起的DILI中,IL-1α和γ-IFN的表達水平升高;IL-4和IL-10的基因突變能使雙氯芬酸誘導的DILI風險升高[4]。MHC由人類白細胞抗原(HLA)基因編碼,HLA是目前已知的人類染色體中基因密度最高、多態性最為豐富的區域,在不同的種族或同一種族不同群體中的分布有明顯的種群特征,從而導致個體對藥物的反應不一,這也是IDILI的發病機制之一。
2 IDILI的體外檢測平臺
近年來,有關IDILI體外檢測平臺的研究取得了較大進展。這對于IDILI的診斷、藥物上市前的肝毒性預測和評估有較大意義,下文將從基因水平、細胞水平和組織水平分別對各檢測平臺作一介紹。
2.1 基因水平的IDILI檢測平臺
全基因組關聯研究(GWAS)揭示了HLA基因多態性與IDILI的相關性,證實了由于風險等位基因的存在,使個體有更高的患IDILI風險,對于指導個體化用藥有重大意義。
阿巴卡韋(abacavir)是治療艾滋病的藥物,接受該藥治療的患者中約有4%發生過敏反應,部分過敏反應是致死性的,GWAS已經證實HLA-B*5701等位基因與患者對阿巴卡韋的高敏反應有關,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FDA)推薦應在進行阿巴卡韋治療前檢測HLA-B*5701等位基因情況,相關的試劑盒已經商品化,這是將藥物遺傳學應用于指導藥物臨床應用的成功案例[5]。氟氯西林是一種半合成青霉素,該藥可導致膽汁淤積型DILI。研究表明,有HLA-B*57∶01等位基因的患者應用該藥時,發生DILI的概率是沒有該等位基因的患者的81倍。盡管研究結論令人鼓舞,但是氟氯西林所致肝損傷的發生率僅8.5/100 000,使得該等位基因檢測試劑盒的臨床應用價值有限[6-7]。米諾環素是一種半合成的四環素,基于白種人的研究表明HLA-B*35∶02等位基因與米諾環素引起的肝損傷密切相關[8],但由于米諾環素引起的DILI發病率較低,且HLA-B*35∶02等位基因陽性率在白種人中僅為0.3%,在非裔美國人中甚至僅為0.1%,使得該等位基因預測米諾環素引起的DILI的價值不高,但是可用于鑒別米諾環素引起的DILI與自身免疫性肝炎[9]。
2.2 細胞水平的IDILI檢測平臺
2.2.1 單細胞平臺 目前原代人類肝細胞被認為是預測DILI最好的單細胞模型。但該細胞來源不易,制備成本高,且在體外培養中會迅速失去關鍵功能,使其應用受限[10-11]。利用能表達藥物代謝酶、轉運蛋白和氧化/抗氧化酶的永生化細胞系模擬肝臟細胞,進行藥物代謝研究,具有成本低、可調控和重復性好的優點。其中常用的是THLE細胞,它是利用SV40大T抗原轉化使上皮細胞永生化形成的細胞系。該細胞系中DME的表達量較低,研究者可以利用轉基因方法使其表達特定組合的DME,觀察藥物的代謝情況,并制成劑量-效應曲線[12]。Leite等[13]使用CYP450轉基因的THLE細胞成功評估了多種藥物的DILI風險。HepaRG細胞是來源于人肝前體細胞系的終末分化肝細胞,保留了多種原代肝細胞的特征,包括DME、藥物轉運蛋白體、核受體的表達等[14]。Mueller等[15]發現HepaRG細胞在懸浮的液滴狀態下具有三維生長潛能,且其中DME關鍵酶的表達遠大于單層細胞狀態。
Benesic等[16]開發了MetaHeps系統,該系統利用來源于受試者外周血的單核細胞衍生的肝細胞樣細胞(MH細胞)對藥物進行肝毒性檢測。由于該MH細胞具有受試者的個體特征,故MetaHeps系統適用于IDILI的檢測,并可用于研究藥物之間的相互作用[17]。研究發現,MetaHeps系統診斷多藥共用狀態下IDILI的敏感度和特異度均高于臨床上常用的RUCAM診斷量表;對31例IDILI患者(實驗組)和23例非DILI患者(對照組)的MH細胞進行可疑藥物的肝毒性檢測,結果實驗組有29例檢測到了藥物肝毒性,而對照組中無1例出現肝毒性,表明MetaHeps系統診斷和預測IDILI的敏感度和特異度都較高;1例IDILI患者同期服用84種藥物,利用該患者的MH細胞對84種可疑藥物進行檢測,僅4種藥物呈陽性表達,表明MetaHeps系統有助于明確多藥共用IDILI患者的致病藥物[18]。中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老年人常罹患多種疾病,需同時服用多種藥物,而大部分藥物通過肝臟代謝,在老年人多藥共用狀態下如何預防及診斷IDILI是臨床醫生面臨的棘手問題,MetaHeps系統無疑可作為一項實用的方法。
利用干細胞技術制備的人類細胞篩查腺瘤檢出率是預測IDILI的一種有前景的方法。隨著可誘導的多能干細胞(iPSC)問世,使利用個體的iPSC進行IDILI預測成為可能。干細胞具有多向分化潛能,如何使個體的iPSC分化為所需要的肝臟細胞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iPSC可以分化為肝細胞樣細胞(HLC),Szkolnicka等[19]的研究表明分化的iPSC能表達CYP1A和CYP3A,并與體外培養的凍存肝細胞表現出相似的藥物應答。但是,HLC目前還無法具有完全成熟的肝細胞表型[20]。
IDILI的復雜性意味著目前沒有任何一種單細胞模型能夠充分模擬DILI的全過程,不論這種細胞是原代人肝細胞、肝細胞系還是來源于干細胞。盡管如此,模擬肝細胞主要特征的單細胞模型在評估潛在的肝損傷風險方面還是具有價值的,對于建立復雜的多細胞肝臟模型也是至關重要的。
2.2.2 肝臟細胞的共培養體系 肝組織中除了肝細胞,還有膽管細胞、間質細胞和多種免疫活性細胞。Kostadinova等[21]應用多孔層狀尼龍支架培養肝細胞、肝星狀細胞、庫普弗細胞和內皮細胞,制成共培養體系,該體系內的細胞能夠沿著尼龍支架生長成三維結構,具有正常肝組織的功能,并能維持11周,通過向支架中加入脂多糖能誘導產生炎性細胞因子。此研究利用該體系成功檢測了CYP450活性和肝細胞對藥物的攝取。另有研究者利用成纖維細胞和肝細胞共培養來模擬肝臟的微環境,但由于該體系內細胞是單層培養,而且僅有兩種細胞,缺乏多樣性,不能反映真實的肝組織環境,在檢測藥物肝毒性過程中出現的假陰性較多[22]。有研究者用基質細胞代替該體系中的成纖維細胞,結果也不容樂觀[23]。Rose等[24]將肝細胞和庫普弗細胞置于24孔膠原涂層板內共培養,成功模擬了肝臟的炎性反應。利用該共培養體系可以對CYP450的活性和免疫反應進行檢測。Chen等[25]報道利用原代人肝細胞構建的多細胞共培養體系對19種已經被FDA證實的肝毒性藥物進行檢測,發現其預測藥物肝毒性的敏感度達100%。
隨著微流體技術、生物打印技術和組織工程技術的不斷發展,研究者已經不滿足于僅將肝細胞和肝臟非實質細胞混合培養的二維共培養體系。肝組織缺血缺氧會影響肝細胞功能,為了模擬血供對肝細胞代謝能力的影響,自2010年以來,多個研究團隊對包含肝細胞和肝臟非實質細胞的微流體共培養裝置進行了研究,在這個裝置中,培養肝臟細胞的微環境是液態的,而且它的氧供和流動性等參數是可調節的。研究者發現,肝細胞和肝臟非實質細胞在微流體共培養體系中生長,肝細胞的I DME活性明顯高于靜態的共培養體系以及不含非實質細胞的微流體培養體系。另外,該共培養體系能成功形成膽小管,并可以檢測轉運蛋白的活性,它的缺點在于不能進行高通量的藥物篩選,目前只用于實驗室研究[26-27]。據報道,利用組織工程技術和新型生物材料構筑球形基質,將肝臟細胞置于其中的微小通道內進行培養,模擬肝臟的三維結構和功能,能模擬肝臟脂肪變性和膽汁淤積[28],已有學者將其用于DILI的研究[20]。有研究者利用組織工程技術制備半乳糖基纖維海綿,將人多能干細胞分化的肝細胞樣細胞(hPSCHLC)用于對乙酰氨基酚、曲格列酮和氨甲喋呤的肝毒性檢測,發現其敏感度明顯優于傳統方法培養的hPSCHLC。
非阿尿苷是禮來公司開發的治療乙型肝炎的抗病毒藥物,在動物實驗中并未發現嚴重的肝毒性不良反應,但是在Ⅱ期臨床試驗中,15例服用該藥的患者中有7例出現肝衰竭,其中5例死亡,該藥的臨床試驗于1994年停止。2011年,Krzyzewski等[29]利用原代人肝細胞和基質細胞構建微模態共培養體系,成功檢測出非阿尿苷的肝毒性,提示利用多細胞共培養體系預測DILI具有光明前景。此共培養體系由于構建復雜,導致成本較高。
2.3 組織水平的IDILI檢測平臺
利用體外培養的精密肝組織切片進行DILI研究,更接近真實的肝臟微環境,能反映肝組織內不同細胞間相互作用和肝組織對藥物的整體代謝過程,相對于多種細胞的共培養體系,其優點顯而易見。Hadi等[30-31]將鼠和人的肝組織切片進行體外培養,成功構建了肝臟炎性損傷模型,已應用于DILI、脂肪肝、肝纖維化的研究中。該系統的缺點在于獲得肝組織切片的過程是有創的,而且組織切片中肝細胞的代謝能力顯著下降,研究者認為肝細胞代謝能力的下降與切片處于靜態的培養體系有關,于是將肝組織切片置于微流體培養裝置中進行培養,發現肝細胞功能得到了良好的維持[32]。
為了更好地模擬肝細胞在體內的生長環境,有研究者將原代人肝細胞原位種植或者異位種植在嚙齒類動物體內,用于DILI的檢測。TK-NOG小鼠能耐受高劑量的非阿尿苷,但原位種植在該小鼠肝臟上的原代人肝細胞表現出與非阿尿苷用藥劑量相關的肝毒性[33]。此檢測方法不適用于檢測由于免疫機制引起的DILI。
3 總結和展望
IDILI具有不可預測的特點,其診斷難度較大。DILI體外檢測平臺對于DILI,特別是IDILI的臨床診治、個體化用藥指導和藥物研發具有重要意義。雖然已有針對發病機制單個環節開發的高通量檢測試劑可用于IDILI的預測,但能夠同時模擬藥物肝臟代謝的整個過程,并具有參數可調控的多細胞或組織平臺對于IDILI的預測無疑更有特異性,這是未來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