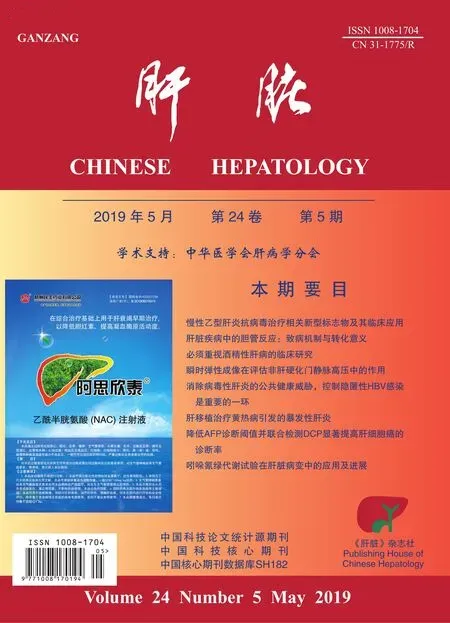必須重視酒精性肝病的臨床研究
韓白乙拉 佟靜 王炳元
近10年來,臨床肝病學的整體格局已經(jīng)發(fā)生顯著改變。隨著乙型肝炎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的有效治療,許多國家的病毒性終末期肝病患者比例明顯下降,酒精性肝病(ALD)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作為當前和未來肝臟相關(guān)健康負擔的主要驅(qū)動因素受到越來越多的關(guān)注。NAFLD可能是全球慢性肝病的主要原因,而ALD仍然是全球肝臟相關(guān)死亡的主要原因[1]。盡管ALD有著巨大的健康和經(jīng)濟負擔,但傳統(tǒng)上它很少受到關(guān)注。最近有學者疾呼“現(xiàn)在是對ALD采取行動的時候了”(Time for action)[2];我們完全同意,應(yīng)該重視酒精性肝炎的臨床研究[3]。
一、ALD是一種預后不良性疾病
流行病學研究顯示,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和印度)酒精攝入量和ALD顯著增加,年輕時開始酗酒者發(fā)生肝硬化的時間比成年期酗酒發(fā)展得更快[1]。由于“非酒精”的界限沒有明確的定義,致使NAFLD與ALD有混淆的趨勢。臨床上單獨因NAFLD住院的患者極少,大部分為無意中(體檢或因其他疾病檢查)發(fā)現(xiàn),而ALD中的酒精性肝炎(AH)或酒精性肝硬化(ALC)往往有明顯的臨床癥狀而需要住院干預。
ALC患者的預后非常差,5年病死率為71%,15年病死率為91%。歐美國家飲酒者超過一半,約1/3的肝病死亡與酒精有關(guān)。發(fā)達國家大約60%~80%的肝病死亡是由于酒精過量造成的,更重要的是死亡的ALD患者2/3是青壯年。這與其他主要慢性疾病(如缺血性心臟病、中風和肺癌)形成了強烈對比,后者青壯年大約占1/3。根據(jù)世界衛(wèi)生組織(WHO)2018年《全球酒精和健康狀況報告》,這種趨勢可能仍會持續(xù)。由于經(jīng)濟的快速增長,中國的酒精消費在過去30年中增長最快[4]。
飲酒模式的變化影響著肝病的病死率。在英國,肝病病死率增加只與總體消費量適度增加有關(guān),但與從酒吧消費的低度啤酒到在家飲用廉價的烈性酒的轉(zhuǎn)變有關(guān),后者還與狂飲文化有關(guān)。東歐部分地區(qū)以烈性酒為主,法國和意大利主要是飲用廉價的葡萄酒。
二、ALD分期系統(tǒng)的特殊性
ALD的疾病譜包括酒精性脂肪肝(AFL)、AH和ALC,還應(yīng)該包括酒精相關(guān)性肝細胞癌(HCC),病理上還包括酒精性脂肪性肝炎(ASH)和酒精性肝纖維化(ALF)。ALD 疾病的進展并不都是按照AFL-AH-ALC-HCC的順序發(fā)展。ALF是基礎(chǔ),ALC是終末期表現(xiàn);AH往往伴隨著ALF,AH可以發(fā)生在ALD的任一階段,有時會發(fā)生重癥AH(sAH),如果sAH發(fā)生在ALC,部分表現(xiàn)為慢加急性肝衰竭(ALD-ACLF)。這種無序的排列造成臨床表現(xiàn)錯綜復雜,也就引來無數(shù)的紛爭[5]。
復雜臨床表現(xiàn)的原因主要源于ALD病理改變的特殊性。與大多數(shù)以門脈纖維化為基礎(chǔ)的慢性肝病相比,ALD或NAFLD的脂肪性肝病與肝小葉中心型損傷相關(guān),后者導致靜脈周圍纖維化(PVF)和/或竇狀隙和細胞周圍纖維化(PCF),這是發(fā)展為肝硬化的基礎(chǔ)。現(xiàn)有的炎癥和纖維化評分系統(tǒng)是否適合ALD或NAFLD?目前仍然缺乏ALD臨床管理和試驗所需的特異性分期系統(tǒng)標準。盡管NAFLD和ALD之間存在形態(tài)相似性,但臨床和組織學特征的差異又可能嚴重限制了已經(jīng)建立的NAFLD特異分期系統(tǒng)在ALD診斷和預后中的應(yīng)用。在類似的臨床環(huán)境的自然史研究中,即使NAFLD患者已發(fā)展成肝硬化,幾乎沒有一個出現(xiàn)肝功能失代償,而ALD患者有較高的嚴重纖維化或肝硬化的發(fā)生率和首次診斷時的臨床失代償。在開發(fā)ALD特異性纖維化分期系統(tǒng)時,已知的與預后相關(guān)的特征除了結(jié)構(gòu)紊亂(PVF)的定義外,還必須考慮PCF的程度和肝硬化的嚴重程度[6]。
三、ALD發(fā)病機制的復雜性
酒精一直被認為是一種直接的肝毒性物質(zhì),攝入的酒精會在腸道和肝臟被乙醇脫氫酶代謝成乙醛。酒精及其代謝產(chǎn)物乙醛會改變腸道菌群,損傷腸道黏膜的完整性和先天免疫功能,其結(jié)果不僅影響腸黏膜屏障,更重要的是增加了腸道的通透性(滲漏),允許酒精和代謝產(chǎn)物乙醛、細菌、細菌的碎片、細菌的代謝產(chǎn)物內(nèi)毒素(脂多糖),可能還有病毒和真菌,以及腸黏膜壞死組織的碎片等通過門靜脈循環(huán)進入肝臟,由病原體相關(guān)分子模式(PAMPs)激活巨噬細胞中的炎癥通路,導致肝細胞無菌壞死、凋亡和/或焦亡。肝細胞損傷又導致?lián)p傷相關(guān)分子模式(DAMPs)的釋放,DAMPs與PAMPs類似的方式刺激肝巨噬細胞,形成惡性循環(huán)[7]。
另外,DAMPs與PAMPs 都能激活多種細胞類型,包括免疫細胞、肝細胞和肝非實質(zhì)性細胞,從而釋放趨化因子、其他細胞因子、急性期反應(yīng)蛋白和細胞外囊泡(EVs),它們在ALD炎癥反應(yīng)的調(diào)節(jié)中起著重要作用。特別是EVs,除了轉(zhuǎn)移小RNA外,還可以將RNA、DNA、脂質(zhì)、蛋白質(zhì)等轉(zhuǎn)移到靶細胞,調(diào)節(jié)ALD炎癥。EVs還可以將熱休克蛋白-90和CD40L等蛋白質(zhì)轉(zhuǎn)移至巨噬細胞,由DAMPs與PAMPs激活觸發(fā)肝臟的炎癥。EVs還能與補體C5aR1相互作用促進脂肪細胞釋放脂肪因子。原核生物(細菌微泡)也可釋放EVs,參與腸道細菌與腸上皮細胞或肝細胞之間的潛在串擾(cross talk)。如何調(diào)節(jié)不同肝細胞類型的EVs釋放以及不同ALD疾病譜中EVs對細胞的不同靶向性是一個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由此可見,EVs涉及腸道、肝臟、脂肪組織、肌肉、肺部和神經(jīng)內(nèi)分泌系統(tǒng)的器官間交叉對話(串擾),也可能有助于ALD的炎癥發(fā)展[7]。
四、ALD臨床試驗的異質(zhì)性
ALD相關(guān)的臨床試驗不僅缺乏,僅有的臨床試驗結(jié)果的異質(zhì)性也較大。原因主要在于:(1)患者和家屬的不配合,臨床試驗中的招募具有很大的挑戰(zhàn)性,需要大量參與者來達到有意義的統(tǒng)計能力水平是很困難的,特別是獲取以病死率為終點的試驗難以實現(xiàn);(2)ALD患者多數(shù)有心理障礙,無法得到準確的飲酒量和飲酒時間,無法預測患者戒酒或復飲,不可避免地影響患者疾病程度的判斷;(3)既有肥胖又有飲酒,ALD與NAFLD的區(qū)分沒有統(tǒng)一的共識;(4)盡管sAH患者被認為是藥物治療試驗的優(yōu)先事項,但AH患者極易感染和誘發(fā)急性炎癥反應(yīng)綜合征(SIRS),病情較輕的患者用免疫調(diào)節(jié)藥物可以從治療中獲益,多數(shù)學者還是擔心可能使病情惡化,急需開發(fā)新的、更安全、更有效的治療藥物[8];(5)早期ALD的臨床試驗需要避免失代償性肝病常見的晚期表現(xiàn),包括近期發(fā)生的嚴重胃腸道出血、腎功能嚴重受損(血清肌酐>3 mg/dL)、呼吸機或升壓藥支持的患者,以及病毒活躍復制(HBV DNA或HCV RNA陽性)的病毒性肝炎患者。因此,ALD臨床試驗開發(fā)的早期階段,對納入和排除標準確定試驗患者的類型要有更高的共識。
五、ALD臨床診斷的挑戰(zhàn)性
肝活檢仍然被認為是建立明確診斷和評估ALD不同階段的金標準,但病理診斷仍然具有很大的挑戰(zhàn)性。因為與NAFLD不同,ALD具有獨特的病理改變,包括細胞的氣球樣變、巨大線粒體、中性粒細胞浸潤為主、mallory小體、小膽管損傷和膽汁淤積、相對粗大的纖維間隔等都明顯增多。目前國內(nèi)外尚無ALD統(tǒng)一的病理診斷標準。
在過去的10年中,已經(jīng)開發(fā)出非侵入性試驗來評估肝纖維化和脂肪變性的嚴重程度。瞬時彈性成像測量肝硬度已成為評價纖維化最常用的非侵入性參數(shù)。在ALD中,瞬時彈性成像已被證明具有很好的檢測晚期纖維化和肝硬化的性能。然而,在解釋肝硬度cut off值時,必須考慮肝功能酶學水平、膽汁淤積、肥胖和飽餐。部分血清學生物試驗(FIB-4和APRI等)也常被推薦用來評估ALD的肝纖維化,仍缺乏大樣本的驗證。
超聲診斷仍然是脂肪肝診斷的初步檢查手段,并能排除腫瘤性或血管性疾病,但限于人員技術(shù)和機器靈敏度的差異,對脂肪變性或纖維化的判斷均有較高的誤差。磁共振波譜和磁共振彈性成像技術(shù)具有很高的準確性和可重復性,在組織學脂肪變性檢測方面具有比超聲更高的靈敏度和特異性。然而,低利用率和高成本限制了該技術(shù)在常規(guī)臨床實踐中的應(yīng)用。最近,受控衰減參數(shù)被開發(fā)成一種新的非侵入性評估肝臟脂肪變性的工具;與瞬時彈性成像相結(jié)合,診斷的準確度更好。診斷和預測各種ALD疾病譜的非侵入性技術(shù),以及新的血清生物標志物也正在積極研究中。
六、ALD嚴重程度評估缺乏特異性
真正單獨應(yīng)用于ALD嚴重程度和預后判斷的只有Maddrey判別函數(shù)(mDF),它僅包括總膽紅素和凝血酶原時間兩個實驗室指標。mDF = 4.6 ×(實測凝血酶原時間-標準的凝血酶原時間)+ 總膽紅素(mg), 當mDF≥32定義為重癥,如無糖皮質(zhì)激素應(yīng)用禁忌證,可考慮4周療程的潑尼松龍(40 mg, 28 d,直接停藥或在2周內(nèi)逐漸減量停藥,激素治療7 d再評估決定停藥或使用28 d)。由于與肝衰竭的實驗室指標重疊,很容易誤認為肝衰竭而失去GC治療的機會,而“極度乏力、消化道癥狀,肝性腦病”的表現(xiàn)是肝衰竭的重要特征。藥物性肝損傷的膽汁淤積型也往往符合mDF的評分,是否也可用激素沖擊,仍需進一步研究。實際上酒精也是一種特殊藥物。
終末期肝病模型(MELD)來源于肝移植前肝功能的評估,并非單純用于終末期ALD患者,所以沒有特異性。MELD包括總膽紅素、國際標準化比值和肌酐(可以在www.lillemodel.com中獲取),比mDF僅多了一個肌酐,所以也常用于sAH的評估,MELD>20(也有指南定義為21)就可診斷。其他評分系統(tǒng)還包括ABIC (年齡、膽紅素、INR和肌酐)評分和 Glasgow酒精性肝炎評分。由于計算公式比較復雜,均沒有被ACG指南推薦。
ACLF是肝病學中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慢性肝病患者迅速發(fā)生進行性肝功能失代償、多器官衰竭和短期病死率增加。雖然ACLF的病因在世界范圍內(nèi)有所不同,但近期酗酒是ACLF發(fā)病機制中常見的誘發(fā)因素。ACLF是所有病因肝硬化患者終末期常見的并發(fā)癥,也是死亡的重要原因。然而,迄今為止,沒有任何研究區(qū)分不同病因?qū)е翧CLF的臨床特點,即使EASL的ACLF指南中,也只有65%與飲酒有關(guān)。在ALD背景下發(fā)生的ACLF稱之為ALD-ACLF,主動飲酒、AH和細菌感染是導致ALD-ACLF發(fā)展的最常見事件。因此,不能將EASL-CLIF的評估方法套用于sAH,更不能將mDF≥32的sAH診斷為ACLF。酒精誘導發(fā)生的ACLF可能是ALD的一種特殊形式,也可能是sAH的臨床進展[5]。黃疸和凝血異常同樣是sAH的表現(xiàn),更多的可能是ALC患者出現(xiàn)了sAH未能得到及時治療而發(fā)展到ACLF。sAH是大量酗酒誘發(fā)的SIRS臨床表現(xiàn),ACLF是SIRS未及時糾正(特別是合并了感染)導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的結(jié)果[3]。由此可見,sAH不等于ACLF,一旦合并ACLF病死率明顯增加。由于缺乏有效的鑒別診斷方法,貽誤了激素治療sAH的時機,相繼出現(xiàn)多器官功能障礙,最終導致ACLF的發(fā)生。
七、百花齊放的ALD治療方法
當前,戒酒、營養(yǎng)支持和GC仍然是sAH的治療基礎(chǔ),針對先天免疫和腸-肝軸的藥物開發(fā)是國內(nèi)外研究的方向,其他正在開發(fā)或試驗的藥物包括抗炎藥、抗氧化劑和作用于肝細胞再生途徑的藥物[8]。
非靶向治療作用于腸-肝軸的藥物臨床研究比較成熟。如飲食、益生菌、抗生素和糞便微生物移植(FMT)等,獨立或聯(lián)合GC應(yīng)用于ALD的治療。特別是FMT可降低疾病嚴重程度,減少或解決諸如腹水或肝性腦病等肝病并發(fā)癥,并提高一年生存率(88%對33%,P=0.018)[8]。針對細菌LPS的研究也已初見端倪。純化的超免疫牛初乳(IMM-124E)中含有抗LPS的IgG抗體,能夠減少血漿LPS,并可作為GC輔助劑而得到有益的結(jié)果;由于脂多糖激活TLR4受體啟動炎癥信號傳導,TLR4拮抗劑也是治療ALD的另一個潛在靶點。
除了國內(nèi)眾多的抗炎保肝藥物之外,國外正在研究的包括IL-1受體拮抗劑anakinra,法尼醇X受體激動劑奧貝膽酸,泛半胱天冬酶抑制劑emricasan,凋亡信號調(diào)節(jié)激酶-1(ASK-1)抑制劑Selonsertib (GS-4997)等。對AH患者具有潛在臨床益處的下調(diào)炎癥的其他治療方案還包括:靶向IL-1b的單克隆抗體(canakinumab)、趨化因子CCR2/5(cenicivroc)的拮抗劑、抑制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cp-1)、降低尿酸水平(別嘌呤醇和丙磺酸鈉)和micro-RNA (miRNAs)等等。
抗氧化劑在治療AH方面沒有顯示出更多的益處,唯一顯示出一些臨床療效的抗氧化劑是乙酰半胱氨酸和美他多辛,兩者均可作為GC的輔助治療,能夠提高患者3個月和6個月的存活率,當然還要進行更大的多中心隨機研究。抗氧化劑治療AH失敗的原因之一可能是這些藥物難以進入線粒體,缺乏特定的線粒體抗氧化作用。使用中和腫瘤壞死因子藥物(如英夫利昔單抗和依那西普)的臨床試驗沒有得到預想的療效,相反具有更高的病死率和更多的不良反應(yīng),特別是與感染相關(guān)。
肝臟具有強大的再生能力。在一項前瞻性臨床研究中,AH患者產(chǎn)生IL-22免疫細胞的密度與生存率相關(guān),這些強有力的數(shù)據(jù)使IL-22成為治療AH的一個重要靶點;肝祖細胞和骨髓源干細胞(包括中性粒細胞)已被證明可促進肝再生;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等生長因子似乎是治療sAH的一種有前途的藥物,使用G-CSF可刺激CD34陽性造血干細胞,能夠增加這些細胞在肝組織上的密度,增加中性粒細胞血球計數(shù),改善肝功能,降低MELD評分,減少感染和敗血癥的發(fā)生率,提高總生存率[8]。
早期肝移植已成為危及生命的sAH或終末期ALC的標準治療方法,但由于擔心器官供應(yīng)有限以及患者復飲的風險,其仍然是爭議的焦點。鑒于sAH的短期病死率高、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以及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6個月規(guī)則不公平地排除了有利的候選者,歐洲對sAH進行了一項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試點研究,之后在美國的回顧性分析中也得到了證實,使對藥物治療無反應(yīng)的高度選擇的sAH患者的治療模式發(fā)生了轉(zhuǎn)變。然而,迫切需要進行前瞻性研究,以解決高度選擇的標準和對酒精使用障礙患者的長期結(jié)果的爭議[9]。
八、重視ALD的研究
公共衛(wèi)生政策和價格的制約是ALD的一級預防,也是戰(zhàn)勝ALD最具成本效益的策略,但是又受制于各國酒文化的影響。戒酒是唯一有效的治療ALD的方法,同樣受酒文化的影響和人們對飲酒的寬容,ALD的癥狀被掩蓋,導致戒酒開始太晚,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無法防止過早死亡。因此,促使行政部門的決策者正視酒的危害、盡快制定公共衛(wèi)生政策、加強社區(qū)醫(yī)生的培訓,做到早篩查、早治療[4];動態(tài)評估肝生化指標是臨床研究中最實用的選擇,應(yīng)根據(jù)疾病嚴重程度進行分層,以避免病死率風險顯著不同的患者不均勻分布在臨床試驗中,導致試驗結(jié)果的異質(zhì)性;建立臨床試驗設(shè)計的共識有助于ALD研究的規(guī)范[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