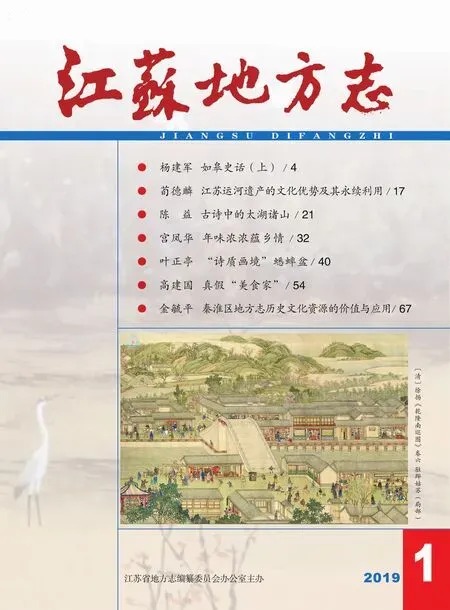石匠軼聞
◎ 涂俊明
曾經的老家,除了平原沃土與波光粼粼的河流外,就是那些高高低低、長長短短的山峰,錯落有致,起伏舒展,是一道故鄉特有的風景。這些山峰群巒中,除了長滿郁郁蔥蔥的植被綠林外,有些山頭還有嶙峋的石峰,且以石灰巖、青石為多,是大自然留下來的寶貴資源。
靠山吃山,似乎是“千年一貫制”的民諺。老家的圣塔山、水母山、白金山、高嶺山以及南部的壽安山群都長著千萬歲的石頭。在靠山生活的鄉民百姓中,生存著一股與石頭打交道的人群,人們管他們統稱為石匠。
當老石匠來到作業現場,放下長方形的木頭工具箱,總會將那些工具鋪放下來,便于隨時取用。大錘、二錘、鋼釬、楔子、鏨子、手錘、手扳風箱,還有劃線的鋼尺和彈線用的墨斗。這些鐵家伙們各有各的用處:大錘和楔子都是開山用的;二錘是砸線用的;鋼釬是撬石頭用的,起到杠桿作用。鏨子的用處較多,在剖、削、鏤、鏟、磨都要用到它,依據用途不同,有長短鏨之分,還有扁鏨之說。“磨”這道工序一般都是用扁鏨。鏨子還有尖口和平口之分,尖鏨一般用于打窠臼、鏤空之作,而平鏨則是在后期鏟平用。
石匠,簡單地分為粗匠、細匠兩大類。粗匠是把山上的石頭采切成大小長短不一的原料石,細匠一般是在山下,或磨,或雕。早年,幾乎家家戶戶都用得著他們,石敢當、搗臼、銘記、碑文、石磨、磉盤、石獅子等等全是石匠們一錘一錘鑿出來的。
石頭是堅硬的,石匠則是“吃硬”的。他們以采石頭、鑿石頭、賣石頭作品為生,是名副其實的“石頭漢子”。
石匠們代代傳承著技藝,開鑿出許許多多的石頭產品,留下了斑駁陸離的軼聞趣事。
“斷磨”石匠的扇形圖
年幼時,每年的秋末,父親總會在母親的催促下,請來鑿磨盤的師傅。那時候的鄉民們稱這種專門鑿磨盤的師傅叫做“斷磨佬”。
上門來“斷磨”的都是四五十歲以上年紀,有著一手硬邦邦的“斷磨”本事。記得他們的手,硬硬的、大大的。十指很粗,勁道強大,手背與手臂上青筋暴突。愛玩撒歡的我們娃兒幾個輪番著,也很難扳倒他強壯有力的一柱大拇指。
“斷磨佬”使喚著型號不一的鋼鏨子,一把拳頭大小的“饅頭型”鐵錘子對著鐵鏨子“鐺、鐺、鐺”地敲打,那冒著白白石粉的鏨子頭,在磨縫條溝里一絲一絲“耕耘”,時不時地吐冒出一串串金亮亮的火花來,他的粗壯手掌移動之后,留下一道道深淺如一的石溝,就是那流淌滑行糧食粉末的磨路。
我們通常看到的多半是石匠給石磨“修道”。老態龍鐘的磨盤,年復一年里上下兩片旋轉磨合,磨棱牙齒就磨損了,磨溝淺了,磨面的阻力大,推拉費勁,出粉率低下。所以,每當石磨的磨棱消磨得差不多了,主婦們就會嚷嚷著當家的,快叫石匠來“斷磨”“洗磨”。這石匠到家,磨塘、磨心、磨棱、磨溝如此這般地開鑿“洗刷”了一遍,新磨牙里好牽磨,石磨便會在一群孩兒們奮力推拉中“上片好似龍吞水,下片就像雪浪飛”,此時此刻,人們都會贊許起“斷磨”的石匠師傅來。
好奇的孩子們總是圍攏在石匠旁邊,看著他不厭其煩地“鐺、鐺、鐺”開鑿著磨道,聽著不緊不慢地說著石磨的事兒,“這磨道大有講究哎,磨心向外走的這些紋路,就是一組規規矩矩的扇子圖嗨。主紋路、支紋路,路路相通,出口在磨圓邊線。紋路受阻不通、紋路深淺不一,就會堵塞,拉磨就費力氣,產量也不高,真正的吃力不討好哦!”老石匠津津樂道,小孩子似懂非懂,就像聽著天書一般。果不其然,在老石匠的鑿刻下,兩幅清晰生硬的“扇形”圖,規規矩矩地刻畫在上下兩片磨盤上。
時過境遷,石磨早早退隱生活,石匠也悄然歸隱,唯有那“鐺、鐺、鐺”的鐵錘與鏨子組合,一絲一毫地“蠶食”石磨的碰擊聲,時隱時現地回蕩耳際。
“圓規”度量的石墩子
舊時,石墩子在人們房舍起居的建筑群體里無處不在,那些圓形、菱形的石墩子大大小小的,是石頭石身的器物,是石匠們“玩石頭于手心”的精美作品之一。
老家的人們自古以來砌房造屋所用的石墩子,都是就地取材,請地面上好手藝的石匠鑿制,按照主人房屋柱子大小,根據各種特定好兆頭好寓意,選定石墩子的大小、高矮、形狀,有些還要在石墩子外表刻鑿上栩栩如生的龍鳳鳥獸圖案。
那時候,老石匠們也沒有量值工具,高明的石匠師傅就是靠著一雙眼睛、一雙繭手,便能夠開鑿出合適的石頭坯料,經過一點點循序漸進的“開、削、洗”,愣是將“石婆頭”敲打成漂亮的石墩子。
老家的橋口、東山、周山、洋渚、夏林等村,是石匠云集的地兒,朱家的鳳林、潘家的海林等高手名家林林總總,能工巧匠云集山腰村前。他們一把榔頭一組鋼鏨,走南闖北,揚名遐邇。橋口村石匠大方,文化程度只有“阿拉伯個位數再加名字”,卻有著一手好技藝。他給人家鑿石墩子,眼觀石頭外形,目測算大小,就像把玩泥團,裁量下料。然后再從掃把上折下一根竹絲棒,把住丫杈,用麻線一頭掐住,竹絲棒居中打點,另一頭繞走一圈。如此放樣定尺寸,一陣敲敲打打下來,石墩子不差毫厘。大方們的竹絲棒作“圓規”,陪伴石匠人生路途,度量開鑿無數個石墩子石鎖把。
“規整”筑造的石庫門
石庫門,在舊時的建筑中很受待見,也是主人身份與望族家業規模的“門面”。石庫門的作者當然就是那些老石匠了。他們遴選那些品質上好的青石條,唯有優級的石材,才能夠開鑿出品相上好、堅固千年的石庫門。
石匠們按照門框的大小,測量尺寸,先是開料。將石材開鑿成需要的高、厚、寬度,做出毛石條坯,才進一步在坯子上做細工。經過一段時間“叮叮當當”的洗禮,使其成為石庫門“橫豎天地”組合。
通常的石庫門有豎檻兩塊、天檻一方、戶檻一塊。
豎檻,又叫筑檻,南方民間習慣把“豎起來”叫做“筑起來”,意思是“立起來”。將左右各一塊按照門的寬度,侍立兩旁。豎檻的頂部一般都留有突出的“雄榫”,兩側各一二。
天檻,就是門頭橫亙的大石板塊。之所以不叫“橫檻”,石匠與主人們都有著講究。頭頂一塊大石頭壓著,不好聽,為去忌諱,喚其“天檻”,是頭頂一方“青天”之吉言。石匠們將天檻又說成“一方”,而避諱“一塊”。天檻的制作中,在兩頭開鑿著與豎檻頂上“雄榫”正好契合的“雌臼”,凹凸交合,天檻與豎檻在頂上完美組成一體,既堅固,又“耦合”,再次印證天地合一的吉語。
戶檻,則是安裝木門的落腳點,石匠把戶檻的“脊”做得筆直且光溜,正好與木門吻合,擋雨遮風。石頭戶檻分為“單篦櫛”與“雙篦櫛”,都因為造型與生活中的篦櫛相似而名。“單篦櫛”戶檻,只是在門檔戶檻一段,寬度一般超出門框之外,呈外八字形,活像一把單面齒的篦櫛;“雙篦櫛”戶檻,則是在戶檻“脊”的內側延伸石檻,只不過是直型而非八字形,多了一對戶樞門窠臼,用來安裝半截小矮門。
所有這些石頭“三件套”“四件套”,組合成為威風凜凜的石庫門并非易事,沒有點兒真材實料,做不成;沒有一手過硬功夫,做不出。石匠們接到用戶邀約,就會精心遴選石料,從石料的成色到形狀挑,再從石面到石紋選,還要從敲擊的石聲聽。有些看上去不錯,但是石體“通筋斜紋”,遲早會崩裂,用不得;那些石面老城,出彩不夠,面子上不靚,要不得;那些身條不錯,雖然“相貌堂堂”,卻石聲沉悶,保不準在開鑿雕刻時“身敗名裂”,老石匠只會將手錘敲打幾下,拂袖而去。所以,要做得一副好的石庫門,光是選料就是百里挑一,猶如在石林里選妃。至于那些裁、削、鑿、光、銑等手藝布施,不說巧奪天工,也是錘錘精煉的“嘔心瀝血”,如此數月雕琢,方能成就“大器”。
“排版”開鑿的石刻文
舊時的石匠隊伍里有一種叫做“文石匠”,其實就是“細石匠”中的一個門類,專門做石雕、石刻之類細工慢活的石匠師傅。就拿鐫刻石碑來說,要做到圖文并茂,栩栩如生,將天地人間之動物景致等惟妙惟肖地鑿刻進石頭,沒有相當的本事豈不是異想天開?
石匠們先將圖像描繪于石體表面,再將文字均勻排列書寫其上,與古代的排版印刷術極似。接下來的就是運用“細石匠”工藝里的短鏨,按照圖案的寬窄、文字的粗細、體例的擺陣,或尖鏨開路,或圓鏨跟進,抑或扁鏨的找平,依據字體、字號、字跡的走向,順溜圖案的凹、凸、淺、深,細工匠手里不斷換用著大小粗細和圓匾不同的鋼鏨子,乒乓乒乓,當啷當啷,石頭印美圖,石刻寫雄文。
石匠人遠去,石刻千萬年。太平橋腹的記載、千手觀音的英姿、社頭碑刻的敘述,還有那些村寨民間百姓林林總總碑刻的宗族碑記,那都是石匠前人們的傳世之作!
“打嶒”挖掘的石頭陣
開山采石為生的叫做“粗石匠”。
山邊世代居住的那些粗石匠,個個臂膀粗壯,力大無比。他們對付石頭的本事“千奇百怪”,其中有一種活兒叫做“打嶒”,那智慧與力量,可了不得!
舊時,采石沒有炸藥,只能夠靠力量與石頭山較勁。粗石匠們選好理想的石頭陣,在反復敲打觀察后,選擇小口里面插上鋼楔子,然后揮舞磅榔二錘,輪流使勁把鋼楔子往石縫里塞,直到把目標石頭與母體分開。他們還會根據石頭形成時留下的鋪層,動用鋼楔子橫插縫線,用鐵錘使勁砸打、震動,再跟進鐵撬的杠桿借力作用,按層剝采石板。
采石高手妙招要數“打嶒”!村里高明的石匠會在石頭鋪層的上方“打嶒”,砸開縫隙或窠臼,以水灌滲窨,利用水的“軟實力”肢解山體,令石頭鋪層“分崩離析”,最終達到山石崩裂,成片的石頭轟然坍塌。石匠用鏨子敲掉多余的邊角,直到毛石變成方石或者塊狀,如要精細的用材,只需用扁鏨把紋理找平,就形成了大量石板等毛料。
老石匠、老作坊的時代遠去了,留下那些石人石馬、石鳥石獸、石龍石鳳,還有那些石頭橋、石板路、石頭墻、石頭墩、石頭碑、石頭城……石匠們如石頭般的頑強精神,還有那聰穎的智慧靈氣,早已融入后人的血液里,在脈動起搏的韻律里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