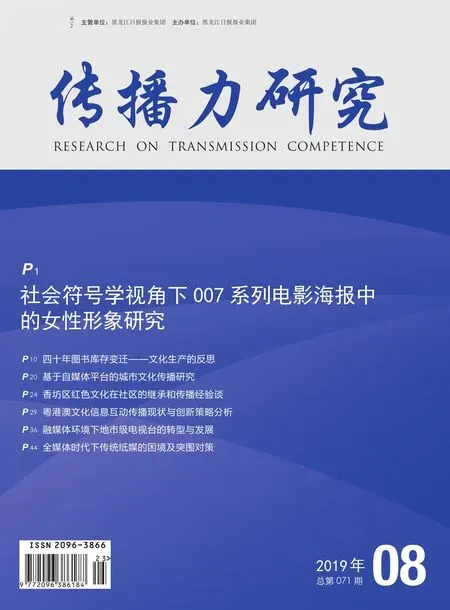社交媒體用戶個人隱私披露成因分析
史倩云 湖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根據CNNIC 的第43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8.29億,而在每個網民手機中,無論是微信、微博還是抖音、快手,社交媒體似乎成為一種標配,于是社交媒體用戶的數據獲取成為了很多媒體和企業的信息來源。
所謂社交媒體和社會化媒體是同一概念,是個人通過互聯網進行信息的共同創作,并可以面向個人社交領域手中傳播的新媒體載體或形態。但在社交媒體時代之下,用戶的隱私侵權問題一直是一個突出亟待解決的問題。百度CEO 李彥宏甚至公開表示:他認為用戶隱私信息是可以被利用的,也側面說明我國網民對于自己的隱私,特別是在社交媒體之中的隱私泄露問題關注度不夠。
一、社交媒體中默認設置與用戶隱私的沖突
站在互聯網公司的角度,流量和盈利是一個重要的生存指標。根據傳播政治經濟學里的“受眾商品論”,受眾被當做了商品賣給廣告商,并且受眾還能通過閑暇時光的“勞動”來創造價值。在大數據時代之下,用戶的數據也能成為一種商品,這種商品雖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實物”,但卻能夠參與到用戶行為、特點與愛好分析,利用到下一次的內容、產品生產過程。
企業在進行受眾用戶信息收集的時候都會有一個相關保護協議。為了更大范圍的采集數據,很多企業會存在一個默認設置,即默認設置通常指向用戶同意這種自身行為的記錄和披露。甚至存在部分社交媒體在用戶使用之初,并未經過用戶知曉就,信息就“被同意”記錄了。很多用戶由于個人對隱私暴露的敏感度和關注度不足,下載軟件之初對于文件內容不會過多關注,希望盡快開啟軟件,于是大多采取默認設置,在此過程中用戶的數據就被“順理成章”的進行記錄。
二、用戶心理是隱私侵權的培養皿
(一)表演與“印象整飾”
“印象整飾”是由著名的美國社會學家戈夫曼所提出,指個人試圖影響他人對于自己印象的現象與過程,也就是對于自我形象的管理。這種對于自我形象的管理不僅體現在日常的行為舉止和穿衣打扮中,在網絡中特別是社交媒體中是進行“自我披露”、“印象管理”的絕佳場所。
網絡中的表演可以通過個人的昵稱、簽名、朋友圈、狀態發布等形式表現出來,而這種狀態的發布加入了個人對自己的認知期待,很多是基于面對“認知失調”的應激反應。而這種表演和“印象整飾”的內容有時會成為自己隱私暴露的來源。當我們去到外地旅游也會發布自己的旅行狀態,在享受美食前第一件事也是先拍照讓“朋友圈”先吃。發布的信息可能包括直接的地理定位信息,或者與自己接觸內容相關的圖片信息。這種地理和圖片信息的暴露是出于個人同意和自主的情況之下,但是也會造成一些不知情的無意隱私侵權。
圖片信息中有時也會暴露準確地理定位,被粉絲親切稱作“老邢”的網紅邢欣瑤,在自己的小號“扛大刀的我”上發布了一張自己在醫院打吊瓶的圖片,圖片中并沒有出現準確暴露醫院名稱的文字,只是醫院輸液處的部分景象,但是卻被粉絲識別具體位置,甚至直接點外賣給正在輸液的“老邢”,即使粉絲是好意,但是這種個人地理位置暴露所帶來的不舒適感使得“老邢”馬上轉換了輸液場所。
(二)第三人效果
第三人效果是由戴維森所提出,指人們在判斷大眾傳播的影響力之際存在著一種普遍的感知定勢,即傾向于認為大眾媒介的信息(尤其是說服性信息或宣傳極其負面信息)對“你”或“我”未必有太多影響,然而會對“他人”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而我們個體在面臨隱私侵權的傷害評估時也會存在著這種心理。即使傳媒為我們揭示了很多關于保護隱私的重要性和隱私侵權的普遍性的事件,但是面對具體情況時個人對于隱私的保護和重視度仍然不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認為這種隱私侵權即使存在,也是普遍存在于他人,而自己受到負面影響可能行比較小。而第三人效果定勢背后的心理依據是“自我強化”,即往往認為自己具有有效避免隱私侵犯的能力,但是其他人并不具備。
三、大數據帶來的隱私隱憂
(一)對于隱私分析的預測帶來的隱私困擾
現在的社交媒體在進行內容推送或信息流排列時多少會應用到算法。而算法新聞也有不同的技術方式依托,其中一種就是“協同過濾”的推薦算法。基于用戶的協同過濾算法的原理是“人以群分”,通過聚類分析若干用戶的行為數據,將行為類似的用戶編入一個隱形閱讀小組,對目標用戶推薦該小組中其他用戶感興趣但未被目標用戶閱讀過的新聞。
這種“人以群分”的數據分析在社會化媒體中已十分尋常,但有時也會涉及到個人隱私問題。個人對于自己的某些狀態、愛好有時是不想為外人所知,想要保密的,但是在大數據面前,基于同類人群的興趣愛好的預測往往使個人隱私無所遁形。
(二)對于歷史信息的記錄
大數據時代之下,“被遺忘”似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所謂“被遺忘權”,指的是信息的主體有權要求信息控制者刪除與其有關的信息,以避免這種信息的進一步傳播,并要求信息控制者有義務斷開與該信息的鏈接,并通知第三方刪除相關信息。
“被遺忘權”可以有效避免人身侮辱、錯誤類信息、歷史信息給當事人帶來的二次傷害,但是在大數據時代之下、特別是在社交媒體之中。這種“被遺忘權”實施難度增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社交媒體之中的傳播權利泛化,不僅是網站平臺或者媒體擁有傳播的權利,而是人人都是記者。在此前提之下,對于已經大范圍傳播的信息進行一一把關的刪除難度會增加。以微博為例,很多以娛樂資訊為主要發布內容的微博認證博主,會以挖掘明星早年的微博、博客內容作為八卦來源。面對自己的之前發布過的很多內容大部分人都覺得是“不堪回首”的,但是在社交媒體中,這種過往發布的內容很容易被挖掘,甚至在自己已經刪除情況下,很可能早前已經被截圖和大范圍傳播,要想做到“被遺忘”,相較于過去傳統媒體發布內容,社交媒體中難度會大大增加。
四、社交媒體用戶隱私披露原則
(一)用戶增強自我防護意識
無論是“印象整飾”中的自我披露還是第三人效果中的減小自己負面影響產生可能性的心理因素,原因歸根結底還是用戶對于自我隱私的重視程度不夠,甚至某些時候就像李彥宏所說:寧愿去用隱私換取便利。
增加自我防護意識過程中還要增強用戶的媒介素養,具體到隱私披露中,包括用戶如何更好地使用、選擇媒介、增強批判意識和甄別的能力;在使用社交媒體過程中合理控制使用的程度和頻度、發表狀態的“披露”程度;以及隱私“被披露”的準則時的細節審查能力。
(二)媒體遵守人文原則
當前的法律硬性保護措施還不夠完善的前提之下,社交媒體平臺需要承擔一定用戶隱私保護的責任。不僅僅是將用戶數據作為流量變現的手段,還需要更注重關于用戶隱私侵權的人文關懷,只有真正“以人為本”,媒體平臺才能夠得民心、更長遠穩定的發展下去。
首先應該完善相關用戶信息的隱私保護協議,明確告知用戶隱私保護協議的存在,并且將內容完整、準確的擺在用戶面前,只有真正經過閱讀、同意的準則才能夠投入運行,承擔起保護用戶隱私的責任和義務。
其次,對于長期使用的社交媒體,用戶會產生一種依賴感和信賴感,便對自己的隱私披露在長期使用的平臺之下不會過多注重。平臺方基于人文原則,也應及時收集用戶反饋、關注用戶需求。因此,為提高用戶對移動社交媒體環境的信任度,提高使用意愿,就需要部分移動社交媒體改變隱私政策默認接受的狀態,使用戶主動閱讀和熟悉隱私政策,以促進移動社交媒體行業長遠健康發展。
(三)法律保護安全底線
法律的保護是隱私保護中最為強制性、硬性措施的一步。一方面法律需要從立法措施上對用戶隱私侵權問題進行明確的規定,從權責劃分、領域劃分、到懲罰措施都需要更加明確,不能使部分倫理違規行為由于規定模糊而鉆了法律的“空子”。從具體實施過程中應當嚴肅,對于不法分子惡意竊取隱私的行為也需要從嚴處理,給予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