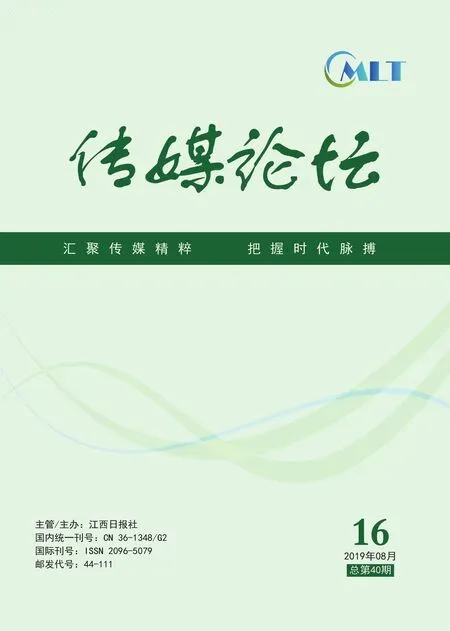日本科幻的美國化難題
——以《攻殼機動隊》為例淺析美式科幻電影的改編困境
王子川
(西南大學文學院,重慶 400715)
2019年,美國科幻電影《阿麗塔》上映,5月,制作人卡梅隆在接受采訪時表明了票房收入遠未達到預期,7月,二十世紀福克斯宣布重新考慮電影續集拍攝的可能性。這是近年來美國科幻電影在改編日本科幻作品時又一次遭遇的失敗。隨著本土科幻創意的衰減,許多美國制片方試圖通過購買日本科幻作品版權為電影提供改編文本,《攻殼機動隊》是這其中的典型代表。但超高的原著人氣和龐大的電影制作成本并沒有實現電影的成功,對《攻殼機動隊》的改編暴露出了美國科幻電影的改編困境。突出的問題是,《攻殼機動隊》沒有繼承發展原作的思想靈魂。美國科幻電影發展的軌跡以及相伴隨的人本化趨勢,決定了它注定不可能還原那些超前而思辨的哲學思考,更無法在電影形而上的領域產生新的突破。就如同電影中義體承載人的思維一樣,它不過是一個年長但前衛的殼承載著更加老邁的思想罷了。
一、從整體思考到個體認知的認同難題
東方國度普遍擁有漫長的歷史與長期的強大,這使得他們的文化能夠跳脫出現實世界的困擾從而向更廣闊的領域發展。這使得蘇軾能夠從整體世界天地的角度思考個人問題。也使得日本《源氏物語》能夠從對個人際遇的悲演進到對自然天地更替的悲。它們作為早期的整體性思考,已經為《攻殼機動隊》(日)的視域拓展提供了較高的基礎。
美國與此不同,這個無時不在為開發生存而埋頭苦干的國家標榜的是實用主義,而拒絕思考與自己無關的東西。體現在美國科幻電影中就是科技對“我”這個個體的影響。在原版影片中,2029年,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高速進步,人與人工智能之間的邊界日趨模糊。人類可以用機器來替代部分身體,來獲得能力的強化和生命的延長;在劇情設定中,很多人在脖子后面裝備了與整體云世界信息相連的輸入端口,個體演變為整體信息系統的終端。主人公“公安九課”的少佐是其中最先進也最復雜的個體,她保留了人體的大腦,采用機器的身軀。原版將少佐的迷茫表現在因為站在整體世界的角度解讀個體,而發出如蘇軾一般蜉蝣的感息,進而傳達對世界的態度。但在美版中,少佐對親情、友情,維護公平正義,發揚英雄主義的興趣都比思考“我在世界中是誰”的興趣要大很多。它的關注核心事實上是人本的,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
這種人本的關注點來自于漫長的美國科幻電影史。如果刨除《月球旅行記》這些早期科幻性質電影的話。從早期科幻電影《太空探險2001》到經典科幻時代的代表作品《異形》《侏羅紀公園》《哥斯拉》,再到新世紀以來,反映生態思想的科幻影片如《金剛》《生化危機》《喜馬拉雅》《猩球崛起》等,科技對人類的影響是美國科幻電影唯一不變的主題。看起來這些電影既有關于工業文明中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也有對科學技術無節發展的批判,甚至在后期幻想了人類命運的終結。有人說這是反人類中心主義的體現,這其實不過是人類中心主義的衍生。
西方研究認為,人類中心主義主要指人類相較同力場其他生命視自己為高等生命,自認為能夠決定包括動物、植物等地球上一切已知生命和一切非生命的存在。現有考古發現已經證明,早在人類文明產生初期,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就已然存在。西方科幻電影中對人類命運的悲哀展望和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思其實立足點還是對人造成了什么后果,目的還是促進人的發展,而非脫離人類視角以一種理性的態度認識社會,這也是造成美版《攻殼機動隊》沉湎于關注網絡犯罪、義體對人的影響等小格局而放棄深入原版唯精神世界等世界觀的主要理論。這種“人本”思想最終導致了大視野退化回小格局。
二、從自然性到人性的思考難題
美國科幻電影另一個突出的趨勢,就是片中的非人一定要具有人行和人性。這種趨勢從《ET》中外星人帶有部分人性和人的行為,到近期“超級英雄”系列人行角色找尋回歸人性的故事。美版的《攻殼機動隊》也走上了同樣的道路。原版中少佐同時具備機器性和人性,在這中間的掙扎與迷茫是引發觀眾形而上思考的動因。其中一段臺詞來自擁有自我意識的機器,解釋了影片的唯精神世界觀,它說道:“生命是存在在信息洪流中的一個質點,DNA對生命而言,就像人類的記憶一樣,獨特的記憶造成了獨特的人……而我則是誕生在信息中的生命體。”在原版作品中,這是最打動讀者的部分,也創造了一種對于人與機器的關系的富有韻味的描述。而在美版中,這種韻味消失了,變成主角直白地和機器劃清界限的無意義感情宣泄:“人性是我的美德”。簡單而粗暴的價值判斷使影片失去了哲學探討的空間,原著中構建的平衡可發展格局退化為單一價值觀導向,喪失了它的科幻意義。
事實上,美國科幻電影在敘事和人物塑造的這種人本性可以追溯到好萊塢“經典敘事”。好萊塢編劇認為,英雄對應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領域的“自我”,而這個形象如果想要成功,就需要讓觀眾產生一種共情。觀眾對人物的認同往往來自對動機的認同,首先要為英雄設計一個觀眾可以認同的動機,之后再讓英雄隨核心事件一同成長。這其實非常符合好萊塢的敘事套路。但是這種套路并沒有能夠拯救劇情,反而硬生生引入諸如復仇、親情等無關枝葉,削弱了原著對“我”的哲學性解讀。
在原版中,主人公有很多赤裸的畫面,在原版對機器性描述的基礎上,我們就可以認知隱含的寓意是對主人公來說,機器身體是衣服一樣的存在,只是一個“殼”。裸體突出了身體的機器性和自然性,強調了自我和本我的對立關系,它并非只是作為別人的觀看物,同時也是屬于自我存在的見證對象。但是由于美版對少佐自然性和人性的剝離,這種裸露最后只成了惡趣味者的福利,不在具備它的情感宣泄作用。
由于本片根本就沒有營造出少佐身上機器性與人性的對立和均衡,而是以好萊塢科幻片一以貫之的“人本位”創作思路,為本片迅速確定了劇情走向和主流價值觀,從而使它一開始就變成了純粹的爆米花電影。最關鍵的是,它回避了一個根本的問題:除了“意識”,“身體”本身是否具有屬性?歷史的本質是時間在個體行為上的反映嗎?個體作為歷史時空的載體,當它開始接受一個全新的“意識”時,它們之間存在形而上的沖突嗎?這些問題本是探討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形而上和形而下問題的關鍵所在。但我們在電影里看到,隨著記憶被植入大腦,意識和身體竟然無縫對接。或許導演根本就不想在這個命題上繼續下去。包括最后一個鏡頭少佐用身體毀滅坦克本應是全劇的高潮,但由于電影根本沒有能夠展開關于存在的探討,自然她身體的破碎就只好如前幾次一樣再去縫縫補補了。影片的精神震撼徹底喪失了,留下的全部是導演讓觀眾得到的生理刺激。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承認,兩種文化對存在的不同認知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本片哲學思辨的力度。在日本神道教中,人們信仰八百神,至于這八百神到底都是誰卻沒有公論。這些神祇存在我們周圍,卻和《攻殼機動隊》中的網絡一樣是一種抽象的存在。日本文化也可以接受形而上的設想,比如德川家康就一直堅稱世間是由大道統領的。但在美國,即使是宗教信仰也是向未降世的天主禱告,形而上的哲學探討本就少見于美國影片中。
三、結論
從美國科幻電影發展的歷史來看,在電影中注重人本人性思想的宣傳一直是他們標榜的,這甚至影響了美國科幻電影中的人物設置和劇情安排。但另一方面,科幻電影中的人本與人性很大程度上卻是不科幻的表現,帶來的后果就是電影靈魂的喪失。尤其是在改編日本科幻作品的過程中,美國科幻電影往往會陷入這種文化困境,對于原作品武斷的工業化加工和生硬的西方文化移植,最終讓電影失去了新意與深度,并在傳播過程中增加了壁壘,最終導致了電影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