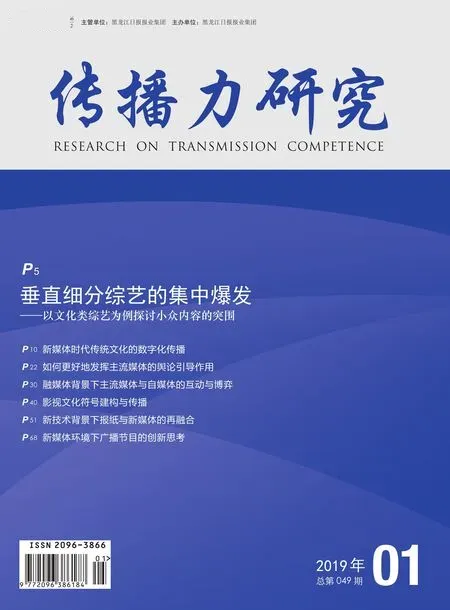從《流浪地球》談中國科幻電影的出路
葛錦 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與歐美國家相比,中國的科幻文化氛圍較為薄弱,科幻影片的數量在電影總產量中的占比也很低。在這種環境下,《流浪地球》能夠突出重圍,不可謂不令人驚喜。影片《流浪地球》值得未來國產科幻片借鑒的成功經驗主要有如下三點:
一、科幻文學為基礎,講述好的故事
科幻電影通常來源于科幻小說,選取科幻小說中的幻想創意或部分情節加以改編、拓展,使其轉化為適宜用于電影拍攝的劇本藍圖,科幻電影可以看作是科幻文學的衍生品。科幻文學起源于歐美,深厚的科幻文學積淀成為歐美科幻電影發展取之不竭的文化寶庫和續航動力。對比之下,中國的科幻文學或許是直到2015年劉慈欣小說《三體》和2016年郝景芳小說《北京折疊》先后取得世界科幻文學最高榮譽“雨果獎”之后才令世界有所注目。
“以科學幻想為內容的故事片,其基本特點是從今天已知的科學原理和科學成就出發,對未來的世界或遙遠的過去的情景做幻想式的描述”[1]《流浪地球》改編自劉慈欣的同名科幻小說,原著構建了規模恢弘的世界和宇宙格局,時間跨度大,情節復雜,直接按照原著拍攝顯然不合適。電影《流浪地球》巧妙地以原著的構思創意、故事背景等元素為基礎,另辟蹊徑講述了地球流浪之旅中遭遇木星引力危機的故事,影片聚焦于劉啟、劉培強、韓朵朵等主要角色人物,同時大大縮短原著的時間跨度,使得影片邏輯因果更明確,情感線銜接更流暢,這種做法使得觀眾接受度明顯增高,講好了電影故事。
科幻文學和科幻電影彼此密不可分,科幻文學的發展推動科幻電影的發展,科幻電影市場的拓展也會刺激科幻文學的創作。“科幻電影的妙處即在于只要某種科學設想一露頭,它就能虛構出原則上是可能產生的模式世界中的人和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或活躍了人們的想象”[2]。電影《流浪地球》啟發我們,以科幻文學作品作為拓展電影故事的基礎和發掘電影素材的寶庫更為合適,不過電影創作團隊要重組元素、發揮想象、增減修改,創作出符合電影藝術特點和觀眾審美趣味的好故事。
二、電影制作高投入、高水準,營造精良視覺效果
《流浪地球》上映之前,觀眾對影片的視覺呈現效果或許是抱著懷疑態度的。好萊塢之所以能夠做到幾乎壟斷了科幻電影市場,原因是他們形成了成熟完善的科幻電影制作鏈,大量科幻電影制作專利技術保障了影片的視覺效果,好萊塢科幻片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震撼逼真的視覺盛宴代名詞。而國內科幻電影起步較晚,短時間內難以企及好萊塢科幻片的制作水準,長期的心理落差令觀眾對國產科幻電影難免抱有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
事實上中國電影人從未放棄追求,《流浪地球》的成功或許正是意味著中國科幻電影迎來了一個階段性的契機。“當科學觀念、藝術想象和電影手段三者結合時,科幻電影隨之產生”[3]。《流浪地球》制作團隊攻克制作技術難關,發揮開拓創新、精益求精的精神,最終電影呈現出了不遜色于好萊塢大片的視覺效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隨著劉慈欣、郝景芳等科幻文學作家創作出一大批優秀科幻作品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科幻電影市場顯示出了巨大的潛力與商機,吸引巨額商業資本不再是幻想,制作技術難關不再難以突破。
三、思想內核本土化,展現中國精神
《流浪地球》展現出的精神思想與好萊塢災難類科幻片相比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首先,這種差異表現為應對災難的態度和選擇。好萊塢的災難類科幻片中,面臨末日危機時,影片中人類往往采取拋棄式的逃逸方式,如乘坐飛船逃亡外太空等。而在影片《流浪地球》中,同樣是末日之下逃亡奔命,人類卻選擇了“拖家帶口”,帶著整個地球去流浪,體現出了中國人對待家園不拋棄、不放棄的獨特情懷。其次,這種差異表現為拯救行動的設計上。好萊塢偏向于突出塑造“救世主式”的孤膽英雄,如《黑客帝國》中的尼奧、《雷神》中的索爾。而《流浪地球》雖然聚焦于主角一行人的身上,但是無數細節卻顯示出全人類的同心同德,例如對行星發動機進行“飽和式救援”,主角一行人未到達目的地而救援行動依然圓滿完成;空間站上多處休眠艙暴動,除主角劉培強之外,同樣有很多空間站工作者在發覺地球危機時想要逃出休眠艙進入控制艙實施救援;以及最終引爆木星的廣播召回了各國無數人民參與。
《流浪地球》展現出中國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胸懷和精神。電影藝術的功能絕不僅僅為娛樂,其強大且潛移默化的教育教化功能不應被忽視。就好比好萊塢科幻片傳達美國精神,各國觀眾享受好萊塢大片的視覺盛宴時何嘗不是同時接受了一場美國思維和精神的宣揚呢?中國的科幻電影應像《流浪地球》那樣具有中國特色的精神思想內核,如此達成外在表征與內在核心的協調一致,才能做成令國人驕傲、令世界注目的中國科幻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