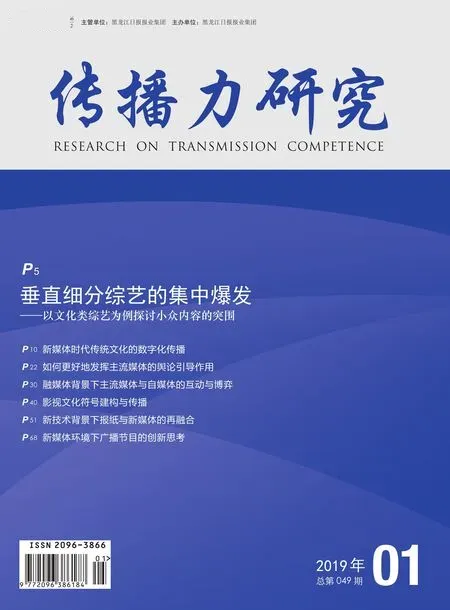森鷗外在《高瀨舟》中的審美構建
陳永岐 東北大學外國語學院
森鷗外(1862—1922),是日本小說家、翻譯家。幼年時代即在私塾學習四書五經等漢文經典,東京大學醫學部畢業后成為軍醫。1884年受陸軍省派遣赴德國留學,留學時接觸到當時最先進的醫學技術和文學、哲學等領域先進知識。1888年回國后擔任軍醫教官,同時活躍于日本文壇,以自己的德國留學體驗為素材創作并發表了《舞姬》等作品以及大量譯作,是日本近代文學的奠基者之一。
《高瀨舟》于大正5年(1916年)1月發表在《中央公論》上。小說取材于江戶后期的一部隨筆集《翁草》中的一篇故事《流放犯人的故事》,解差莊兵衛押送一個被宣判流放的犯人喜助,由京都前往大阪,在高瀨舟上喜助講述自己獲罪的經歷。文體簡潔、典雅。日夏耿之介(1890-1971,日本的詩人、英國文學研究家、評論家)認為《高瀨舟》是森鷗外作品的最高峰,是森鷗外歷史小說中的杰作。
為什么說《高瀨舟》是森鷗外歷史小說中的杰作?筆者認為森鷗外在《高瀨舟》中構建的美,符合了日本讀者的審美情趣。因此,在本稿中筆者以《高瀨舟》文本為主要研究對象,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論述。知足、勤儉之美的構建;兄友弟恭—兄弟情義之美;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之美的構建;自然之美的構建;眼睛描寫之美的構建;呼應、暗示之美的構建。
一、知足、勤儉之美的構建
喜助獨自上船,無人陪伴。雖然允許睡覺,但是他并沒有躺下,默然望月,神情爽朗,眼中閃光,仿佛是乘船游山玩水。對于喜助的反常行為,莊兵衛感到奇怪。不管出于何種原因殺死弟弟,按照人之常情,心中都不會好過。喜助是不是一個十足的惡人或者瘋子?但是他的言談舉止又沒有不合情理之處,莊兵衛百思不得其解。這個疑問是小說展開的原動力。而莊兵衛的作用是與讀者一同解開這個疑問,理解喜助為何行為反常。
根據喜助的描述,他和弟弟居無定所,一旦找到工作,拼命奮斗,盡管如此,總是過著入不敷出的日子。進入大牢,每天不勞而食,流放之前還發放二百文錢,感覺愧對衙門老爺。
莊兵衛從喜助的頭上看到了“豪光”(佛眉間向四外輻射的光芒),欽佩喜助的知足、無欲,如同敬畏神佛一樣。《山椒大夫》(1915年)中也有類似“豪光”的描寫,“今早,安壽臉上因為喜悅而神采飛揚,大大的眼睛,燦若明星”①。
莊兵衛還將自己的家庭與喜助做了比較,妻子出身于富商家庭,有心用丈夫的工資維持生活,但是自幼嬌生慣養,與莊兵衛家勤儉的家風不和,因此,屢屢發生爭吵。通過比較,莊兵衛贊同喜助的想法。莊兵衛對知足、勤儉家風的贊同正是森鷗外的寫照,森鷗外自幼受到武士道德教育,通習中國經典。他的思想正是來源于《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魯斯·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一書中分析了封建社會的武士與農民兩個階級之后,指出“他們的信條是,儉樸是最高的美德”。
二、兄友弟恭—兄弟情義之美
喜助的弟弟因病無藥醫治而臥床不起,每天在家等待喜助買吃的回來。小說之中,關于兄弟的關系,喜助陳述如下:“在我小時,父母染上瘟疫,雙雙亡故,剩下我和弟弟兩人。起初,街坊上的人就像可憐屋檐下的小狗一樣,周濟我們一些吃的,我們則給他們跑跑腿,免去了挨餓受凍,活下來了。漸漸長大后,哪怕去找活干,我們兄弟二人也盡量不分離,總是在一起,相幫著干活。”由此可以看出,喜助作為兄長,時刻關愛著弟弟。弟弟深知自己的疾病無錢醫治,加之生活困難,不想拖累哥哥,在用剃刀刎頸未成功之際,請求哥哥幫助拔出剃刀以結束生命。求生本是人類的本能,喜助弟弟卻毫不猶豫地選擇并面對死亡。喜助弟弟是在充分考慮現實情況之后做出的決定,其選擇是理性的、過程是堅決的,弟弟為了減輕哥哥的負擔慷慨而死。可見社會歷史的現狀令人不勝嘆惋。森鷗外有意識地刻畫這種長幼有序、手足情深,其源流來自中國儒家思想,以及作為長子的自覺。實際上也是對傳統道德觀的一種肯定和妥協。森鷗外的長子意識,在其他作品中也有體現。《山椒大夫》中的安壽為了讓廚子王逃跑自己慷慨赴死。
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之美
喜助父母雙亡,與弟弟相依為命。幸好鄰里照顧,長大成人。弟弟生病失去勞動能力,喜助毫無怨言,一個人支撐起家庭。雖然當時幫弟弟拔出剃刀,“殺”弟弟確實是迫不得己,但從喜助的話語中卻絲毫找不到他對裁決的不滿,甚至對大牢不勞而食,得到二百文錢流放的判決展露出了感激之情。他的欲求是簡單而容易滿足的。更進一步說,喜助對自己的處境自始至終是認同的,沒有絲毫反抗的意識。
通過對莊兵衛心理活動的描寫,可以看出莊兵衛是一個善于觀察、富有同情心的人。他被眼前這個無欲、知足的喜助深深打動。聽完喜助傾訴境遇后,他也曾質疑過權威。“殺人,當然有罪。但是,一想到這是為了不讓人在再受罪,不由得產生疑問,而且始終不得其解”盡管莊兵衛絞盡腦汁思考了很長時間,但最終還是決定將判斷交給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對于喜助的遭遇,莊兵衛確實哀其不幸,最終也無力回天。莊兵衛最終還是服從權威的裁斷。
由此可見,喜助與莊兵衛都是安分守己的人,符合了日本人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審美取向。
四、自然之美的構建
莊兵衛百思不得其解,為什么喜助的眼中會閃著光輝?從喜助以前的困境來看,十分滿足得到的二百文錢。這對于喜助來說是一種自然的狀態。
從人之常情的角度來看,不忍直視弟弟的痛苦,按照弟弟的指示,替弟弟拔出剃刀,使其獲得安樂死,作為一般人來說也是自然的狀態。
從莊兵衛的角度來看,向權威提出疑問(喜助真的有罪嗎?詢問衙門老爺),對于莊兵衛來說,也是一種自然淳樸的心情。
由此可見,森鷗外對于求而不得的自然之人的向往。
二人乘坐高瀨舟,滑過黑色的水面,事如春夢了無痕,正是一種自然的狀態。
《高瀨舟》處于森鷗外歷史小說的最后一部,展示了森鷗外尊重歷史“自然”的態度和追求人類“自然”的態度。
純粹的自然描寫也是十分成功的,例如:“春日黃昏,知恩院的櫻花隨著暮鐘聲紛紛飄零”。“那一夜,傍晚時分,風停了,漫天的纖云,遮得月影朦朧。初夏的溫煦,仿佛化成霧靄,從兩岸與河床的泥土中升騰起來。……周遭一片寂靜,但聞船頭水生欸乃”。“云影忽濃忽淡,月光也時明時暗”。
綜上所述,森鷗外在《高瀨舟》中構建了諸多自然之美。
五、眼睛描寫之美
森鷗外巧妙地描寫了弟弟的眼睛。“弟弟眼神十分可怕,不停地催促著。”我終于想,只好按弟弟說的去辦,我對他說:“沒法子,那就給你拔出來吧”。話音剛落,弟弟的眼神豁然開朗,似乎很高興。
這一部分關于眼睛的描寫,暗示了弟弟含著感激之心而死去。在這里也令人聯想起喜助的眼睛的描寫,在舟中,喜助不睡覺,沉默望月的場面寫到“喜助臉上神情爽朗,眼里閃著微光”。弟弟眼睛的眼神“豁然開朗”與哥哥眼睛的“閃著微光”有著共同之處。
森鷗外是非常善于描寫眼睛的。例如在《舞姬》(1890)之中,描寫太田豐太郎與愛麗絲相遇的場面寫道“她那淚光點點的長睫毛,覆蓋著一雙清澈如水,含愁似問的碧眼。不知怎的,她只這么一瞥,便穿透我的心底,矜持如我也不能不為所動”,愛麗絲的一顧緊緊地抓住了太田豐太郎的心。這段眼睛的描寫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山椒大夫》之中也有對安壽和廚子王的眼睛的描寫。安壽與廚子王二人做了同樣的夢,“……雙眉緊蹙,總是凝眸望著遠方”。還有,勸弟弟與自己一起登山的場面也有眼睛描寫,“蒼白的面龐透出了紅暈,一雙眸子閃閃發亮”。“安壽……大大的眼睛,燦若明星”。這些都表現了安壽放跑弟弟,自己跳水自殺的決心。
六、呼應、暗示之美的構建
押送罪犯從京都去大阪的解差也是形形色色,莊兵衛屬于設身處地替別人悲哀,偷偷跟著難過不形于色的解差。所以押送人犯是一樁令人不快的差事,這與小說最后“惟上面的裁斷是聽,只能服從權威意志”相呼應。
“春日黃昏,知恩院的櫻花隨著暮鐘聲紛紛飄零”與“夜色朦朧”相呼應。小說首尾呼應之美。這是一個美的、余味無窮的結尾。在這里任何的思考、追究、判斷悄然停止。二人沉默不語,乘坐在高瀨舟上滑在朦朧月色下的漆黑的水面上。這是一篇深刻追求人性的文學。如詩歌一般是一部藝術性完美的作品。
“十分稀奇的犯人給押上了高瀨舟”,讀到這里,讀者就會疑問:犯人是怎樣的一個人?與一般的犯人有怎樣的不同?自然而然喚起讀者,吸引讀者的興趣閱讀下文。
“孤零零一個人上的船”,這與解差有權允許一名親屬上船陪到大阪的管理不符。結合下文方知,這里暗示了喜助沒有親屬,只有兄弟二人生活。
森鷗外在小說之中通過這樣的描寫構筑了呼應、暗示之美,而這種寫作手法起到了引人入勝的作用。
七、結語
筆者在本稿中考察了小說《高瀨舟》的文本,結果表明:森鷗外在《高瀨舟》中完成的審美構建,分別是:知足、勤儉之美,對于一般的日本人來說,知足、勤儉是一種美德。兄友弟恭—兄弟情義之美,在日本社會之中自古以來就非常重視家族。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日本人守本分,也就是說,考慮自己處在什么樣的階層位置上,做什么事情要與之相符。自然之美,崇尚自然,尊重自然即是森鷗外也是日本人的追求。眼睛描寫之美與呼應、暗示之美,這兩部分體現的是森鷗外寫作技巧之美。森鷗外在《高瀨舟》中完成的審美構建正符合了日本人的審美情趣,所以這部小說成為經典,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感受到美的滋養。
森鷗外在《高瀨舟緣起》(《心之花》大正五年一月)一文中寫明該作品的情節得益于《翁草》(江戶后期的隨筆集)。其中存在兩個問題:一是財產觀念,盡管人的欲望永無止境。但是,喜助被流放是得到200文錢,喜出望外。二是可否在醫學上實現安樂死。針對前者,羽田莊兵衛對自己生活的反省,可以看作是森鷗外的自省。后者是森鷗外的長女森茉莉身患重病時,實際發生的問題。也就是說森鷗外將自己在生活經歷之中所關心的問題,借用歷史上的人物或事件表現出來。
注釋:
① 本稿中高慧勤譯《舞姬》、艾蓮譯《山椒大夫》、艾蓮譯《高瀨舟》的譯文,引自高慧勤編選.《森鷗外精選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3-18頁、455-476頁、522-5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