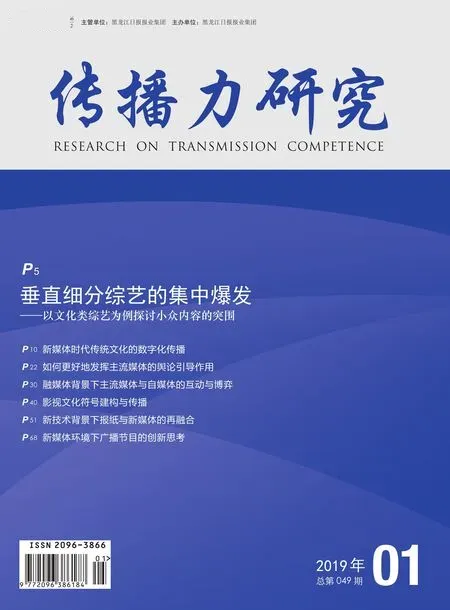新聞報(bào)道中法律誤區(qū)探析
柯麗娜 黑龍江廣播電視臺(tái)都市頻道
近年來,隨著我國依法治國的全面推進(jìn),各領(lǐng)域?qū)Ψ傻闹匾暢潭仍絹碓礁撸瑢?duì)新聞報(bào)導(dǎo)中涉法問題的研究,正是新聞行業(yè)尊重與重視法律的體現(xiàn)。但法律畢竟是一個(gè)專業(yè)的領(lǐng)域,新聞媒體在進(jìn)行涉法報(bào)道時(shí),依然存在一些問題,一方面,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影響新聞報(bào)道的專業(yè)性,更損害法律的尊嚴(yán),且不利于法律的普及;另一方面,媒體由于沒有自身職能錯(cuò)位,會(huì)對(duì)司法審判進(jìn)行干預(yù),使司法獨(dú)立遭到破壞,以至于產(chǎn)生一系列不良的社會(huì)影響;當(dāng)然,在一定程度上,法制新聞也在推動(dòng)著中國法治的進(jìn)步。因?yàn)樾侣剤?bào)道能使被監(jiān)督的對(duì)象產(chǎn)生巨大的社會(huì)和政治壓力,進(jìn)而促使被監(jiān)督對(duì)象改正其錯(cuò)誤,弘揚(yáng)社會(huì)正能量,使我們的社會(huì)朝著更加民主和法治的到路前進(jìn),促進(jìn)社會(huì)的全面進(jìn)步。
一、新聞報(bào)道中的法律用語錯(cuò)誤
新聞從業(yè)者對(duì)于新聞報(bào)導(dǎo)的嚴(yán)謹(jǐn)性一直以來都非常重要,就法制新聞報(bào)導(dǎo)而言,其不僅要求事實(shí)、評(píng)論及標(biāo)題的客觀與準(zhǔn)確,而且要求法律用語的準(zhǔn)確。近幾年,新聞報(bào)道中法律用語錯(cuò)誤有許多,最常見的錯(cuò)誤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首先是主體錯(cuò)誤。新聞報(bào)導(dǎo)中的法律術(shù)語的使用,有時(shí)僅僅差一個(gè)字,就分屬于不同的法律范疇了,并且有著不同的使用主體及意義,絕對(duì)不可替代或錯(cuò)位。比如“被告”與“被告人”這兩個(gè)稱謂,缺乏法律知識(shí)的普通民眾確實(shí)難以區(qū)分,但是新聞媒體在報(bào)道新聞時(shí)應(yīng)該注意其區(qū)別。“被告”是指民事訴訟案件中,原告相對(duì)應(yīng)的當(dāng)事人;而“被告人”只是指刑事訴訟案件中與被害人、公訴人相對(duì)應(yīng)的當(dāng)事人。值得說明的是,在刑事訴訟中,情節(jié)嚴(yán)重的情況下,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可能遭到限制,但是即使如此,在法院的判決書下達(dá)之前,新聞報(bào)導(dǎo)也不能稱其為罪犯,而應(yīng)該稱其為被告人。由此可見新聞從業(yè)者在新聞報(bào)到時(shí)不可僅依據(jù)某些事實(shí)想當(dāng)然地運(yùn)用法律術(shù)語,一定要清楚司法審判的程序,在一定的審判階段運(yùn)用合適的法律術(shù)語,否則則可能貽笑大方了。
其次是自創(chuàng)法律術(shù)語。專門的法律用語有著嚴(yán)格的學(xué)術(shù)上的規(guī)范和法律法規(guī)依據(jù),不可隨意編造。有些媒體在報(bào)道新聞時(shí),自行創(chuàng)造出一些法律用語,例如,劉某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公安機(jī)關(guān)“拘捕”。事實(shí)上,“拘捕”一詞并非規(guī)范的法律術(shù)語,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沒有“拘捕”一說,拘捕是拘留和逮捕的合稱,這是兩種性質(zhì)、效力不同的,對(duì)人身自由進(jìn)行限制的強(qiáng)制措施。“拘留”是公安機(jī)關(guān)在緊急時(shí)刻對(duì)需要受偵查的人依法暫時(shí)對(duì)其人身自由進(jìn)行限制的強(qiáng)制措施;“逮捕”是指經(jīng)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審判,公安機(jī)關(guān)對(duì)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采取的一種限制人身自由強(qiáng)制措施。因此,在新聞報(bào)導(dǎo)中不能使用“拘捕”一詞,而應(yīng)確切地用“拘留”和“逮捕”。自創(chuàng)法律術(shù)語在新聞報(bào)道中較為常見,歸根到底還是新聞從業(yè)者法律素養(yǎng)不夠高,無法在各種新聞事件中自由切換使用法律術(shù)語,根本的解決辦法還是要從思想上重視起來,學(xué)習(xí)法律知識(shí),查閱法律文件或咨詢專業(yè)人士來規(guī)范報(bào)道以避免錯(cuò)誤。
再次是新時(shí)代仍沿用舊的法律。隨著時(shí)代的發(fā)展,法律也在不斷地發(fā)展,舊的法律制度被廢止,新的法律制度確立。但是法律制度與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之間存在不平衡性,新法在具體普及過程中往往會(huì)受舊法的干擾,新聞媒體在進(jìn)行報(bào)道時(shí),沒有及時(shí)更新法律知識(shí),會(huì)導(dǎo)致知識(shí)滯后于時(shí)代發(fā)展的需求。比如,如今許多新聞報(bào)導(dǎo)仍稱“村主任”為“村長”,實(shí)際上這是舊的法律中的稱謂,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農(nóng)村設(shè)置有“村長”這一職位,但八二年憲法廢除了這一稱謂,規(guī)定“村一級(jí)基層組織設(shè)村民委員會(huì),村民委員會(huì),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員若干人組成。”也就是說,從法律意義上我國已經(jīng)沒有“村長”一職,新聞報(bào)導(dǎo)中仍采用“村長”稱謂是嚴(yán)重滯后于時(shí)代的,也與新法不符,應(yīng)當(dāng)予以糾正。
二、新聞報(bào)道中的侵權(quán)現(xiàn)象
新聞媒體在報(bào)道新聞事件時(shí),侵權(quán)情況也時(shí)有發(fā)生。在新聞報(bào)道中,所報(bào)道的事實(shí)是否真實(shí)存在,是分析是否成立新聞侵權(quán)的重要依據(jù)。按照有關(guān)法律法規(guī)對(duì)新聞侵權(quán)方式內(nèi)容的解說或劃分,新聞侵權(quán)行為針對(duì)個(gè)人的主要有三種:侮辱、誹謗、揭露隱私。這方面新聞侵權(quán)可細(xì)分為侵犯名譽(yù)權(quán)、侵犯榮譽(yù)權(quán)、侵犯隱私權(quán)、侵犯姓名權(quán)或名稱權(quán)、侵犯肖像權(quán)等。在新聞“官司”中,最常見的是對(duì)個(gè)人名譽(yù)的侵權(quán)。
如廣西省北海市公安局以涉嫌受賄對(duì)蘇秀全進(jìn)行刑事拘留,經(jīng)調(diào)查后,法院宣告蘇秀全無罪。后《南國早報(bào)》刊登一則題為《北海市挖出八條執(zhí)法蛀蟲》的報(bào)道,涉嫌對(duì)蘇秀全名譽(yù)侵權(quán)。蘇繡全以廣西報(bào)社侵犯其名譽(yù)權(quán)提起訴訟,二審法院認(rèn)為,《南國早報(bào)》在報(bào)道中對(duì)蘇秀全人格進(jìn)行貶損,對(duì)蘇秀全構(gòu)成了侵害,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相應(yīng)的民事責(zé)任。再如李天一(歌唱家李雙江之子)涉嫌輪奸的事件。媒體也以非常多的版面和時(shí)段來進(jìn)行所謂的深度報(bào)道,不僅對(duì)事件的前因后果進(jìn)行挖掘和還原,還捎帶刨根問底李天一的成長經(jīng)歷,而這,明顯是不合適的。《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對(duì)于未成年人犯罪不應(yīng)公開審理且犯罪被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應(yīng)封存犯罪記錄。這些規(guī)定的目的是為了保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的個(gè)人及犯罪信息不被公開傳播對(duì)未成年人的身心造成傷害。
三、新聞報(bào)道中的媒介審判
媒體從業(yè)者對(duì)司法抱著一種比較復(fù)雜的心態(tài),對(duì)監(jiān)督司法的問題存在一個(gè)由模糊到清晰的認(rèn)識(shí)過程。媒體從業(yè)者認(rèn)為走 社會(huì)主義道路的中國,不存在任何不受輿論監(jiān)督的機(jī)構(gòu),司法機(jī)構(gòu)當(dāng)然也不能例外,出于對(duì)民生的關(guān)切和對(duì)司法正義的期待,媒體會(huì)將相當(dāng)大的注意力投向司法領(lǐng)域,通過司法程序無法伸張正義的百姓終于在媒體中找到了正義,媒體從業(yè)者也因此獲得了巨大的成就感。
媒介審判最典型的案件要數(shù)藥家鑫案。此案件經(jīng)媒體報(bào)道后持續(xù)發(fā)酵,引起極大的民憤。藥家鑫被捕后,新民網(wǎng)《西安警方通報(bào)大學(xué)生故意殺人案:嫌犯被捕》這篇文章對(duì)藥家鑫事件的事實(shí)的選擇以及細(xì)節(jié)的描述都比較感性,報(bào)道中有些地方違反了新聞的客觀性原則。新聞客觀性原則要求新聞報(bào)道中事實(shí)必須真實(shí)可靠,因此,在新聞報(bào)道中,除了事實(shí)以外不應(yīng)有報(bào)道者個(gè)人的論點(diǎn)、情感,甚至也要排除價(jià)值判斷。但是在藥家鑫事件的報(bào)道過程中,卻出現(xiàn)了許多主觀色彩濃厚的表達(dá)。有些報(bào)道甚至采用大字標(biāo)題“對(duì)話受害方父親,藥家鑫親屬一句道歉的話都沒有”。記者采訪了被害人張妙的親戚朋友,獲知了藥家鑫親屬?zèng)]有說過一句道歉的話,但是卻沒有同時(shí)去采訪藥家鑫的親屬,確認(rèn)張妙家屬一方的說法是否為事實(shí),便如此表述。在同類的報(bào)道中,幾乎都涉及藥家鑫的家境富裕、父母學(xué)歷高或者可能是官員,導(dǎo)致網(wǎng)絡(luò)媒體及公眾對(duì)藥家鑫的家庭進(jìn)行各種猜測(cè),新聞報(bào)道中的用語激發(fā)了社會(huì)上的“仇富”和“仇官”的心理,在藥家鑫案中,這種心理得到了爆發(fā)。最后,法院判判處藥家鑫死刑,并剝奪政治權(quán)利終身。
關(guān)于此案,法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法院對(duì)藥家鑫的量刑過重,屬“媒介審判”。持此類觀點(diǎn)的學(xué)者包括我國著名的刑法教授張明楷。類似案件還有鄧玉嬌案、蔣艷萍案等。可見,社會(huì)期待與司法公正有時(shí)候并不能統(tǒng)一,新聞媒體自身必須明白司法審判與媒介審判的界限,把握好輿論監(jiān)督的尺度,否則,輿論監(jiān)督一旦越界,就會(huì)變成媒介審判,妨礙司法獨(dú)立,給我國司法體制造成破壞,給當(dāng)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
綜上,涉法新聞的報(bào)道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從認(rèn)知層面上分析,則反映了采編人員關(guān)于法律的知識(shí)儲(chǔ)備不足。因此,新聞采編人員應(yīng)通過學(xué)習(xí)法律知識(shí),查閱法律文件或咨詢專業(yè)人士來規(guī)范報(bào)道,避免出現(xiàn)新聞報(bào)道與法律規(guī)定相背離的情況。因?yàn)樾侣剤?bào)道中出現(xiàn)法律錯(cuò)誤不僅會(huì)影響新聞的專業(yè)性和權(quán)威性,有時(shí)還會(huì)損害新聞當(dāng)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使當(dāng)事人蒙受損失,嚴(yán)重起來甚至?xí)璧K我國的法治進(jìn)程。因此,新聞報(bào)道中的法律問題,新聞從業(yè)者不可不重視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