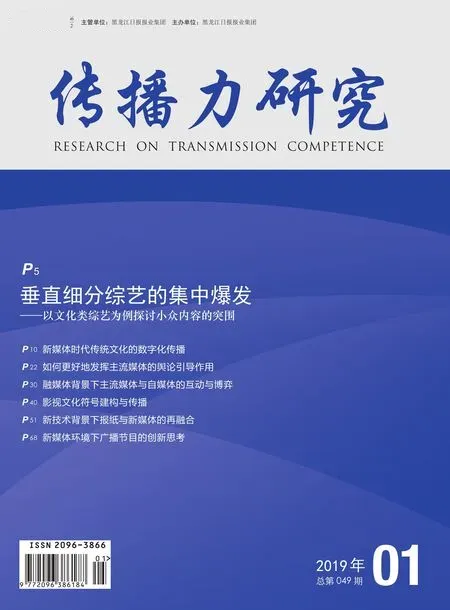媒介環境學視閾下社交媒體研究
黑鈺婕 上海師范大學
近些年,媒介發展日新月異,媒介相關的研究也是風起云涌,媒介環境學則是媒介研究中無法回避的一個重要學派。媒介環境學的理論并不是一家之言,而是三代學者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研究背景、不同媒介發展階段,在泛媒介論這一基礎理論的指導下對媒介進行的研究,因而每位學者對于媒介的研究角度觀點也不盡相同。但是雖然每位學者的研究側重不同,但媒介環境學研究有一個共通之處就在于關注媒介、人與社會三者間的關系,才能最終融匯成以環境的方式考察媒介的視野。本文也想要以媒介發展進程為線索,探析媒介環境學三代學者處在不同媒介時期,對于媒介態度的變遷,旨在對目前處理人與社交媒體、與人工智能的關系有所啟示。
一、大眾傳播技術早期發展下的樂觀與審慎
(一)芒福德:提出人、社會與技術三者關系的研究視角
被譽為技術哲學開山祖師的芒福德(1895—1990年),他對于技術的敏感和濃厚的人文關懷,極大的影響了日后媒介環境學派的發展,因而也被該學派視為先驅和奠基者。
芒福德出生在印刷媒介鼎盛、電子媒介萌芽的年代,出生的那年,“黃色新聞”的泛濫造就了美國第二次大眾報刊的高潮,當時美國的商業報刊多達2250家。芒福德小的時候很喜歡和爺爺在紐約城中散步,見證了紐約地鐵開通,高樓拔地而起,人口結構變化等一系列的發展。可以說芒福德的成長軌跡中不斷有新技術迸發,運輸、建筑、傳播技術都在不斷的更新著他周圍的環境,芒福德伴隨著廣播的發展,一同走進了大眾傳播的時代,這與他在研究中對技術的敏感不無關系。1934年,芒福德在《技術與文明》這本書中,將歷史分為“三個前后相繼,但互相交疊和互相滲透”的階段[2]:以天然環境要素為資源的前技術階段(約公元1000年到1750年)、以煤蒸汽為資源的舊技術階段(1750年之后)和以電力和合金為資源的新技術階段(20世紀發軔)。
有學者評價芒福德對技術的態度是謹慎的樂觀。這是在于他在審視技術時始終以人為出發點,樂觀在于并不抵觸技術向人的需求方向發展,謹慎在于技術的擴張使人成為機器的奴隸,芒福德秉承人與技術平衡的生態觀點,重視人與技術和諧的關系。
(二)伊尼斯:社會需要平衡的媒介生態環境
加拿大學者哈羅德·伊尼斯(1894-1952)被尊為媒介技術論的開創者,他的研究雖然不是細化的,偏向于覆蓋整個歷史時期的概括,但卻是提綱挈領式的。
伊尼斯與芒福德的出生年代所差無幾,一樣經歷了運輸和傳播媒介的大變革。那是印刷媒介的黃金時期,早在1911年,加拿大的就出現了多達143家的日報種數。報刊不是伊尼斯唯一關注的媒介,20世紀30年代,、世界性經濟危機使得加拿大經濟受到沉重打擊,[3]報刊發行量急轉直下,但廣播卻飛速發展,到50年代,幾乎每家每戶都用收音機。
伊尼斯對媒介的研究和觀點,最終匯成了1951年出版的《傳播的偏向》。他關注傳播媒介的形式對傳播內容的影響,指出石頭、莎草紙、羊皮紙、楔形文字、口語是時間偏向的耐久媒介;印刷術促成了空間偏向媒介的形成,這使得伊尼斯最為推崇的口頭傳播的重要性被代替。因為伊尼斯認為,在時間偏向的社會中,原始的口頭傳播可以打破知識壟斷,實現社會民主。
不論他的觀點是否有有失偏頗,他的研究方法都為媒介環境學提供了一種研究范式,伊尼斯對選取具體的媒介進行分析和基于偏向對媒介的分類,形成了對媒介靜態研究中的種和類的研究方向。
二、大眾傳播媒介充分發展后的和諧與深憂
(一)麥克盧漢:找到了人與媒介和諧相處的方式
麥克盧漢作為被國人最為熟知的媒介環境學者,也是這一學派的集大成者。麥克盧漢1943年獲得劍橋大學的文學博士學位,這一年全美的收音機數量已經超過4400萬臺,到1960年,全美電視機數量猛增至4000萬臺,88%的家庭擁有電視機。
麥克盧漢注意到了這一媒介的更迭,1964年出版了《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沿著芒福德的觀點從人出發,主張“泛技術論”和“泛媒介論”,認為一切技術都是人類機體的延伸,基于人對媒介的參與程度,將媒介分為冷媒介和熱媒介。這為媒介環境學研究提供了范式,就是對媒介本體的本質分析和分類分析。
在麥克盧漢做研究的幾十年里,電視媒介一直都處于主流位置,他對媒介的基本判斷是:時代的主導媒介的威力是無法逃避的,最自覺的反制也徒勞一場。麥克盧漢走上神壇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注意到了媒介的影響,并沒有警惕的唱衰歌,而是順應技術的發展,但同時利用電視這一先進的媒介去喚醒人們對電視消極影響的注意,關注媒介發展的規律和對社會文化的影響,這也是媒介環境學重要的研究角度之一。
而麥克盧漢走上神壇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不僅發現了問題,更找到了人與媒介和諧相處的方式,就是喚醒人們的媒介意識,使人們意識到一切都是媒介,媒介是我們身體的外化和延伸,這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媒介而為我所用。
(二)尼爾·波斯曼:深入關注電子媒介對社會文化的影響
尼爾·波斯曼可以說是媒介環境學真正的開山鼻祖,1968年,波斯曼在“英語教師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年會演講中,首次正式提出“媒介環境學”這一術語。這之后的幾年里,有線電視、付費頻道出現,衛星實況轉播體育賽事、HBO(家庭影院)開始流行起來,娛樂節目增加了電視的趣味性。
1979至1985年之間,波斯曼出版了三本媒介環境學派發展過程中的核心著作,勾勒了媒介環境學的輪廓。在第一本《作為保存活動的教學》(1979)中,波斯曼重溫“ecology”這一術語,提到了媒介環境學的一種定義:媒介環境學研究信息環境,它致力于理解傳播技術如何控制信息的形式、數量、速度、分布和流動方向,致力于弄清這樣的信息形貌或偏向又如何影響人們的感知、價值觀和態度。這也是首次厘清了媒介環境學的研究對象、目的和理想,在后兩部核心著作《童年的消逝:家庭生活的社會史》(1982)和《娛樂至死:娛樂時代的公共話語》(1985)中,提出了“媒介即隱喻”的觀點,媒介用隱蔽而強大的暗示來“定義現實世界”,因為它們都有自己的偏向,這種偏向透露出的訊息就會塑造所傳達的文化。
在波斯曼看來,印刷媒介偏向于邏輯、理性、嚴肅的公眾話語形式,印刷時代是“闡釋時代”,而電子媒介則偏向于支離破碎的、脫離語境的、娛樂的話語模式,電子媒介時代被視為“娛樂時代”。盡管波斯曼所處的時代,電視媒介已經在美國大行其道,但是當時電視節目的娛樂化對人的麻痹,以及電子媒介的特點對社會公共話語的解構,使他對電子媒介報以悲觀的態度,賦予印刷文化優先的地位。
三、正在進行時的數字媒介技術
(一)保羅·萊文森:探求數字媒介發展的內在動力
萊文森是媒介環境學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萊文森有幸親臨了數字時代從起步至今的整個過程,他主要考察的正是前輩學者的缺憾——數字傳播,因此他也被稱作數字時代的麥克盧漢。
萊文森可以說是電子媒介的嘗鮮者,持續做了20余年的網絡教育。可能正是由于對數字技術的體驗使萊文森體會到了它的高效與便捷,以及其對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所以萊文森與他的老師波斯曼不同,是一位技術樂觀主義者,對數字媒介的發展始終保有樂觀的態度。
萊文森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三個核心的媒介觀點,在《軟邊緣:信息革命的歷史和未來》(1997年)中強調了人的主動性,人能夠去完善媒介,一切媒介都是能補救過去媒介的不足的“補償性媒介”;在《人類歷程回放——媒介進化論》中提出了媒介進化的“人性化趨勢”,媒介演進三階段是玩具—鏡子—藝術,這與麥克盧漢對媒介發展規律的探究的范式是一脈相承的。萊文森認為,雖然科技技術的發展推動媒介的發展,但其內在動力是人性對媒介的需求。可以看出,萊文森在研究中強調人和人的理性對媒介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前輩學者對技術的倚重,更具有現實人文關懷,畢竟媒介環境學的理想就是探求媒介與人、社會三者的關系。
(二)以社交網絡為代表的媒介技術帶來新的思考
站在時間的長河岸邊不難發現,隨著媒介現實的不斷發展,學者們對媒介的研究也是在邏輯層面不斷深入的。
芒福德率先以謹慎的態度提出新媒介出現后,與人與社會關系的研究視角;伊尼斯雖然對新媒介的到來持懷疑態度,但仍然進一步提出社會文化以及政權穩定的基礎是和諧的媒介生態環境,為社會與媒介的相處找到了方向;而接下來的學者麥克盧漢則是更加主動的意識到,媒介技術發展大潮滾滾而來的不可抗性,客觀的看待新媒介的發展,進一步為人與媒介相處找到了具體的方法就是去理解媒介是人體的延伸;波斯曼則是在更深的層次審視了電子媒介對社會文化和話語的影響;萊文森除了以樂觀的態度順應媒介的發展,更重要的是探求了媒介發展的內在動力,這是對媒介研究深度的再一次突破。
對過去媒介研究的回顧,目的是希望前人對媒介的態度、研究媒介的角度以及處理人與媒介關系的方式能夠對我們研究目前到來的新媒介有所啟示。
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促成了社交媒體飛速的更新迭代,更高位的媒介人工智能、虛擬現實AR的出現都在顛覆著傳統的傳播方式,我們站在這樣的歷史節點上,是應該重新審視現有媒介的屬性。以媒介環境學的泛媒介觀點來看,一切訊息都藏身于媒介之中,也就是說所有媒介都是信息的載體,但是我們立足現實,目前社交媒體的屬性絕不僅限于信息傳遞的功能,以社交媒體為代表的媒介功能和價值正在擴大化。
社交媒體依然承擔信息傳遞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現在我們在講社交媒體時,更多的稱其為社交網絡,突出連結網絡的作用,這就是因為社交媒體開始成為社會關系的締結,成為數字化社會基本的框架脈絡和人際網絡。
在現有的媒介環境學的研究脈絡上畫延長線,可以看出媒介傳遞信息的內涵已經產生了重要的變革,我們要以怎樣的態度看待媒介技術的發展,如何處理人與媒介、技術、社會發展三者間的關系,這都是需要繼續走下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