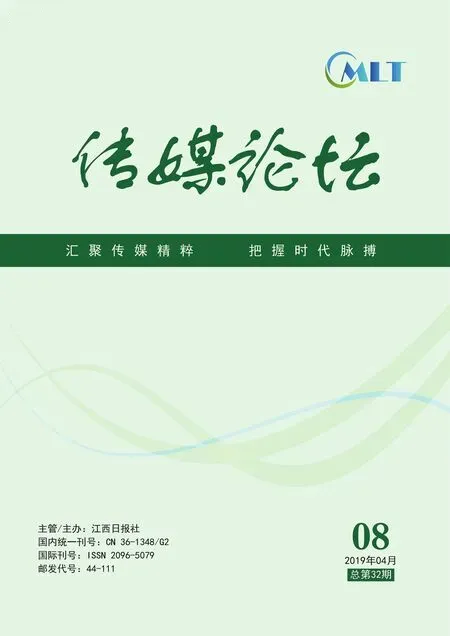從網絡傳播視野看短視頻平臺“抖音”的火爆
胡了然
(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山東 濟南 250000)
“抖音”APP最初是字節跳動公司推出的社交媒體的一種新形態,它采取音樂創意短視頻的形式,針對青年群體,以緊貼移動時代的創意和視聽沖擊力,推動當前依然成為潮流的短視頻更加深入人心,成為普通人記錄美好生活、傳播美好事物的個性化社交平臺和視頻化營銷的主流陣地。當前,“抖音”正在逐漸發展成為匯聚中國年輕一代聲浪的新媒體集散地。
一、“抖音”為何而新,因何而紅
人為什么對“抖音”短視頻如此情有獨鐘?如果說,僅僅只是因為時長十幾秒鐘卻內容豐富的短視頻能夠更有效率地傳遞信息,那么一則表意短小精練的文字或圖片同樣能夠高效地傳達內容。然而,它們并未獲得如同受眾對“抖音”一樣的依賴度,這證明了短視頻平臺“抖音”有著其他傳播方式不可及的特殊之處。
(一)相較于文字、圖片的強感染性音樂視頻傳播形式
相較于單一的圖片和文字,“抖音”等短視頻平臺憑借其節奏鮮明的背景音樂、豐富多樣的情節內容、極大的故事情節不確定性等帶來的趣味體驗、貼近生活的話語模式,能夠提供給受眾更加鮮明、生動的觀感體驗。
(二)相較于傳統網站短視頻的伴隨式、碎片化、交互性的傳播特征
“抖音”并不是短視頻的先行者,早在“抖音”以前,門戶網站、移動客戶端,它們均已成為短視頻傳播制作的載體,但是卻無一達到如同“抖音”一樣火熱的傳播效果。由此可以推斷,在新媒體環境下,“抖音”一定有它適應于新媒體傳播的生存法則。
1.影像“碎片化”與移動智能時代受眾的碎片化媒介使用習慣相契合
早期的視頻網站主要是面向PC終端的,時長沒有特別限制,進入移動時代后,由于傳播時空等因素的影響,網絡視頻生產開始向“短視頻”傾斜。“抖音”將所有視頻的時長一律壓縮到短短15秒,將深入人心的情節進行“碎片化”的“快”剪輯,在此基礎上再通過字幕和特效等二次加工從而形成相較于一般短視頻更具沖擊力的影像內容。
當前,伴隨著手機、平板電腦等移動端的大范圍普及,碎片化成為新媒體受眾普遍存在的閱讀習慣。而“抖音”短視頻將事件最具沖擊力的高潮部分在15秒內就呈獻給受眾,達到在幾秒鐘內就抓住用戶注意力的效果,這完全和當下的媒介用戶碎片化的使用習慣相契合。
2.“趣味搞怪+音樂”與手機移動端伴隨性媒體特征相契合
不少專業媒體將傳統視頻轉化為移動短視頻時,雖然注重時間的壓縮,但是,大量內容敘事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與移動終端所呈現的伴隨性的媒體特征相匹配,或內容過大過空,缺乏生動性;或敘事過于繁復冗長,對受眾注意力的要求較高;或表現過于嚴肅莊重,缺乏趣味性和吸引力。而“抖音”中的短視頻普遍搭配著強感染力的背景音樂以及趣味搞怪、新鮮奇特的故事畫面,內容淺顯易懂且感染力強,這與移動媒體時代移動智能媒體傳播信息的“伴隨性”特征同樣契合。
所謂“伴隨性”即指受眾在與媒介接觸的過程中可以“非專注性”地接收信息,而這里所說的“非專注性”在用戶使用“抖音”的過程中可以從兩個方面體現出來,一層是指受眾可以在從事非專注活動的過程中同時瀏覽“抖音”的視頻內容;另一層是指當下“抖音”用戶所接收的媒介信息其內容本身對受眾的注意力要求極低,受眾瀏覽視頻完全不需要全神貫注,而可以選擇“非關注性”關注,不用花費過多的精力。而正是“抖音”這種可與其他行為相伴或對受眾注意力要求不高的特性是其他廣播電視、門戶網站、移動客戶端短視頻無法比擬的。
(三)相較于一般移動短視頻平臺的大數據算法機制
1.基于“個人偏好”的個性內容的精準推送
最初使用抖音時,系統會隨機向用戶推送視頻內容,在“廣撒網”的過程中,通過受眾選擇的傾向性,后臺就能大致了解受眾的偏好與需求;若用戶在歌舞、Kol內容界面停留時間較長,或是點贊頻率較高,平臺便會不斷地將同類型的視頻內容推送給該用戶,進而該用戶看到的內容大部分是其喜愛的內容,增強用戶的使用體驗。這也就是為什么不同的人看到的抖音也是不一樣的。
在傳播學之中的“使用與滿足”理論指出,受眾是有著特定“需求”的人群,他們的媒介接觸行為是基于特定的動機來“使用”媒介,從而讓自己的特定需求得到“滿足”的過程。具體到“抖音”的“用戶偏好”設置,抖音充分利用“今日頭條”的數據挖掘技術,依據用戶的瀏覽痕跡、點贊情況、個人的基本信息等描繪用戶媒介使用曲線,分析用戶的畫像,并根據用戶自身的需求與特點推送相應的視頻內容。
“抖音”成功地將基于大數據的算法機制與音樂短視頻的信息傳播形式嫁接,憑借其強大的算法和先進的信息捕獲技術,它可以準確地分析用戶的媒體使用習慣和個人喜好。以此作為抖音“個性化”推送的依據,為用戶提供“個性化定制”的合適的內容。
2.基于“用戶體驗”的軟件界面的開發創新
當下,移動化、碎片化、強感染力的短視頻受到年輕一帶的狂熱追捧,PGC+UGC模式的短視頻APP層出不窮,但大多在發展后期由于缺乏創新意識,同質化特征顯現,難以維持用戶黏性而最終曇花一現。而“抖音”則并不完全照搬現有的成功模式,基于對用戶性別、年齡、居住環境、媒介使用習慣、在線時長、點贊情況、瀏覽痕跡等具體數據的調查和分析,按照年輕用戶群體的喜好,為他們量身定做了一款主打受眾是年輕群體的APP,動感、個性、炫酷成為其基本定位和主打調性。
不僅如此,大數據技術在“抖音”背后的應用也有助于他們分析當今年輕人的社會心理,在視頻制作剪輯方面也進行了個性化的處理。“抖音”擁有豐富的視頻特效,用戶可根據自己的需求和喜好隨意使用各種視頻特效,各種視頻特效的加入成功包裝了大量原生視頻,使其內容更加炫酷,迎合了年輕群體的個性化特征。
二、傳播學視野下“抖音”傳播的問題
(一)基于大數據算法機制的個性化推送產生的“信息繭房效應”
桑斯坦在《信息烏托邦》中提出,網絡技術的發達和便捷使得受眾可以在海量的信息中自由選取所需要的信息內容,就像為自己量身定制一份個人日報。這種“個人日報”式的信息選擇行為會導致個體信息繭房的形成。
“抖音”基于大數據技術,隨著時間的推移,根據用戶的基本信息,喜歡,瀏覽痕跡和其他數據信息,將用戶推向個性化的“定制內容”,從而產生興趣固化,視野越來越狹窄等問題,這無疑會加劇“信息繭房效應”的形成。
基于大數據算法機制的用戶偏好個性化推送,這即使“抖音”區別于一般的短視頻APP,在激烈的短視頻平臺競爭中獲得優勢,但這也是加劇用戶信息繭房效應的助推因素,容易使用戶產生審美疲勞、喪失新鮮感、與用戶黏性難以維持等潛在問題。
(二)“碎片化”傳播不利于信息的深度挖掘
“抖音”特有的15秒短視頻傳播模式,順應了新媒體時代人們的媒介使用習慣,同樣也在無形之中加劇了人們碎片化閱讀思考的習慣的養成。
15秒后一段視頻就播放完畢,下一個15秒又是另一個主題信息的發起。在這種信息傳播的情景之下,人們難以對某一事件形成深度的關注,難以形成鏈條性、有深度的思考。雖然“抖音”并不作為嚴肅性新聞信息的傳播平臺,多數情況下它只作為公眾的娛樂工具,但是這種碎片化閱讀、瀏覽的媒介使用習慣一旦養成,也會在人們面對重大新聞事件時產生作用,使得許多深度性新聞信息、系列性綜合報道難以被接收,甚至難以被挖掘。
大數據時代,“抖音”精準定位受眾群體,基于大數據算法機制為用戶精準畫像,極大地提升了用戶的媒介使用體驗,但與此同時,內容傳播的低俗化、信息繭房效應、議程設置擬態環境構建等因傳播方式的改變而產生的問題也隨之而來,這對媒介平臺本身、把關人乃至兼具媒介信息傳播者和接收者身份的用戶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