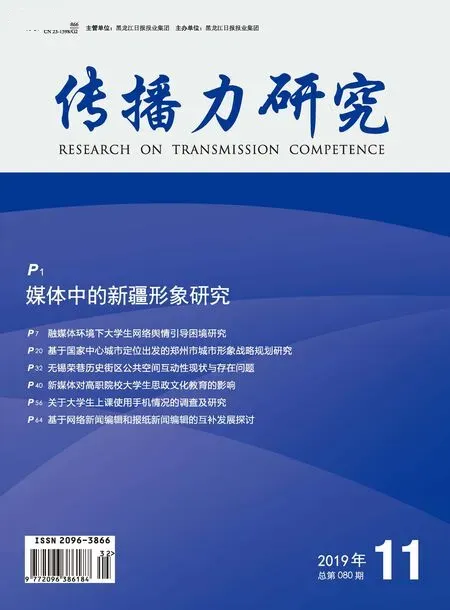短篇小說改編電影的主題改編研究
高羽 中國傳媒大學
一、改編電影概述
作為一門視覺與聽覺共同具備的綜合性現代藝術,電影具有的審美文化樣式是十分獨特的;而文學又擁有著濃厚的文化內涵和跌宕起伏的情節發展,和電影能夠形成一種相互依靠的關系,文學為電影提供豐富多彩的創作源泉,而電影則是深化了文學的內涵,擴大了文學作品的傳播,這就催生了改編電影的出現與發展。改編電影中,小說改編電影是從古至今都常常被采用的形式,而在這之中,短篇小說的語言簡潔干練,情節單一精致,是電影敘事的良好框架基礎,還留給了電影編劇發揮想象力的空間,是改編電影的常見選擇。
二、主題改編的分類
針對短篇小說改編中有關主題內容的改編,早在上世紀安德列·巴贊就提出了將文學改編為電影的三種方式,后來被另一個學者杰·瓦格納歸納總結為移植式、注釋式和近似式三種改編形式。移植式就是指對原著不做任何改動,用鏡頭圖解原著;注釋式是以原著中的某個人物或某條情節為主要線索,剪除其他枝蔓,整合故事結構,稍加修改;近似式則是一種自由式的改編,有的時候甚至連原著中的人物命運都改變了。從移植式到注釋式再到近似式就是改編的程度從小到大的不同,也就是從忠實到變形的過程,但這種忠實也并非文字上的忠實,而是精神上的忠實。
文學是以文字敘述,電影靠畫面敘事,文學先抽象后形象,電影先形象后抽象,兩種表達方式屬于不同的系統,電影改編時就是將文本中具備的適合改編的內容元素通過電影的視聽語言表達出來,將原作中抽象的氛圍、節奏和情感表達出來,從人物形象、故事情節、矛盾沖突等方面來刻畫,更具有直觀性和可視性。本文以1987 版《倩女幽魂》為例,研究短篇小說改編電影中主題改編的應用。
三、小說改編電影的主題改編研究
1987 版的《倩女幽魂》是由徐克導演的一部古裝愛情片,改編自清代蒲松齡《聊齋志異》藝術中的一篇短篇小說《聶小倩》,主要講述了女鬼聶小倩與書生寧采臣起伏的愛情故事,是一部經典之作。原著小說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表達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意蘊深厚,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小說中塑造的主人公聶小倩優美動人、心地善良,是勇敢追愛的象征。在電影中,導演順應了時代要求,試圖在原有情節中彰顯當代人的文化審美觀,在小說原著的基礎上進行了創造性的改編加工,將情節結構有選擇性地進行了刪減,豐富了多線索的具體內容,也塑造了更加真實鮮明的人物形象,表達了任何時代人們心中都有對美好愛情的執著追求,還宣揚了邪不勝正的傳統價值觀,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
(一)主題現代化,增加新元素
電影對短篇小說進行改編時,要結合時代語境,以現代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來進行藝術表現,在尊重原著的基礎上順應時代,增加一些不可少的現代新元素,避免不融于時代的生硬感。電影《倩女幽魂》中就去掉了《聶小倩》原著中那些庸俗落后的內容,比如認為女子為了報恩就要以身相許、女子的唯一價值就是傳宗接代、延續子嗣等封建思想,順應新時代女性地位的變化,更加突出男女主人公之間平等的關系地位,不摻雜其他因素的純粹的相愛,用更加突出的愛情故事來取代舊的“糟粕”。導演徐克將原著小說中的許多人物去掉或弱化,把《倩女幽魂》的故事集中在了聶小倩身上,還把副標題定為《妖魔道》,著重描寫一段人鬼戀情,以喚起人們對美好精神戀愛的向往。
(二)保留原著精髓作為基礎
蒲松齡在寫《聶小倩》這個故事時,除了他固有的浪漫主義的筆觸,奇特詭譎的故事情節以外,還想要通過這個故事來表達邪不勝正的永恒主題。小說一反之前的固有觀念,認為鬼怪和人類一樣,也有是非之辨、善惡之分的,不管這世界上的黑暗勢力多么強大,最終都會被正義力量所取代。
電影很好地將這一個思想精華保留下來,大量刻畫了男女主人公相愛的美好情愫和純真的感情,賦予了“女鬼”這一角色全新的形象特征,給觀眾帶來了不一樣的精神食糧。在這種改編下,電影雖然有對原著中的一些情節段落進行刪減和二次創作,反而加強了原著的內涵。
(三)增加寓教意義
小說通過語言給讀者提供想象空間,而影視作品是依靠聲音和畫面直接的引起觀眾的情感共鳴,影視作品采用全新的美術特技和手法來包裝傳統的聊齋故事,既帶給了人們視覺上的沖擊,又能夠引起大眾思想的共鳴。從普及的意義上看,將文學名著改編為電影,變成一種大眾文化,反而擁有了其他藝術形式無法相比的社會與藝術影響力,觀眾能通過電影更加了解傳統文化,促進民族文化的長遠發展。
四、《倩女幽魂》的細節改編與主題變化
(一)用人物塑造的變化來呼應主題,反映主題
原著中,主人公小倩為了感激寧采臣幫她逃出魔掌,以身相許,為取得寧采臣母親的認可,在寧采臣家中為奴為婢,任勞任怨的操持家務。這是在當時時代背景下塑造的人物形象,隨著社會發展和觀念變遷,電影改編時要將這些壓迫女性地位的封建內容修改掉。于是在電影中,小倩這一人物改編為具有現代女性的心智,不僅是美麗動人,還有捉弄寧采臣時的調皮與活潑、情竇初開時的嬌羞嫵媚,她的人物形象豐滿生動,既有古典風情又有現代人的獨立意識與個性。
另一位主人公寧采臣的形象也一樣被重塑,影片中他的第一次出場,雖穿著破爛、處境狼狽,但仍十分樂觀,勇于助人;雖然膽小懦弱,卻有一股執著與勇氣。這種形象與原著中端正耿直、唯唯諾諾的形象截然不同,為他增添了許多閃光點,又保留了他的一些弱點,這種性格上的些許缺陷和能力上的不足,讓寧采臣這個人物形象更加貼近現實生活,由于他的不完美顯得人物更加真實存在。
(二)情節結構的重新設計,呼應現實
《倩女幽魂》原著中的故事發展是依照時間先后順序,平鋪直敘。而電影則摒棄了依照時間順序的敘事方法,重新設置了懸念,導致了情節的跌宕起伏。導演重新設計了情節和結構,讓故事的發生、發展更自然,情感鋪墊更為到位,還增加了一系列反映社會現實的場景,引發觀眾對社會的思考。
首先,電影與原著極為不同的是增加了許多反映社會現實的場景,比如夏侯惇作為官吏卻因小偷的偷竊行為而輕易的取人性命、十分無情;字畫鋪的老板因為樣貌身份的不同就區別對待、嘲笑他人等等令人發笑又深思的情節。社會的混亂不堪襯托出了人性的丑惡;捕頭燕赤霞決定退隱江湖,也是源于他對社會的失望,這些現實的刻畫是小說中所沒有的,放入電影的情節中既豐富了情節,也是對現實的映射。
同時,與小說相比,電影還很明顯的增加了許多小倩與寧采臣的愛情細節的具體描寫。二人的相識、相知、相戀都通過鏡頭一一表現,寧采臣的心中有對小倩的同情、有相愛的甜蜜,還有對現實的掙扎,這種矛盾復雜的心態升華了二人的感情,通過細節感染了觀眾。原著中并不存在這樣的愛情描寫,而是將二人之間的感情更多地刻畫為報恩之情,并且有大量關于小倩婚后在寧采臣家中辛苦操持的情節,這部分情節的刪去,更好地順應當下的愛情觀與價值觀,是對情節的優秀升華與提煉。
電影通過對小說的改編,將敘事脈絡梳理的更加清晰連貫,情節更加具有戲劇性和沖突性,人物形象飽滿,同時也貫徹了原著中人性與情感的主題,保留了原著的精神內涵,是較為完滿的改編。
五、結語
短篇小說是通過文字語言的美麗給予讀者無限想象的空間,而影視作品則多是依靠聲音和畫面語言直觀形象地引起觀眾的情感共鳴。影視作品采用全新的視聽技術手段和藝術手法來包裝小說故事,既給了觀眾視覺上的體驗與享受,又能夠保留原著精髓,引起大眾思想的共鳴,是傳播文學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弘揚傳統文化、提高大眾素養的重要方式。電影改編短篇小說,要充分遵循這種改編規律與方式,不僅要滿足觀眾的審美想象和娛樂需求,也要傳播小說中有效的文化價值觀,促進改編文化的長遠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