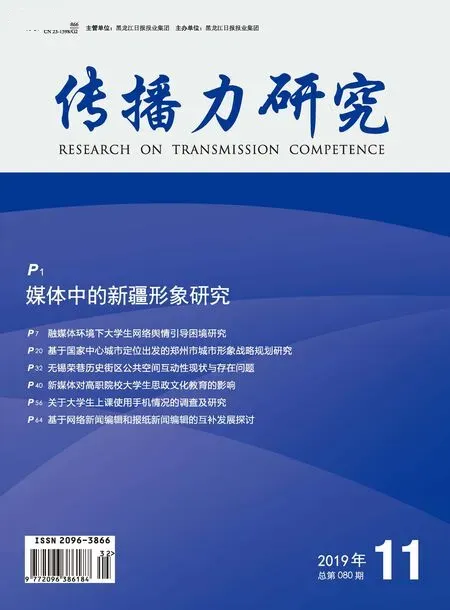“成名”的對面:從公眾的變遷談新聞專業主義
張悅 廣西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成名的想象》指出,在中國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新聞工作的專業主義成為首要議題,這本身就是社會變革的一種標志,它反映了新聞改革面臨新的挑戰,其核心就是新聞工作者如何應對商業盈利、服務公眾利益和政黨宣傳這三者之間的關系。而作為被服務的對象,公眾成為中國新聞專業主義的變遷中無法忽視的因素。
一、公眾身份的變遷
(一)誰在使用媒介
誰在看新聞?我認為這是每個新聞從業者在工作時常常會想到的問題。自己的作品會被什么樣的人看到?從這個問題出發,每個新聞人用事實給出自己猜想的答案。而新聞的受眾也的確在時間的過程中經歷了多次的變遷。
從最初的政論報刊,再到政黨報刊,然后是商業報刊,報刊的變遷史也是服務對象的變遷史。新聞每天都在變,看新聞的人也在改變。新聞是一片園地,無數新聞工作者來來往往,一些人成了名,一些人離開了。在“成名”的對面,是我們對“讀者”這一群體的構想和感知。
人們并非永遠都在追逐新鮮的消息,看新聞的人有一天也會不在關心世界發生了什么。是新聞將互不相干的人群聯系在一起,使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而這個身份會在閱讀新聞的過程中得到確認和強化。
社會的形態經歷了幾番變化,從封建社會到風險社會,人們迫切關心的議題在新聞中得到體現。黨派斗爭伴隨著封建政治制度的瓦解,政黨宣傳預示著新政體的建立,而如今的后現代社會中,公眾關心的議題從政治轉向更為復雜而更為切身相關的話題。食品安全、出行安全、經濟形勢以及教育醫療社保等話題牽引著關注這些問題的人,構成了“成名”的對面——公眾。
(二)公眾地位的變化
潘忠黨指出,早期的著名報人,包括王韜、黃遠生、梁啟超等,多因變法失敗或不事科舉而走上了以辦報參與社會變革的道路。中國近代史上兩次辦報高潮,都和思想啟蒙與政治變革——戊戌維新與辛亥革命——密切相關。這時的報人繼承的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議政傳統,懷有主持公理、指斥時弊的理想。
故而在中國報刊事業的早期,報刊的讀者對象是作為“被啟蒙者”的形象出現的。他們被認為是對社會變革不了解的人,需要被傳授新觀念。傳授啟蒙知識,培養國民素養,是當時報人較多陳述的,如梁啟超表述的“報刊的兩大天職”。伴隨民族危機而出現的早期報刊,致力于將上上下下培養為“國民”,以力圖挽救民族危亡。這時的“名記者”多是關心國家的內政外交,傳遞不同思潮,討論民族命運的文人。
到建國后,新聞成為關注社會焦點、關切民生問題的社會聲音。關注的問題從國家命運轉向社會民生等更為現實的問題,公眾在關心與追問中與記者形成一種不言自喻的合作。公眾向媒體提問,而媒體通過新聞報道等方式回應公眾的關切。這種從“被啟蒙者”到“參與者”的公眾地位變化,賦予了新聞工作者新的使命——關注民生。
而當今媒介技術發展為公眾更廣泛的參與新聞生產提供可能,而“成名”的評價標準似乎也更加復雜多元。影響力、社會價值、媒介形式等諸多因素的考量之下,是“成名”的對面——公眾旨趣的變遷。公眾作為新聞媒介服務的對象,不在甘于坐在臺下傾聽,而是選擇走到臺上,參與新聞的生產與傳播。這種公眾地位的變遷,也改變了“新聞專業主義”的內涵。從傳授內容的把關到公眾的服務性,“專業”本身也在被不斷定義。
(三)隱性的媒介使用者
新聞接觸或主動或被動,但其本質依然是注意力,“讀者”本身即關心的人,對新聞的關注構成了狹義的“公眾”。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中寫道:“斯科特問芝加哥被調查者被調查者,他們每天讀多少版報紙,結果表明71%的芝加哥人認為自己一天的讀報時間是15 分鐘,這其中讀下2-3 版的讀者占67%”。
由此可見,真正每日接觸新聞的人,并非每天花費大量時間閱讀新聞。而關心新聞的人,也并非都是閱讀報刊、收看電視節目的人。新聞的對象,包括但不僅限于它的讀者觀眾。“新聞專業主義”所面對的,是社會絕大多數的公眾。這構成了一組矛盾,即媒介的消費者和媒介的生產對象并不完全吻合。
“成名”暗含了一層寓意,即獲得社會認可,取得一定的社會地位。這意味著取得行業和大多數公眾的認可。這個大多數,并不僅限于“媒介使用者”或是“看報紙的人”。類似世界杯這樣的“媒介事件”的報道,產生出的社會影響已經超越了新聞媒介本身的范疇,將更多的人卷入媒介所關注的事件中。
這種矛盾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新聞從業者在新聞生產的過程中,需要以更廣泛的對象作為“想象讀者”,兼顧經營的同時力求獲得更大的社會效益。這一理念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在新聞教育與培訓中得以傳遞,成為新聞行業默認的“成名”標準,成為“成名”的隱性內涵。
二、公眾需求的變遷
(一)生存與好奇的起源
原始社會我們需要獲取周邊信息,保證狩獵采集,延續族群。而今風險社會之下,我們仍然渴望知曉遙遠的地方發生了什么。即使是今天,我們依然渴望了解我們未能親眼見證但同樣關切的事實。
新聞從業者的成名,背后的原動力即在于對于好奇的滿足,對于生存信息的提供。這種對于最新消息的原始渴望,是“成名”不可或缺的基礎。我們像渴望食物和水一樣,渴望新聞,這促使新聞從業者追問事實。
這一需求從古至今并沒有太多變化,盡管對新聞有用或是無用的爭論不休,但我們仍然樂于在每天早晨看看新的一天有什么新鮮事發生。我們樂于為這樣一種沖動尋找理由,不管是生存還是好奇,對新聞的需求本身并無爭議。“成名”源于對事實的追尋,這一點沒有隨每日更新的新聞消息而改變。
(二)從地緣的接近性到心理的接近性
從過去因調查地方煤礦、醫療、貪污等重大事件而一戰“成名”的記者,到如今“咪蒙”等公眾號成為許多人茶余飯后討論的話題。這也反映了公眾需求從地緣接近性向心理接近性的轉變。一些記者認為過分關注讀者心理需求,一味取悅討好公眾的方式,并不應當成為眾多新聞從業者的導向。
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公眾的選擇權在不斷擴大,那些硬新聞以外的軟新聞,從以前的供不應求到現在的供應泛濫,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成名”的定義。依靠軟新聞“成名”,這種在過去并不被主流新聞行業關注的途徑,在近些年逐漸走入大家的視野。公眾不再僅僅滿足于知道5W+1H,并嘗試自己生產新聞來滿足具有同樣需求的人。
盡管這種強調心理接近性的軟新聞,嚴格來說不夠嚴肅,觀點有時蓋過新聞要素,但我們依然不能否認,“咪蒙”等公眾號的“成名”使得新聞從業者關于“成名的想象”更加豐富。
(三)消遣和娛樂性
中國香港娛記狗仔是出了名的,也有像“甘比”那樣有傳奇命運的。不是沒有人反感這種關心明星私生活比關心自己老媽還厲害的娛樂新聞,但這種消息總是很快就不脛而走,我們甚至很難說清自己到底從哪個渠道先得知的。總之,等我們回過神來的時候,大街小巷似乎已經人盡皆知了。
正如我們渴望知道地震的確切位置一樣,我們同樣渴望與閨中密友聊一聊最近選秀出道的小鮮肉們。很難說哪一個需求永遠重要,這種需求的重要性排序并沒有嚴密的規則,甚至經常隨所處的場景變動。在學術會議中我們聊的新聞和散會后在走廊里閑聊的新聞并不相同,這種場景間的轉換也影響了我們的新聞需求。
但這種“成名”,總還是有一點貶義在其中。用當下流行的詞語來形容,就是“黑紅”——伴隨著爭議的“成名”。娛樂新聞的“成名”仍然停留在是否應該拿來討論的階段。我們默認娛樂新聞不能拿來與硬新聞一同比較,但是事實是我們不拒絕娛樂新聞,甚至有時喜聞樂見。他滿足了公眾的窺私欲,打發了午后的聚會時光,成為一種信息消遣。
三、結語
“成名”的想象中,有新聞從業者對自身的期許,有行政、利益的誘惑,還包含了一種獲得公眾認可的期待。這種期待的對面,是不斷變動的“公眾”。一方面,新聞塑造了它的讀者,另一方面,公眾也在塑造做新聞的人,不僅是行為,也包括了心理。想要怎樣獲得公眾認可?獲得什么樣的公眾認可?他們是否會喜歡?這一切仍然是懸在空中的風箏,高高掛在每個新聞從業者頭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