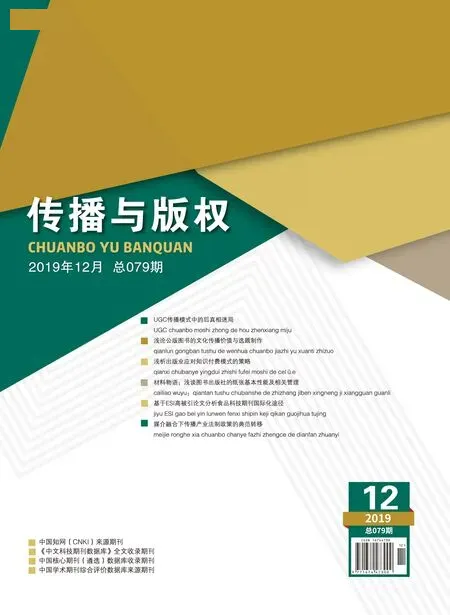政法新媒體的功能、話語與生產研究
伍 欣
(華東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1600)
媒體是法治理念、法律法規等法治信息傳播的重要工具,也是普通民眾了解法治信息的重要平臺。我國擁有數量龐大的政法媒體,它們既是政法機關公布重要文件、發布公告的重要載體,也是民眾與政法機關溝通的重要渠道。傳統媒體時代,法治類報紙和法治電視欄目一直發揮著普法宣傳和溝通民眾的功能,然而隨著新媒體技術和移動終端的迅速發展與普及,政法機關紛紛開通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平臺,形成政法新媒體群體。
本文從新聞業視角出發,探討政法新媒體,分析其興起的背景、功能、話語模式以及生產機制,并探討其發展過程中的不足,進而分析提升其專業性與傳播效果的空間。
一、政法新媒體發展現狀與興起背景
根據2018年初光明網輿情中心發布的《2017年政法系統新媒體應用藍皮書》顯示,截至2017年底,經過官方認證的政法微博累計2.8萬余個,微信公眾號約5600個,頭條號約1.8萬個。[1]作為維護政治安全、社會穩定的前沿力量,近年來,政法系統利用新媒體,秉持專業性,涌現了“中國普法”“最高人民法院”“山東高法”“浙江檢察”“平安北京”等從中央到地方,公、檢、法各條線共同組成的“網紅”新媒體,“政法新媒體矩陣”已然初具規模。其中,“中國普法”微信公眾號2019年5月的文章總閱讀量就達到了1860多萬次,政法新媒體正成為司法信息公開、普法宣傳、政務服務等重要平臺。
政法新媒體蓬勃發展的背后,首先離不開的是新媒體技術與數字化新聞生產對媒體傳播環境的改變。近年來,互聯網尤其是社交網絡的發展,打破了傳統媒體對新聞生產與傳播渠道的壟斷,使得越來越多的新聞行動者加入新聞場域中從事信息生產活動,除了民間大量的個人和企業創辦的自媒體外,這其中還不乏以政法機構為代表的政府、黨委部門獨自創辦的新媒體賬號。政務新媒體已經成為繼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政府網站之后,確立的第三大政務信息公開與新聞輿論發布引導的官方平臺。
其次,隨著法治國家建設的深入,由于依靠傳統媒體普法的效果不佳,而公眾對法律需求卻逐漸增加,公眾發生了從被動接受到主動搜集法律知識的變化,更多的公眾希望能方便地獲取權威的法律信息。同時,政法部門也越來越重視對新媒體的運用,特別是社交媒體在輿論引導與普法宣傳、政府形象宣傳中的應用。在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的《中央宣傳部、司法部關于在公民中開展法治宣傳教育的第七個五年規劃(2016—2020年)》中就明確提出:要充分運用互聯網傳播平臺,加強新媒體、新技術在普法中的運用,推進“互聯網+法治宣傳”行動。開展新媒體普法益民服務,組織新聞網絡開展普法宣傳,更好地運用微信、微博、微電影、客戶端開展普法活動。加強普法網站和普法網絡集群建設,建設法治宣傳教育云平臺,實現法治宣傳教育公共數據資源開放和共享。[2]
此外,官方與民間輿論場的變遷造成原本借助黨管新聞媒體體制、依靠大眾媒體為中心的政治溝通系統出現一定程度上的傳播失靈。傳統媒體在一些重大的法治案件中缺乏輿論引導力,由此促使政府開始依靠新媒體平臺創辦自己直接管轄的發聲平臺,發布權威準確的司法信息引導輿論,重塑政治傳播生態,進而應對網絡輿情生態并回應社會關切。
二、政法新媒體的功能、話語與生產
目前,政法新媒體在功能發揮、話語模式、生產機制上都有相應探索和實踐。首先,政法系統的新媒體平臺突破了傳統媒體以信息為主導的功能,它包括正面宣傳、政務服務和網絡問政等混合功能,實質上成為集多元功能為一體的政務信息服務平臺;其次,政法新媒體的話語方式多樣,糅合了故事模式、信息模式以適應新媒體環境的政治傳播;最后,政法系統利用新媒體平臺采取專業生產與社會化生相結合的信息生產模式,建設屬于政法系統的新媒體矩陣運作體系。具體表現如下:
(一)功能:法治宣傳與司法服務相結合
政法新媒體分別通過法治宣傳、司法服務、政法資訊等多項功能來塑造政法部門形象,以此提升政法部門在社交媒體上的影響力,形成政法部門與民眾之間良性的互動關系。作為法治信息的權威發布官方平臺,政法新媒體在一些熱點案件、司法解釋以及相關指導性文件的發布上具有天然的優勢。政法部門作為信息源,通過新媒體這一平臺能夠在第一時間把這些信息公布于眾,進而促進官方與民間輿論互動。特別是在一些熱點法治案件中,政法機關的權威聲音可以保障公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并起到良好的普法效果,弘揚法治精神。在山東于歡案二審庭審中,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微信“山東高法”持續通過文字、圖片、視頻直播庭審實況,讓關注該事件的社會各界人士能夠第一時間了解到庭審情況,極大地促進了司法公開。據了解,這次直播一直持續到當天23時04分結束,直播時間長達15個小時。該案直播期間,山東高院微博共發布微博134條,微信5條;宣判直播發布微博31條,微信2條。此外,“中國普法”“中央政法委長安劍”“最高人民法院”等中央一級的微信平臺也對其二審結果進行轉發,總閱讀量均超過10萬次,引發廣泛關注。
就司法服務而言,政法系統通過創建政法微博、微信,極大地減少了司法服務的中間環節,同時又能提高辦事效率。如上海市高院的微信平臺“上海法院12368”,它的公眾號頁面設置有“訴訟服務”“智能法寶”“滬法縱覽”三大版塊,從中可以鏈接進入整個上海市法院系統的官方微信平臺,進而可以直接進行法律咨詢、查詢被執行人信息、法律法規開庭公告等。大部分的基層法院微信平臺還開通了微信掃碼自助立案、預約辦理、人工咨詢等便民服務,讓民眾通過新媒體便可以直接與其進行互動,突破了傳統媒體以信息傳播為主導的功能,實際上成為多元功能的政務信息服務平臺。
(二)話語:信息模式與故事模式相結合
從大多數政法新媒體發布的微信文章來看,文章話語模式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雜糅現象,它們既有專業媒體新聞報道的信息模式,同時又糅合了政論模式以及故事模式,這便是當下政法新媒體的話語實踐。根據舒德森歸納的“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兩類新聞來看,故事模式往往強調“新聞的首要任務是為讀者帶來令人滿意的審美體驗,幫助讀者詮釋自己的人生,使其融入所屬的國家、城鎮或階層”;而信息模式則認為“報紙的角色應該被定義為一種獨特的文獻形式,提供的事實不能經過修飾,純粹用于傳達‘信息’”。[3]通過對“上海浦東法院”微信公眾號的文章研究發現,它們糅合了信息模式與情感模式兩種不同的傳播模式。上海浦東法院的新媒體編輯根據法官的審判故事和辦案心得,發布了多篇關于法官審判過程中的故事的文章,如《史一峰:每一個案子都教會我,如何做一名溫暖的法官》《他,男神?克星?》等,通過對法官日常辦案中的故事進行挖掘,生產出了一系列具有新媒體特色宣傳風格的文章,收獲大量粉絲。
觀察現有政法新媒體的新聞實踐,相對于傳統專業媒體而言,它們最大的區別在于不具備采編權,但它們對傳統媒體的報道方式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進。大多數政法新媒體一改以往相對刻板、嚴肅的說教式的宣傳面貌,恰到好處地運用“新媒體”語言,拉近與受眾距離的同時也贏得了受眾,并能夠對輿論場施加影響,進而進行有效的法治宣傳教育。以“中國普法”和“中央政法委長安劍”兩個微信公眾號為例,它們會不定期地綜合整理出全國各地一些有趣的法治案例,沿用傳統以案釋法的方式,但卻使用生動有趣的新媒體語言來進行編輯。如“中央政法委長安劍”在“618購物節”之際整理出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且有趣味性的案例,提醒讀者如何保護自己的權益,防止在購物時被騙,這既達到娛樂大眾的“笑果”,同時又寓“法”于樂,淺入深出地達到普法宣傳作用。
(三)內容生產:專業生產與社會化大生產相結合
政法新媒體擺脫了傳統媒體這個“傳播中介”依賴、能夠更為自主地向公眾直接傳播法治信息,它們作為信息源進行的信息生產也更具權威性,在具體的內容生產上較為專業與嚴謹。為打造功能多元、綜合型的政務服務平臺,政法新媒體往往還會采取新媒體矩陣化、體系化運作,同時采納和引用網民的評論與意見,進行一種社會化生產即把內容生產的工作轉移給廣大受眾。除了功能上的分擔外,政法新媒體在生產機制上還需要多方面的協作。采取這樣的生產機制,是由于政法新媒體缺乏固定或充足的編制,實際運營人員較為不足。以著名的“中央政法委長安劍”為例,它自2016年4月更新以來,累計推送了5000多條內容,原創文章1349篇,然而它背后的編輯團隊卻一直保持4人,主要是“80后”“90后”。[4]除了原創文章以外,他們每天需要時刻關注各級政法新媒體、法律專業媒體以及其他網絡平臺發布的新聞信息,對其直接轉載或者歸納整合進行二次編輯。編輯成員主要來自中央政法委新媒體工作站,他們每半年會從全國公檢法司各單位挑選優秀的新媒體人才,分配到各個新媒體崗位。[5]觀察大部分的政法新媒體,它們在內容生產上,大多數也是采取這種專業生產與社會化生產相結合的形式進行,內容既有來自官方的各級政法部門、法律類的專業媒體,同時也有來自用戶的評論、反饋以及社會自媒體的原創內容等。
三、政法新媒體運營的不足與提升空間
(一)專業性缺失,缺乏專業新媒體人才
在一些熱點案件中,政法新媒體對案件信息的不恰當發布、不妥當轉發評論,甚至“小編”隨意抒情的三言兩語,擅自配發的表情包等,均可觸發受眾敏感的神經,從而引來預想不到的輿情,甚至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如2018年南昌鐵路公安關于在G1420次高鐵上“疑似猥褻女童”事件的情況通報,由于南昌鐵路公安在微博平臺上公布的情況通報中措辭表達不嚴謹,出現“兩人系父女關系,不構成猥褻違法!”的不規范表述,一時引發網絡輿論,激起民憤。事態發展表明,事情的發酵與該公安部門微博平臺發布的情況通報表述不嚴謹、用語明顯不當有很大的關系。因此,政法新媒體運營者既需要具備法律專業知識,又需要具備新聞傳播專業素養,而由于人員數量限制,政法新媒體普遍面臨人才緊缺的窘境。因此,建議在制度上對政法新媒體工作給予保障,制定相關發展規劃,統籌安排人員、經費等。在政法系統內打造一支專業人才隊伍,內部“挖潛”,對新媒體人才進行摸底,發現一批政法專業寫手,加強培訓,使之成為政法網絡新媒體優質內容的提供者。
(二)傳統媒體思維與新媒體環境不合拍,出現“脫節”現象
在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中,提到了慣習與新的場域相遇會出現“不合拍”或“脫節”現象。即“在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歷史局面里,客觀結構中的變化過于迅速,那些還保留著被以往結構形塑成的心智結構的行動者行為,就會表現出落伍現象,他們的所作所為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甚至前后矛盾。”[6]一些負責政法新媒體運營的負責人仍用傳統思維來管理新媒體,忽視其公關、社交和服務功能,往往將新媒體作為自家的宣傳工具,仍然堅持原來的那種“我想宣傳什么就宣傳什么,反之就不宣傳”的落伍思維,如將新媒體當成領導活動的報道平臺、輿情發生時不及時應對等。政法機關的業務本就相對專業,如果再以這種形式發布消息,就會顯得不合時宜,久而久之,很可能導致發布的內容陷入自說自話的尷尬,“引關圈粉”能力隨之下降,甚至可能因此“掉粉”。
(三)缺乏原創內容,內容挖掘不足同質化嚴重
從中央一級的政法新媒體到各省級甚至是再下級政法機關的新媒體都出現了大量內容同質化的問題。盡管這些政法新媒體保持了較高的更新頻次,但大多數政法新媒體發布的內容皆是轉載自其他部門的微信、微博,而原創文章少、內容單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政法部門人力、精力有限,不重視新媒體平臺建設;另一方面是受思維所限,認識不到一些案件的新聞價值,或者仍不愿過多公開;再者,原創內容的采寫需要業務部門配合,靠運營者“一頭熱”解決不了問題。實踐中發現,在一些影響力大的熱點案件開庭、宣判后,一部分政法新媒體只發布簡短通稿,然而根據通稿,網友只能大致了解事件脈絡,大量細節隱藏在辦案、庭審等環節之中。如何結合自身職能,以適當方式將可公開的信息公開,政法機關需借鑒一些經典的案件的發布與宣傳經驗,提前做好準備,設置網絡議題。
在政法新媒體蓬勃發展的今天,各政法機關在運營上仍存在許多不足,政法機關有理由、有責任重視新媒體對法治宣傳、輿論引導的作用,不斷在實踐中總結經驗。牢牢占據輿論引導、思想引領、服務人民的傳播制高點,增強受眾的法律意識,讓法治理念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