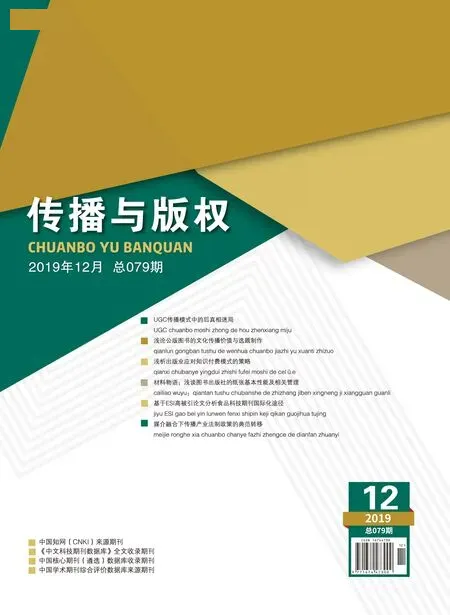數字出版產業鏈背景下學術期刊發展問題探究
趙燕萍,章 誠,劉俊英,林本蘭
[《南京工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編輯部,江蘇 南京 211800]
數字出版產業鏈主要包括內容提供商、技術提供商、網絡服務提供商、終端設備商和讀者等幾個環節[1]。內容提供商為產業鏈提供了各種信息內容主體,一般為出版社、期刊社,是數字出版產業鏈的基礎環節;技術提供商將內容進行加工制作形成數字化后發放到數字平臺,如中國知網、重慶維譜、萬方數據庫等,是數字出版產業鏈的中堅力量。數字出版產業鏈中各個環節緊密協作,共同維持著鏈條的穩定運作,然而由于企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自的利益訴求,或者是某個環節的壯大必然壓縮了其他環節的生長,使得鏈條中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長此以往產業鏈運行不暢,導致該產業中斷與癱瘓。
一、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產業鏈發展現狀
(一)產業鏈分工不明
在當前的媒體融合背景下,技術服務提供商(如知網、萬方等)推動了傳統出版走向數字化,推進了數字出版的進程,是數字出版產業的中流砥柱與中堅力量[2]。然而,在我國技術服務提供商處于絕對強勢主導一方,學術期刊在使用其技術時往往以出賣版權等重要權益為代價,技術服務提供商妄圖憑借其技術優勢從而染指內容的生產,從而達到數字出版產業鏈中的壟斷地位。
目前,技術提供商為了擴大市場開始爭相與學術期刊社簽訂科技論文的網絡出版權協議。特別是開出高利誘惑試圖得到獨家轉讓權。學術期刊社對此則十分糾結,一方面對技術提供商提出的各種高新技術優惠使用政策、采編系統維護使用、免費專題推薦、優先出版等等有利條件,無疑能大幅度地加快資金和軟實力較弱的期刊社的數字化出版進程;另一方面,簽訂了獨家協議后即意味著無法再在其他平臺傳播,這種做法是否會影響期刊的影響因子與學術論文的引用率仍未可知。其次,學術期刊社與技術提供商單方面與簽訂網絡出版協議并未與論文作者簽訂協議,這種做法是否合理合法仍有待商榷。
(二)學術期刊作為內容提供商處于弱勢地位
內容提供商的主體為出版社,在傳統出版業中出版社處于主體優勢地位,國外的大型數據庫平臺一般由大型出版商轉型而來,如Elsevier數據庫等[3]。然而,我國數字出版起步晚,技術提供商首先推進了數字出版發展,因而在我國的數字出版產業鏈中,內容提供商明顯處于劣勢,對信息內容并無實質貢獻的技術提供商憑借其雄厚的資產和技術優勢而占據整個產業鏈上峰,學術期刊出版社作為內容提供者的勞動成果得不到有效保護,其產生優秀信息內容的積極性被減弱。傳統學術期刊出版社在長期運營當中對科技行業的把握與專業知識素養能為學術論文提供專業性的指導,學術期刊出版社能從選題策劃、組稿編稿、欄目策劃、內容取舍等方面為期刊發展提出有效性建議,這是技術提供商遠不能達到的高度。一味地追求技術的發展,勢必會導致數字出版產業鏈追求短期收益,一切向金錢看,而需要時間與耐心的專業性、內容精神文化素養則被整個產業鏈所忽視,導致數字產業鏈看似壯大其實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沒有優質的內容資源信息做支撐的產業鏈并不能走太遠。
二、學術期刊如何在數字出版產業鏈中尋求發展的對策
(一)技術為輔、內容為王
學術期刊由于讀者、作者群體相對單一,傳播也局限在有限的范圍內,因而在數字出版產業鏈中受到了嚴重制約。學術期刊在數字出版產業鏈中扮演著內容生產者的角色,內容質量的好壞直接影響了學術期刊的生存與發展,可以說好的內容是辦好學術期刊的基礎與核心,掌握著數字出版產業鏈的命脈所在,即使有再先進的技術做支撐,離開了好的內容也是無根之木、無水之源,會將整個數字出版產業連根拔起,造成毀滅性的打擊[4]。學術期刊如果能更好地整合內容資源,無疑能迅速地占據數字出版產業鏈的制高點。
因此,學術期刊應該強調自身的優勢,把精力放在內容生產上,以提供優質內容保持期刊的核心競爭力,不要脫離實際盲目建設開發數字出版技術平臺,而應該多借助現階段專業技術水平提升內容質量,確定自身定位與期刊品牌優勢,從而與技術開發者有更多的談判籌碼,達到共生共立合作,共同建設一個健康發展的數字出版平臺。首先,中國的大型技術企業應加大精力投入到數字化技術的基礎建設,建立大型數據庫平臺和兼容性更強的數據文本、統一標準,注重自身企業技術發展,而不是試圖吞并整個產業鏈。同時,在競爭激烈的數字出版時代,傳統學術期刊需要迅速適應各種異軍突起的新媒體形式出版,在嚴謹治學的基礎上不斷尋求風格創新、適應各種新型出版形式與技術平臺相兼容,以生動、有趣、富有特色的辦刊風格吸引該領域更多的讀者與作者,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期刊,與時俱進不斷發展。學術期刊可以通過建設微信公眾號、期刊網站等新媒體形式加強編輯、讀者和作者三者之間的聯系交流,通過信息推送等為用戶提供更專業、定制化的服務,建設更全方位的信息發布與互動服務平臺,從而達到拓展內容資源的目的。學術期刊出版單位還要從內容資源的選題策劃和組稿等方面出發完成內容的數字化出版,做好學術內容質量把關人,學術內容與新媒體相結合,打造品牌期刊,為讀者和作者提供優質的溝通渠道。
(二)加強版權保護
版權是數字出版在經濟流通當中的核心部分,版權在產業鏈流動中起到了串聯各個環節的作用[4]。在數字出版產業鏈中,學術期刊必須高度控制內容版權,只有對內容版權擁有絕對主動權才能在產業鏈中保持優勢。版權作為無形的資產,很容易被學術期刊社忽視,不知道怎樣保護自身版權,同時如何避免侵害作者的版權,這就要求我們期刊工作人員在與數字技術商、網絡運營商等機構合作時一定要注意簽署授權協議,并仔細研究閱讀協議內容,注意雙方的利益分配是否合理、是否存在過度開發共享行為、是否簽署的獨家等,權衡利弊之后再授權傳播;同時,學術期刊一定要注意是否獲得內容的信息網絡出版權,在與作者簽訂版權協議時是否包含了數字出版權。對于學術期刊出版社來說,數字出版權的保護一方面是與萬方、知網、維普等數據庫等簽訂有限制性的數字出版傳播協議,另一方面也要及時與作者進行聯系,得到作者論文的數字出版授權,這樣才能牢牢控制數字出版鏈中內容主體版權。
(三)政府管理部門的合理指導
學術期刊的繁榮發展直接影響我國的科技進步,是關乎國家發展的大事,國家政府管理部門應該在尊重市場化競爭的前提下進行合理指導,優化整體戰略布局,引導數字出版產業鏈健康平穩發展。政府相關管理部門要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對數字產業鏈中的“鯊魚企業”進行管控,防止個別企業擾亂行業發展秩序、壟斷行業發展,從而保護產業發展生態平衡[5]。完善法律、法規等措施加強數字出版產業建設,對數字出版版權保護、標準等等出臺指導性文件,加快基礎設施和數字出版服務平臺建設。
學術期刊雖然處于產業鏈的上端,然而經濟實力較弱,政府應該通過政策優惠、資金撥款等方式加大對學術期刊的扶持,對技術服務商可以采用“連橫合縱”策略,對外可以將國內各大技術提供商的聯系,整合資源,建立共享數據出版平臺,與國外大型數字出版商抗衡;對內則可以按信息內容進行細分,如按學科分類進行數據平臺劃分,做到對整個數字出版產業鏈利益進行合理調控分配,從源頭保證產業鏈。
(四)創建新型學術期刊協會
數字出版鏈不僅需要政府職能部門的監督管理,同樣需要引進社會力量對行業進行自我監管,學術期刊可以參照歐美國家創辦的協會的經驗維護自身的利益。
第一,可以嘗試分學科、分地域組建多個學術期刊協會,將學術期刊聚集起來,定期開展交流會,不斷完善協會的職能與作用。所謂“行有行規”,期刊協會應該在合理、可推廣、可操作性原則下出臺一些行業準則供期刊會員遵守,保證行業秩序和期刊穩定健康運行。學術期刊協會應該增強自身權威性和合法性,協會可以嘗試與政府職能部門多聯系交流,做好期刊與政府的溝通人角色,向政府挑明期刊發展現狀與需要的扶持,為期刊謀求發展空間、財力、物力、人力支持。
第二,期刊協會可以起到團結大家統一戰線保護行業利益的作用,例如知網為了搶占期刊數據庫大市場,積極與各大科技期刊聯系獲得其獨家數字出版權,此時期刊協會就應該向其會員分析其中的利害關系,團結一致慎簽獨家。單家期刊與數據庫、網絡運營商等談判是占下峰的,然而協會作為無數期刊的代表與數據商等談條件無疑是有利的,協會可以從中協商得到一個雙方更為滿意、公平、公正的結果。對于嚴重侵害期刊利益的數據庫,協會甚至可以組織會員統一退庫,共同維護期刊利益。
(五)專業數字化編輯人才隊伍發展
期刊出版社在數字化出版進程中需要一支專業化的具有數字出版思維的編輯團隊作為支撐,時刻緊跟數字發展潮流,對期刊內容進行數字化創新,加強數字平臺的運營管理,更好地服務現代化需求的讀者。
小中型學術期刊社一般由四五個編輯組成,編輯待遇不高,留不住高端人才是現在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數字化出版編輯人才不僅要掌握傳統出版知識,同時還要能綜合運用新媒體技術,加強對復合型編輯人才的培養。期刊編輯的工作將不僅是筆案工作更應該對期刊內容進行多渠道、多樣化加工創新。媒體融合環境下的期刊編輯人員開始關注如何更好地經營期刊公眾號、期刊網站等,綜合運用聲音、視頻等形式多角度展示學術論文,新穎、多樣化、個性化的新媒體期刊更受讀者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