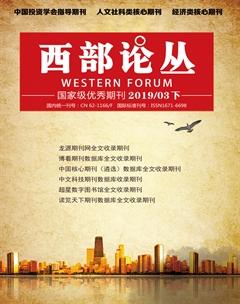淺談中國(guó)畫(huà)的“空寂”之境
摘 要:意境,是中國(guó)美學(xué)的重要審美范疇,是藝術(shù)家創(chuàng)作追求的最高層次。它是“超以象外”的無(wú)限境界,是主客觀的相互統(tǒng)一。 “空寂”美學(xué)植根于中國(guó)古代哲學(xué)思想與宗教精神,而“空寂”之境,更是中國(guó)古代文人畫(huà)普遍的藝術(shù)審美的一部分,是他們藝術(shù)精神的重要組成。本文圍繞“空寂”之境的主題思想,從感悟“空寂”之境帶給我的心靈體驗(yàn)和藝術(shù)啟發(fā)。其一,文人畫(huà)“空寂”之境的精神追求。其二,文人畫(huà)“空寂”之境的營(yíng)造。
關(guān)鍵詞:意境 空寂 文人畫(huà)
“意境”一說(shuō),最早出現(xiàn)在唐代詩(shī)歌審美欣賞與評(píng)品上,唐代詩(shī)人王昌齡的一部詩(shī)論雜著《詩(shī)格》中提到:詩(shī)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其中意境三:亦張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則得其真矣。意境強(qiáng)調(diào)發(fā)揮想象和聯(lián)想的作用,以心觀物,將心與物的界限打破,向內(nèi)尋求精神的深化與自由,主張個(gè)人生活經(jīng)驗(yàn)與情感自然流露。以情入境,得其真諦,從而進(jìn)入藝術(shù)審美的最高階段,力求營(yíng)造出令人有所共鳴,感動(dòng)人心的藝術(shù)境界。
這“意境”是空靈、飛動(dòng)、而含蓄雋永的。進(jìn)入精神世界的“境”,已經(jīng)超越了本身“界限”的含義,從有限轉(zhuǎn)化為了無(wú)限的“空”。“意境”與“意象”相互聯(lián)系,它們都以“意”為核心,都認(rèn)知于廣闊無(wú)際的真實(shí)本心。它又超脫于介在實(shí)與虛中間的“意象”,完全納入精神性的范疇。美學(xué)家宗白華先生認(rèn)為意境是“鳶飛魚(yú)躍,活潑玲瓏,淵然而深的靈境。”
文人畫(huà)的形成與發(fā)展作為歷史必然的文化現(xiàn)象,經(jīng)歷時(shí)間的推動(dòng)不斷完善和成熟。佛教傳入中國(guó),在唐朝時(shí)期逐漸興盛,與中國(guó)傳統(tǒng)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中國(guó)本土文化下的禪宗,至此三教合流,改變了之前以儒,道思想為主流的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文人畫(huà)家受到儒、禪、道思想的深刻影響。文人畫(huà)家將自然展示于人,通過(guò)山水花鳥(niǎo),四君子或木石等抒發(fā)個(gè)人包袱與追求,表達(dá)隱逸之思,高潔之格,或憤世嫉俗之感。生活上,他們淡泊,孤獨(dú),內(nèi)心追求精神的自由和虛靜。筆墨上講究意趣,道法自然,注重人格修養(yǎng),畫(huà)面上注重象外之意和意境的營(yíng)造。“空寂”一詞,主要源于佛教,謂指佛法境界或佛教語(yǔ)。在禪宗里也指“禪境”。隨著在佛、道、儒思想融合的演變下,它也呼應(yīng)與融合了儒道的思想精神內(nèi)涵,“空寂”之美成為了中國(guó)古典藝術(shù)審美范疇的重要部分,它是文人筆下所追求的言外之意,更成為了一些文人畫(huà)家所追求的畫(huà)外之境。這一切的演變,都使得“空寂之境”具有了象外之象的虛幻性、無(wú)限性,同時(shí)也具有了個(gè)人情感精神世界的獨(dú)立性。
“空”是“虛空”,是老、莊所謂“道”,虛空不是一無(wú)所有,而是宇宙之上,萬(wàn)物之源泉”,是文人畫(huà)家游心所在的太虛之境。
“空”是空靈,是文人畫(huà)筆下的妙境。文人畫(huà)家把詩(shī)書(shū)畫(huà)結(jié)合,融萬(wàn)境于墨法中,造就妙境。文人畫(huà)意境是空靈的,物我渾融的。抽象的筆墨虛靈如夢(mèng)。筆下畫(huà)境猶如宇宙,空曠而高遠(yuǎn)。文人畫(huà)里的山川花鳥(niǎo)是寫(xiě)實(shí)的,但又是空靈的,是心靈于自然的合而為一。
“空”又是無(wú)限,是文人畫(huà)家在有限中表現(xiàn)出無(wú)限境界,是剎那中蘊(yùn)涵的永恒。在無(wú)限中又回到有限的局部和生命里,循環(huán)往復(fù)。如倪云林的山水,平淡疏遠(yuǎn),簡(jiǎn)之又簡(jiǎn),卻簡(jiǎn)中寓繁。一花一葉都蘊(yùn)意著無(wú)邊的宇宙。
“寂”是靜寂,宗白華先生所謂:“中國(guó)繪畫(huà)里所表現(xiàn)的最深心靈究竟是什么?答曰,它既不是以世界為有限的圓滿(mǎn)的現(xiàn)實(shí)而崇拜模仿,也不是向一無(wú)盡的世界作無(wú)盡的追求,煩悶苦惱,彷徨不安。它所表現(xiàn)的精神是一種深沉靜默地與這無(wú)限的自然,無(wú)限的太空渾然融化,體合為一。”
“寂”是孤獨(dú),是文人心靈的獨(dú)處。是“空山不見(jiàn)人,但聞人語(yǔ)響”的寂寞。如畫(huà)家詩(shī)人獨(dú)自游歷山水間,忘卻世事繁雜,靜觀寂照,物我兩忘,俯仰山川,心靈與大自然相融合,在一丘一壑中感悟生命,才能回返內(nèi)心,使“凡畫(huà)山水,最要山水性情。得其性情……自然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1],獲得源源涌現(xiàn)的藝術(shù)靈感。
“寂”也是禪境,是“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shí)”的超然境界。禪境,不是棄置生活上的情趣,而是超越五欲六塵,得到更真實(shí)的和諧與寂靜,是從現(xiàn)世生活感悟道無(wú)處不在,若能頓悟即得解脫。以禪心觀照萬(wàn)物時(shí),縱使一沙一石,一風(fēng)聲一鳥(niǎo)語(yǔ)一花影,都充滿(mǎn)無(wú)限機(jī)趣。在“剎那的頓悟里領(lǐng)悟世間色相變化微妙至深的禪境。這一禪境是在審美主客體的交融升華中達(dá)到的最高審美境界。
文人畫(huà)家所追求意境之美,在于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識(shí),秉持淡泊,空靜的心境。追求精神上的獨(dú)立與自由,游歷山川,歸隱自然。基于“外師造化”,尊重自然,又在自然之中融入自我的生命情調(diào),創(chuàng)造獨(dú)特的意象,呈現(xiàn)無(wú)不往復(fù)的空間,注重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在有限里體悟到無(wú)限,即是所辟之獨(dú)境。
文人畫(huà)家順應(yīng)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看待這自然造化,是仰觀俯察萬(wàn)物生命時(shí)空,感悟大道無(wú)常。沈括提出“以大觀小之法,其間折高、折遠(yuǎn),自有妙理,豈在掀屋角也 ”,雖然其主要針對(duì)山水畫(huà)的創(chuàng)作而言,但我認(rèn)為“以大觀小”法具有更普遍的美學(xué)意義,對(duì)觀照萬(wàn)物生靈皆應(yīng)如此。“以大觀小”是要求畫(huà)家用“心”游觀自然,或俯或仰,或遠(yuǎn)或近,或前或后,或目極千里,應(yīng)目會(huì)心,加之想象的創(chuàng)造力,達(dá)到“眉額頰輔,若晏笑兮;孤巖郁秀,若吐云兮。橫變縱化,故動(dòng)生焉,前矩后方而靈出焉。”的意境,即畫(huà)人物,可著其神姿,畫(huà)山水,著其氣韻生動(dòng)。則以此法感悟到的空間,是隨著時(shí)間而變化,是萬(wàn)物在寂靜中生長(zhǎng)衰敗的自然之全貌,是游心太虛而得氣韻橫生,鳶飛魚(yú)躍的空寂之境。
文人畫(huà)的精神世界,教會(huì)我在之后的學(xué)習(xí)和繪畫(huà)道路中,可以萬(wàn)般皆從容,不被世俗浮華利欲而蒙蔽初心。也希望更多的人在藝術(shù)道路上,能夠更多的學(xué)習(xí)到傳統(tǒng)文化精神的精髓,更多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下去。
注 釋
[1] 明代唐志契:《繪亨微言·山水性情》
作者簡(jiǎn)介:李冰(1986—),女,漢族,山東濰坊人,碩士研究生在讀,現(xiàn)在就讀于首都師范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現(xiàn)代油畫(huà)專(zhuān)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