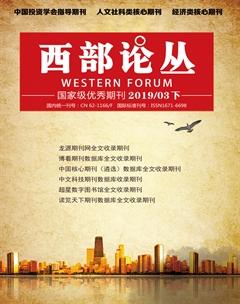淮安地區古琴音樂流變考
摘 要:古琴文化歷史悠久,在中國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以淮安地區古琴音樂文化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對該地區古琴音樂發展史的梳理,從而探究淮安古琴藝術在不同時期的傳承情況及歷史價值,以期對淮安地區古琴音樂文化的發展有更加深入的認識。
關鍵詞:淮安地區 古琴藝術 琴派考辨
古琴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所謂“士無故不撤琴瑟”,古琴既是中國古代文人修身養性、抒發心緒的一種形式,也是中華民族精神及傳統音樂文化的重要載體。地處江蘇的淮安是一座人杰地靈、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此地琴人博采眾長,潛心向學,且融合其它琴派之長,形成了自身獨特的藝術風格,其所具有的學術研究價值不言而喻。本文通過對淮安古琴發展史的梳理,探尋該地古琴音樂的傳承脈絡及歷史淵源。
一、淮安地區古琴師承考辨
古城淮安歷史悠久,人才輩出,諸多古琴名家誕生于此。淮安地區古琴音樂獨具風格,與廣陵琴派、金陵琴派等流派聯系緊密,代表琴人有喬子衡、楊子鏞、夏一峰、凌其陣等人,他們都在中國古琴音樂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為古琴藝術在近現代的傳承與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淮安地區古琴藝術的第一代傳承人可追溯至琴家喬子衡之母。琴家凌其陣在其《淮陽琴派》一文中寫道:“……始見喬氏所傳原譜。其譜中用‘退吟、‘退猱等指法,節奏曲折,頗類中州琴操。”[1]由此可見喬母的琴風或許與中州一帶有著一定的關聯,進而也對淮安地區之后的琴風發展與傳承有著一定的影響。清同治、光緒年間的淮安琴家喬子衡與弟喬子安年少時師從母親學習古琴,為淮安地區古琴藝術的第二代傳承人。其中以喬子衡的影響更為深遠,凌其陣《淮陽琴派》一文較為詳細的記載了喬子衡教琴的過程:“學琴之家在學琴前先備茗點款待,然后學琴。琴課完畢,以學費和所剩糕點,盡數交其所侍琴弟子攜歸……”[2]喬子衡對待學生認真悉心,培養了諸多優秀的琴人,其中的杰出代表有許老太、楊子鏞和釋空塵等。其中許老太語焉不詳,釋空塵一般視為廣陵琴派琴家,故淮安地區古琴第三代傳人以楊子鏞為代表。他較為完整的繼承了喬氏一脈的琴風,且吸取眾家之長,融入自身豐富的情感體會,加之富有創新性的技巧,演奏極具表現力。楊子鏞擅彈《大學之道》、《秋塞吟》、《平沙落雁》等,為淮安地區古琴藝術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力量。楊子鏞所傳第四代中有夏一峰、凌其陣及葉名珮等。《淮陽琴派》一文中記載:“夏一峰所傳琴操,已由楊蔭瀏先生記譜,刊入《古琴曲匯編》第一集中,其中《良宵引》、《平沙落雁》、《漁樵問答》為喬家原譜本。夏一峰所彈《良宵引》的節奏得自喬子衡的另一女弟子許(徐)老太太,與其他琴譜中《良宵引》的節奏迥然不同。”[3]由此可見夏一峰與喬氏一脈的師承脈絡及其對喬氏琴風保留之完整。凌其陣先生回憶楊子鏞老師曾說道:“今日夏一峰彈琴的功夫較我為深”[4],由此看來也不無道理。夏一峰所教學生有四十余人,然而受當時的環境影響及其它種種原因,幾乎沒有能夠繼承喬氏原有琴風的人,可以說“夏一峰是淮陽派最后的琴人”。[5]
淮安地區四代傳人師承脈絡清晰,其中諸如喬子衡、楊子鏞、夏一峰等琴人對淮安地區古琴藝術的發展影響深遠,更在中國古琴發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激勵著后世淮安琴人們不斷進取,傳承著他們博采眾長、勇于創新的精神品格。
二、淮安地區古琴流派考辨
關于淮安地區古琴的流派之說一直以來都是眾說紛紜的,目前主要有“淮陽琴派”及“淮安琴派”這兩種名稱。“淮陽琴派”一說可見凌其陣《淮陽琴派》一文,文章首句寫道:“淮陽琴派之說,未見諸書。一九三二年,余在上海侍淮安老琴家楊子鏞起鵬先生琴席時,始聞其說。”[6]然而并無相關例證能夠說明“淮陽琴派”這一名稱的由來。嚴曉星的文章《此是喬家正始音——“淮陽琴派”史料再考察》是關于淮安地區“淮陽琴派”相關史料的探究,對喬氏一脈及其傳人進行梳理。嚴曉星在其文中借用了凌其陣《淮陽琴派》一文的成說,故而也沿用了“淮陽琴派”一說。且文中對甘濤《淮安琴派夏一峰》一文的標題提出異議,認為甘濤直接將“淮陽琴派”改成“淮安琴派”是稍欠嚴謹的。另有葉占鰲、張國昌的《淮安琴派淺考》一文,文中認為“淮陽”是因口述誤傳而導致以訛傳訛,實則應是“淮安琴派”。
筆者認為淮安地區的古琴流派之說仍有待考證。首先,一個琴派的產生必然有其清晰明確的師承關系。縱觀淮安地區的古琴發展歷程,唯有喬氏一脈及其傳人的四代師承關系,且其第一代傳人喬子衡之母師承何人我們不得而知,且至夏一峰之后便再無其他清晰的師承脈絡,或者可以說夏一峰之后的琴人已經另具琴風,并沒有繼承喬氏一脈的風貌。其次,傳譜也是一個琴派應具備的要素之一。喬氏一脈及其傳人都未有傳譜,只有劉鶚所輯《十一弦館琴譜》流傳于世,且不論劉鶚本身是否屬于淮安地區某個琴派,就琴譜本身而言所收錄的曲目也并不具有代表性。也許淮安地區歷史上的“琴派”可以視為揚州廣陵琴派的一個分支,又或許的確是自成一派,這依然是有待考證的,但不可否認的是以喬子衡、楊子鏞、夏一峰、凌其陣等人為代表的淮安琴人對該地區古琴藝術的發展做出的突出貢獻,其歷史價值不言而喻。
三、結語
如今,通過淮安琴人們的不懈努力,淮安地區古琴藝術的發展不斷壯大。淮安琴人李家祥師承廣陵,他延續了山陽琴派與廣陵琴派的歷史淵源,創辦了山陽琴社,并成立淮安市古琴學會,開設諸多古琴相關的文化藝術活動,如公益講座、雅集、古琴藝術進校園等,各地琴友慕名而來,交流學習,使古琴藝術成為淮安優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古琴音樂文化本身就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精華及積淀,它不應在歷史的潮流中被埋沒。對淮安古琴音樂文化的研究,意義不僅體現在音樂文化方面,更重要的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弘揚,它理應被更多的當代琴家與學者傳承發揚下去。
注釋
[1][2][3][6] 凌其陣.學琴札記(二則) [J].音樂生活.1984(11):25.
[4] 甘濤.淮安琴派夏一峰[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版),1990(03):52.
[5] 嚴曉星.此是喬家正始音——“淮陽琴派”史料再考察[A].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11):178.
作者簡介:張思琦,溫州大學音樂學院2015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