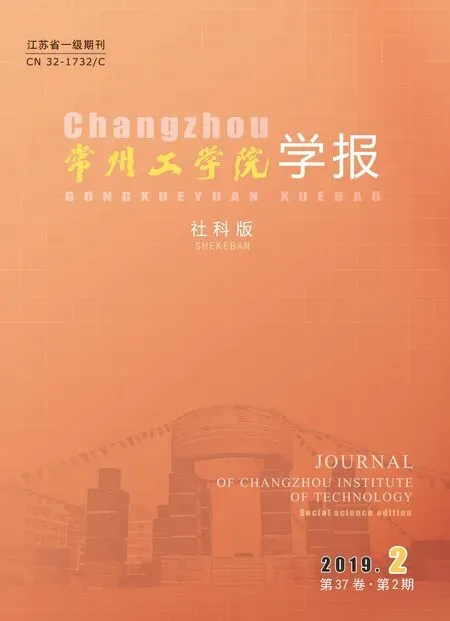《悲情城市》與《海角七號》敘事比較分析
張浩宇,張霽月
(河南大學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一、 多重轉換的敘事時空
“熱奈特在敘事學領域提出任何敘事都建立兩種時間性:被講述事件的時間和講述行為本身的時間性。”此外,“大部分敘事需要產生接納事件的空間環境,電影敘事的基本單元——畫面,就是一種完美的空間能指,表現引發敘事的行動和與其相配合的背景”[1]104。影片《悲情城市》與《海角七號》采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敘事手法,將個人經驗與歷史經驗相結合,引發了不同時期觀眾的共鳴。
(一)非線性敘事時空
在影片敘事中,《悲情城市》并非采用傳統連貫的線性敘事,而是大量使用景深鏡頭與空鏡頭等緩慢節奏的敘事手法,反復使用相同場景,在時間和空間中發掘更深層次的內涵。故事展開敘述的場景較為單一,如小酒館、家、醫院、漁港,主要為室內景,通過人物的行動揭示其在歷史長河中的悲劇命運。廖慶松采用氣韻剪接法,“剪畫面跟畫面底下的情緒,暗流綿密,貫穿到完”[2]。兩個畫面中插入一段空鏡頭,不僅具有空間能指的意義,而且使整部影片有機地連結起來,充滿敘事張力。因此空鏡頭的設置,在承接轉場的同時為故事設置懸念,使缺憾的空間具體可感,成為情緒延宕的補充。下文以幾個空鏡頭為例,進行非線性敘事時空的分析。
忽明忽暗的燈光下氣氛陰暗,臺灣動蕩的局勢下人心惶惶。影片透過窗簾內產婆的虛像,讓人觀測女人生孩子的動態,隨后林文雄的兒子出世,取名“林光明”。導演通過鏡像觀察事物的方式,“類似法國麥茨說的‘電影之愛’:觀眾接受并看著來自現實世界的影像銘刻在銀幕上,而產生內在愉悅”[3]。與此同時,字幕交代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臺灣將脫離殖民者的統治進入后殖民時期,但新生命出世的喜悅,仍無法改變悲痛事件的繼續發生。畫面進而轉向一片靜默、美麗的漁港,空曠的場景展示“二二八”事件爆發前九份的平靜狀態,有起承轉合與設置懸念的效果。接下來的畫面是,林家“小上海”酒館開業,一家人沉浸在熱鬧的氛圍中。銜接鏡頭依然是美麗的漁港,伴隨著《流亡三部曲》的歌聲,長達38秒的空鏡頭,承載著年輕一代臺灣人對祖國強烈的歸屬感,思念的情緒與赤子之心寄托于美麗的大好河山中。畫面與聲音分屬于不同區域,有聲的抗日音樂與文清、寬美通過字條無聲的交談,構成影片內部的敘事張力。鏡頭自上而下搖移俯視漁港,雨聲與雷聲銜接下一個鏡頭,寬美在收拾醫院的床單,文良被綁在病床上,眼神呆滯,殘酷的戰爭剝奪了一位有志之士應有的尊嚴。畫面視點進行了虛化處理,營造出深焦效果,借助漁港、天空等轉場景物與富有情緒表現性的雷聲、雨聲交代敘事時空位置,呈現有層次的時間與空間的對比關系。小酒館內的歌聲與窗外雷聲延展到醫院,構建另一個空間,暗示時間的更替。緊接著黑幫勢力找上門來,文雄開始了顛沛流離的跑路生活,由林家客廳里女人們的談話轉場到文雄臥室,文雄倉忙逃跑后僅留下妻子和兒子。天空稀松的云朵將電線桿拉向遠方,而近處房屋處于黑暗面,隱喻女人必須要堅韌地撐起半邊天,完成家庭的重任,渴求未來的光明來代替眼前的黑暗。陳儀廣播的同期聲承接薄霧籠罩的山間,一只雄鷹在畫面邊框處盤旋,直至消失在山野中,隱喻人物在自然與歷史中渺小的地位,老大林文雄是動蕩的臺灣黑暗勢力的犧牲品。文清和寬美婚禮的嗩吶聲延續到白天,綠色的山野間時空的變化,暗示葬禮到婚禮的轉折,空鏡頭代替時空流轉,由悲轉喜預示了臺灣的未來終將是光明的。最后一幕是車站月臺的空間場景,來往的列車不斷卻不知何處是真正的歸程,無論文清與寬美何去何從,始終也無法擺脫個人在歷史進程中無法決定自己命運的無奈。整部影片以空鏡頭串聯故事的邏輯性節奏,以非線性敘事結構表現敘事時空的同時,表現了臺灣新電影畫面詩意性的內涵意蘊。
(二)雙重交叉的時空套層
“虛構”與“現實”為二元對立的概念,后新電影的去中心化賦予了臺灣地景兩種不同方向的表達。影片《海角七號》中,過去友子的故事與現在的友子在虛幻空間與現實性空間交替出現在同一畫面中。除了現實生活中阿嘉與友子背離現代都市的空間外,另一種則是60年前由于歷史造成的日本先生與學生友子分離的回憶空間。作為影片重要敘事線索的7封信,出現在阿嘉與友子兩人感情發展的每個重要節點,將兩代人的愛情跨時空穿插在一起。
“太陽已經完全沒入了海面,我真的已經完全看不見臺灣島了。”日本先生作為敘事者以旁白的形式念出7封信,以日本戰敗遣返回鄉為敘事背景,信中流露出遺憾、傷感等情緒,激發觀眾興趣的同時引出現代青年人的感情,告誡人們要懂得珍惜。阿嘉在受到挫折時機緣巧合讀到這封信,畫面中閃現年輕友子的臉龐,時空交織以平行蒙太奇的手法連結起阿嘉和友子,使二者建立關系。日本先生乘船返鄉與學生友子從此訣別,與此同時阿嘉受挫離開都市臺北返鄉,同樣的離別,前者表現了日本先生與愛人分離的無可奈何,后者表現了阿嘉只能與夢想告別繼續流浪。臺灣人與日本人早在20世紀已有的情感糾葛,交錯在現代時空中呈現發展,人物身份、處境也因此發生轉變。阿嘉和友子第一次擦肩而過是在在地樂團甄選會上,看似不和諧的樂隊組成,在7封信的穿插中,與信件獨白者情感的波瀾轉折形成情緒共鳴。“友子,預計明天入夜前我們即將登陸,但愿這彩虹的兩端,足以跨過海洋,連接我和你。”演唱會前夕的友子在陽光下看到了彩虹,阿嘉在送信的路上,踏著彩虹而來。銀幕上呈現的現實世界與信件中構建的虛構世界的關系變化,如同鏡像般相互對立呈現,又彼此嵌套。再者,當日本教師訴說因思念而日漸蒼老的容顏時,鏡頭交錯呈現友子若有所思地走在海灘邊、郵差茂伯補送信件及阿嘉在海岸邊的畫面。“友子,我已經平安著陸,我會假裝你忘了我,假裝你我的過往,像候鳥一般從記憶中遷徙。”最后一封信,將他與友子的情感置于絕望的極端,正如同他將思念與懺悔化作7封情書,穿越60年的時空,依然無法送到信件中早已不存在的舊地址。究竟年邁的友子小姐是否讀到這些信件,年輕的友子與阿嘉最終是否走到一起?“兩個異質時空的段落相互切換,亦散發著一種過去未完、有待未來加以延續、承接并深化的意思。”[4]
7封信的套層空間將不同時空的故事交織剪輯在一起,日本先生與他的學生友子曾經真摯美好的感情因歷史而斷裂,只留下純粹的回憶。阿嘉追逐音樂夢想以及與友子的愛情,借助旁白的方式,貫穿整個故事,相互照應與融合。雙重敘事的時空套層結構,鄉村與都市的對立,傳統與現代的融合,經過片段式的拼貼,描繪出臺灣本土文化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產生的焦慮現象,展現多元化語境下臺灣的真實面貌。
二、個人經驗折射集體經驗
在侯孝賢的電影中,臺灣的日式風格建筑被視為一個暫時性的過渡空間,通過不同角度的固定鏡頭,揭露了后殖民時期種種殖民殘余的痕跡,以及戰后國民黨統治的戒嚴背景。“按照我們制定的體系,‘視覺聚焦’表示攝影機所展現的與被認作是人物所看見之間的關系。”[1]175影片中的人物關系在這個具有文化意味的空間中呈現出來,透過家庭成員日常生活中的行動,以寫實鏡頭聚焦多重敘事視點,充滿后殖民時代的隱喻色彩。
(一)女性視角與旁白
《悲情城市》延續臺灣新浪潮電影的美學風格,以人物關系折射出個人經驗背后的歷史建構,表達臺灣本土身份認同的困境,追溯臺灣的歷史悲情。侯孝賢導演置身于“二二八”背景之下,呈現女性視角的多重敘事,以寬美的內聚焦視角和旁白為主,推動故事的時間軸敘事進程。
“旁白聲音既是敘述的傳達者和執行者,也是一種獨立的存在,音色、質感、語氣、腔調、節奏都暗示講述者的‘聽覺性格’。”[5]寬美的旁白是故事的直接敘述者,天皇和陳儀廣播中產生的歷史重大事件敘事乃是間接敘事,寬美與二嫂女性話語的講述則呈現出循環往復的齒輪式歷史時間,呼應空鏡頭中自然生命的不息與重生。整部影片由寬美的日記構成,通過與文清的交談勾勒出歷史背景下林家小酒館里人物的生活,以日記為線索,將主人公的重擔設置在一位聾啞人——社會的弱勢群體身上。同時用字幕、旁白、廣播、音樂等敘事形式,以宏觀視角觀照歷史背景。片中寬美的日記是幫助觀眾了解敘事發展的關鍵,醫院場景的出現頻率僅次于小酒館,醫院是寬美工作的地點,通過寬美交代敘事情節。寬美在給阿雪的信中,提到新生的希望——阿謙在健康茁壯地成長,當初想要逃避到如今心態平和,再提到文清又一次被抓,生死未卜,以及面對未知的情況已然可以坦然面對,結局是導演將個人情懷轉化為置于高點的宏觀性觀看與審視。影片最后設置了在林家客廳,林父與林家老三文良在正廳餐桌吃飯的場景,一個是日漸衰微的父權,一個是喪失正常人理智處于半瘋癲狀態的老三,在門框后一直忙碌的母親與客廳中來回穿梭的孩子成為家庭的支柱與希望。寬美在信中提到要寬榮照顧好身體不便的文清,另外阿雪在寫給寬美的信中,怒斥上天不公,連聾啞人都不放過,畫面切入寬美堅定的旁白“天理有無我不管”,帶出對文清的個人關懷以及對命運的吶喊。
多層次的聲音片段,顛覆官方的獨白式史詩敘述,細致描繪出從日本殖民轉移到國民黨統治的過渡時期臺灣的真實生活。作為兩次重要的旁白,天皇宣告日本撤離的字幕和陳儀的廣播,帶動敘事的發展。由于廣播電臺信號頻率的緣故,天皇的聲音微弱嘈雜,侯孝賢采用字幕的方式表述歷史背景,也借此處理方式暗示日本的殖民勢力在臺灣已無話語權。第二個是廣播中陳儀的講話,以富有方言味道的“國語”講述如何處置事變,以及宣布戒嚴。與天皇宣告日本撤離的聲音微弱嘈雜相同的是,陳儀的廣播同樣頻率不穩定,通訊受到干擾,國民黨執政雖有些水土不服,卻依然成為事實。不同的是,陳儀的廣播有固定的聽眾,醫生與護士圍繞在桌子前,不管是否深入思想,儀式感是存在的,即使在做毫無意義的宣告。《悲情城市》中寬美的日記是片段式的、去政治化聲音的一部分,廣播和字幕則通過另一種旁白形式,講述個人成長經驗并折射出歷史集體記憶。
(二)內聚焦視角敘事
熱奈特指出:“內聚焦敘事是指有固定的內聚焦,敘事說明的時間仿佛是經過唯一一個人物知覺的過濾。”[1]177《海角七號》以阿嘉的視角為線索,展現現代年輕人的愛情觀和人生觀。阿嘉作為主要敘述人物,以其與行為人之間的互動,呈現臺灣本體內部的多元文化差異與民族認同感。影片中“國語”“臺語”與交雜的日語充斥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本土音樂、建筑、美食等文化生活均為最真實的寫照。影片打破以往臺灣電影以本省與外省矛盾為主的話語體系,探尋多民族并存、文化碰撞的復雜社會中人們身份認同出現的困境與焦慮。
影片開頭,阿嘉騎著機車穿梭在城市與鄉間,飛馳而過的臺灣代表性建筑逐漸遠去,鏡頭通過阿嘉的個人視野展示繁華、物欲橫流的都市生活,機車后視鏡中反射出的都市場景與即將通往的鄉村田野逆向而行。阿嘉的行動構建出飲食男女的生存場域,也構成影片前后敘事空間的對比,通過對比凸顯導演對臺灣人生存主題的思考和觀照。年輕人逐夢的理想屢遇現實的打擊,都市似乎是鄉村年輕一輩不可企及的存在,信件、內心獨白、海邊思考的靜態鏡頭都以阿嘉內在的本我敘述主角的內心世界,使人物個性更加飽滿。同時,作為講述者,內聚焦敘事與外在的他者敘述相結合,使觀眾了解到位于鄉村的臺灣在地人的日常生活與欲望訴求:“國寶級”月琴彈奏者茂伯曾經的至高榮譽與現在被人遺忘淪為郵遞員的生存困境;原住民交警對離世愛人的思念;憨厚的修理工人水蛙對已有家室的老板娘不敢開口的暗戀;辛勤奮斗的創業者納拉桑終于收獲人生的幸福以及天籟孩童大大代表祖國的希望等。敘事視角的不斷轉換,使觀眾在融入故事的同時,又能作為一名全知全能者,以客觀冷靜的距離審視整個事件與行為本身。影片以阿嘉的視角為基點,眾分支線帶動主線的發展,同時為主線鋪墊,融入觀眾未知的世界,使觀眾感受導演所傳達的意涵。
三、本土敘事書寫人物身份
(一)本省人與外省人話語表達
《悲情城市》以外省人和本地人為主,穿插其間的多重話語,既展現了臺灣由日本統治時期到新臺灣過渡身份建構的復雜困境,又呈現出日本殖民勢力的消長與接受大陸新文化所要克服的陌生感與疏離感。
在政權交替的過渡階段,臺灣人在夾縫中生存,一邊是日本殖民政府文化的深入滲透,一邊是對大陸新政府的接納,處境艱難又充斥著矛盾。是使用本土方言“臺語”,還是標準普通話,又或是早已成為日常語言的日語?語言上的沖突在文清于車廂險些被捕的場景中達到高潮。文清被火車上一批手持棍棒的本省人圍住,質疑其身份,這些人第一遍用閩南語質問,得到文清結結巴巴的“臺語”“我是臺灣郎”后,第二遍又用日語重復提問,得不到正宗的日語回答后欲施以暴力,幸得本省人寬榮解圍。將此場景置于歷史場域中,“二二八”時期,會講“臺語”的人不算是正宗臺灣人,兼會“臺語”、日語兩種語言,方可成為合格的臺灣人。不僅隱喻國族認同往往還伴隨著外界勢力的介入,也常常伴隨著創傷經驗,地道的本土特質在歷史繁衍過程中淪為尷尬且不被認同的身份特質。
其中一場關于談判的戲中,在印刷日本假鈔票的事情敗露之后,黑幫紅猴被殺害,兩派黑幫反目成仇,請來本地頗受尊敬的阿姐主持公道。她提出三分制解決辦法,兩邊幫派一份,紅猴年邁的老母一份,簡潔明快地解決雙方的爭端,具有權威的主導性作用。另外一場關于談判的戲中,老大林文雄為文良早日出獄尋求上海幫派的幫助,林文雄講“臺語”,手下翻譯為廣東話再轉述為上海話,談判語言的多元化從而形成多元化的人物身份。由于雙方在語言表達上存在障礙無法溝通,本是一衣帶水的男人力量群體代表,有話語權卻無法得以完善表達,談判效果大打折扣,只得以借助外物的形式——罪惡的毒品使對方明了。另外,小酒館的餐桌上,同樣出現因語言文化差異帶來的矛盾沖突。在場人物有臺灣本地人、上海人,兩組人馬談論走私生意,當本地人欲要說著一口閩南語的酒女來招待外省人時,上海人情緒激動且氣憤,臺灣人立即招呼酒女回自己身邊。然而在聽京劇時,這位上海佬又如癡如醉。為響應政府號召,醫院聘請知識分子講授“國語”,曾經以日語為母語的臺灣人正接受母系文化的輸入,從另一層面也反映出以醫院的醫生護士為代表的工薪階層,對國民黨執政的接受。影片中知識分子在寬榮家的抱怨,法院的院長、工作人員都由國民黨的親屬要員組成,“法院是你家開的嗎?”一句話點出國民黨妄圖一手遮天的資本家本質。脫離了殖民身份后依然面對不自由、沒有話語權的社會,政權的罪惡帶來知識分子對前途迷茫的擔憂。
(二)多元身份的建構
相對于《悲情城市》小酒館里圓桌吃飯的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沖突,《海角七號》則展現出社會族群的多元文化身份,日本人、臺灣在地人、原住民、外省人等,來自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群像,其身份、族群、年齡、背景與職業都具有能指與所指的意涵,充分體現出導演的精心安排。
海灘演唱會中臺灣本土音樂,阿嘉創作的流行歌曲,日本傳唱度極高的民謠,通過混雜的語境,再現了臺灣多族群的日常生活。倒車鏡里出現的高大建筑物,從鏡像中隱喻城市與鄉村的背道而馳,影片中幾位掙扎于人生苦海的年輕人:本是模特卻淪為模特經理人的友子、離開霹靂小組的警察勞馬、修摩托車的水蛙、努力的“小米酒”推銷員馬拉桑等,將在恒春小鎮完成遙不可及的人生夢想。從《悲情城市》到《海角七號》人物身份多元化,情懷不同,激烈的身份沖突轉化為具有包容性的日常敘事,由二元對抗呈現為多元對抗。極具象征力的恒春在地樂團是匯聚融合多元身份的包容性場域。中孝介以曾經的殖民者身份加入演唱會,與臺灣在地人組成的樂團形成友好的平等關系,海灘演唱會不再以日本歌手為中心,本土身份得到認可且被接受程度大于知名日本歌手。作為他者介入的中孝介,以化解族群間積怨已久的矛盾、達到和解為任務,促進了臺灣本土自我身份的覺醒。阿嘉與友子的感情出現破裂時,故事安排村民的一場婚禮,作為消解矛盾的催化劑,通過喜結連理的婚姻,達到緩解氣氛并融解矛盾的作用。愛情的碰撞,樂團友情的身份,人性的溫暖,促使看起來并不合群和擁有不同背景與身份的一群人,凝聚成團結的集體。他們熱愛音樂,勇敢追求,為了同一個目標絕不輕言放棄,以實際行動詮釋臺灣精神,完成對臺灣身份的嘉獎。
四、結語
首先,相對于侯孝賢《悲情城市》非線性的敘事表述,《海角七號》嘗試了不同的美學實踐,融合多元素的剪切手法,創造雙重敘事的時空套層。其次,《悲情城市》借助旁白,通過女性視角反映歷史現實,魏德圣導演則通過阿嘉的視角,觀照多元文化的碰撞與融合。最后,敘事場景的選擇在建構與觀眾之間或親密或疏離的關系的同時,也體現出多元文化身份的焦慮與尷尬處境。總而言之,相較于新電影的單一敘事,后新電影使用更為豐富的敘事手法,展現都市與鄉村的二元對立,新電影則更致力于本土化空間敘事。魏德圣導演作為后新電影導演的代表之一,在敘事手法上與以侯孝賢為代表的新電影導演產生一定的繼承與背離,在肯定新電影寫實主義敘事風格的基礎上,將眼光投向多元族群與社會的不同階層,開辟了后新電影的敘事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