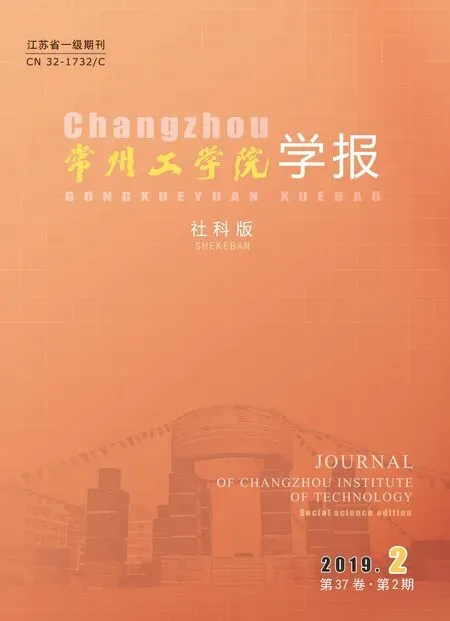“曇花一現”
——再讀張悅然短篇小說《家》
張瓊方,羅關德
(集美大學文學院,福建 廈門 361021)
被媒體以代際命名的“80后”作家憑借“在青春里寫青春”進入大眾視野,彼時的他們不僅處在以年齡為標準截取的青春區間內,也以“青春”的情感、心理狀態去感受個人的狹小天地。刻意夸大的青春書寫,使他們在這種重復的“憂傷”中消耗了自身的元氣。當青春的光芒褪去,“80后”作家已步入而立之年,青春的囈語與私密的情感向他們作別,同時他們也以主動的姿態企圖脫離“青春寫作”的桎梏。張悅然卻始終堅守著文學的陣地,不斷以新的文本進入大眾的視野,企圖揮別“昔日的云彩”,求得嶄新的突破。2016年,原載于《收獲》的長篇小說《繭》出版,這被視為張悅然暌違數年帶來的重量級作品,自然受到諸多評論家的關注。例如小說題材轉向歷史在楊慶祥眼里就不失為一種可喜的變化,然而,“題材的轉變未必意味著成熟,將創作視野轉向歷史的縱深,未必就會自動給作品加分”[1]。同時,楊有楠提出,張悅然告別“青春寫作”的起點可以追溯至2006年出版的《誓鳥》。但是,“《誓鳥》的歷史敘事表現出諸多不足,其最明顯的問題在于盡管作者力圖為故事營造一個宏闊的氣象,但具象歷史場面描寫的缺乏,以及主要敘述空間的狹小都在很大程度上銷蝕了作者的主觀愿望”[2]。那么,讓我們將目光聚焦于2010年其短篇舊作《家》,以后經典敘事學的角度重新觀照,會發現它不是簡單的故事陳述,更不是“青春”的訴說,而是攜帶有多重意旨的文本,可視為張悅然諸多作品中盛開的“曇花”。
一、“曇花”初綻——《家》與小資產階級一代的困境
《家》是關于裘落、井宇以及保姆小菊的故事,兩位主人公在同一天各自逃離了共同的家,小菊則以新主人的身份占據了這個空間。張悅然將筆下的主人公設定為小資產階級一代的年輕人,自然也是“80后”一代的生存寫照,她利用獨特的空間敘事企圖向同時代人提出問題:小資產階級一代人面對生存壓抑下不滿的現狀該走向何方?
20世紀60年代末,受結構主義思潮的影響,敘事學作為一門學科在法國正式誕生。結構主義敘事學在強調作品的內在性和獨立性的同時,也不同程度切斷了作品與社會、歷史、文化語境的關聯。于是,20世紀90年代,后經典敘事學應運而生,其不僅更為關注讀者以及社會歷史、文化語境的作用,也拓展了敘事學研究的領域,注重敘事現象的跨學科、跨媒介研究。而敘事學研究在這種開放的語境下也開始了空間維度的轉向,繼而誕生了空間敘事學。《家》便包含了多種空間,蘊藏著有關小資產階級一代的無窮意味。
在小說上半部中,通過裘落的視角,故事外敘述者為我們描述了“家”的內部結構以及牽涉到的頗具現代品質的生活方式。客廳里的音箱以及電動窗簾、浴室的風筒等等陳設都是大空間“家”中的小空間,主人公恣意地享受音樂,品嘗咖啡與面包,收取當日的報紙,洋溢著濃郁的小資產階級情調。進而,敘述者又為我們描述了裘落臨行前的行程,也涉及了諸多空間:10點來到超級市場,12點到干洗店取衣服,12點半離開餐廳前往寵物商店,下午1點來到咖啡館,下午3點半離開咖啡館前往洗車店與加油站,最后回到家。這就是裘落一天的“空間”的變換,“空間場景的意義不僅在于它作為小說情節結構要素之必不可少,而且其本身往往也具有特殊的意味”[3]。大城市已經“程式化”“機械化”的生活節奏將個人時間一點一點打碎,時間似乎失效——它的存在不過是為了證明空間無限制地膨脹,城市之子們于時間割裂之下在這種膨脹中匍匐前進。敘述者冷靜的語調以及輾轉的“空間”強化了裘落對“物化”生活的厭倦。而男主人公井宇也同樣于現狀不滿,生活的疲憊、消極之感步步侵蝕著他,抵達心臟。“這個早晨,他的動作格外緩慢,已經過了平時出門的時間,卻還坐在桌邊看報紙,手中的咖啡只喝了一半。”[4]169-170井宇拼盡全力如同被鞭子抽著的陀螺一般,而升職后卻失去了旋轉的動力,小資產階級一代在物質上不斷豐富滿足的同時也不免留下一聲聲沉重的嘆息。
小說不僅通過空間的鋪排來展現小資產階級一代人的生存狀態,還將兩個空間并置進行敘事,深刻反映了裘落與井宇面臨的兩難局面。在西方的地理學、語言學、修辭學中,“場所”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它并非是一個純粹的地方,而是容納各種事件發生的一種特殊的空間。空間不僅僅是可觸摸的實體,其中還彌漫著各種社會關系、權力運作、人的思想觀念等形而上的意識形態的內容。井宇上司老霍的別墅就成為一種特殊的空間,不同的人物輪番上演,顯示出心底的虛榮與偽飾。這座擁有私人花園的歐式洋房,一屋子歷史悠久的古董家具,精美得像油畫一般的水果以及閃閃發光的器皿無一不沖擊著裘落脆弱的內心。“她攥著酒杯的時候心想,還從來沒有喝過那么晶瑩的葡萄酒。”[4]175這一虛偽的“空間”深藏著主人公的嫉妒,又因為求而不得產生了極大的反諷,折射出裘落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她表現出對這種奢華的極度艷羨;另一方面,她又在憎恨這種渴望接近和抵達的生活。與此同時,井宇感到這幢房子充滿了虛假,“但作為一個奮斗目標,它又是那樣真實”[4]176。張悅然將同為一種屬性的兩個空間——老霍的家與主人公的家——并置起來,豪宅代表著高于小資產階級的層次,豪宅里的一切是小家所不能及的,小家里的一切都是豪宅所不屑的,小資產階級青年在羨慕嫉妒大資產階級之外也綿延出一種深切的無力感。于是,井宇與裘落以對“家”的雙重逃離邁出了改變現狀的第一步。
通過空間鋪排以及空間并置的書寫,將主人公在當下的困境毫不掩飾地呈現出來:社會結構的固化使亟待成長的年輕人喪失了生存的活力。小資產階級一代告別青春期的病態,不再囿于靜止的舒適圈內沾沾自喜,而是感覺對現狀不滿并展開對人生的思索,繼而動身逃離固有的天地,尋得一種新的可能,這便是《家》的第一重闡釋。
二、“曇花”怒放——《家》與女性的獨特奧秘
優秀的文本總是多義性的,如果作者僅僅將創作視野從個人經驗擴大到同一代人,那么《家》的下半部便顯得突兀而多余。顯然,這是作者主動選擇的敘事策略。小菊不僅是邏輯結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而且這個農村姑娘的在場又為讀者提供了另一重的解讀可能,而裘落正是突破闡釋之門的鑰匙。
要想讀懂小菊這一女性角色,必須追溯至裘落。作為小資產階級女青年的裘落,不僅面對著與井宇同屬一代人的困境,其背后還暗藏了女性獨有的奧秘。在“家”中,裘落以相對傳統的女性形象承擔了各種生活瑣事,不免也淪為了男性的附屬品。她離家之前的內心想法讓人深思,對井宇新生活的假想——主要是對新的女性伴侶的猜測就足以使她受傷與難過。再者,裘落還看了有關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電影及其文集,她凝視著書籍扉頁的作者像:“那張實在不能算漂亮的長臉上,有一雙審判的眼睛,看得人心崩塌,對現在所身處的虛假生活供認不諱。”[4]174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裘落的自白,虛假的生活使裘落與伍爾夫達成了一致,攜帶著女性主義意識的伍爾夫也成為了她追逐的目標。裘落無法與結婚生子的同性好友談論伍爾夫,女性意識的話題也不再為她們所共有。可見,她并不認同女性成為妻母的生活方式,而是逃離了“家”。由此,對這一空間的叛逃又象征著女性的自我解放,出走也成為了女性的一種自衛方式。
當資產階級一代退場,故事的視角轉移到了農村保姆小菊身上,小菊的故事也撐起了一個富有張力的空間。裘落與井宇雙雙逃離卻互相不知,而小菊成為連接他們與“家”的關系的紐帶,同時小菊也作為在場的主體置身于他人的“家”中。或者說,“家”這一空間貫通了小說的上下兩部分,承擔著組織情節、推動故事發展的作用。敘述者首先以小菊的視角講述了她只身一人在外打工以補貼家用的心酸,女性成為了挑起家庭重擔的主要勞動力,作為丈夫的男性卻終日無所事事。可見,小菊雖身處現代化的大都市,但仍舊無法擺脫封建傳統的家庭關系。小菊的另一關鍵作用還在于她代替裘落成為了井宇的傾訴對象,我們通過小菊對井宇信件的閱讀洞察了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深層次關系,而此時小菊也是溝通讀者與文本的中介,指引著讀者進入“百花深處”。張悅然并沒有再次利用“青春期”的代入感以引起讀者的共鳴,而是使故事人物與讀者攜手拓寬了文本的意義空間。通過信件,讀者得知井宇與裘落并未步入婚姻殿堂,而是以同居的方式相處了6年。“家”之于他們只是一個共有的空間,根本無法承載“家庭”的重要意義。巴蘭坦曾經寫道:“家負載有意義,因為家是我們認識世界的基礎,與我們生活中最為私密的部分密切相關。家目睹了我們所受的羞辱和面臨的困境,也看到了我們向外人展現的形象。在我們最落魄的時候,家依然是我們的庇護所。”[5]家是人類的避風港,而對井宇與裘落而言,嚴格意義上的“家”并不存在,“家”叛離了原型意義而成為禁錮的牢籠。同時,男女主人公的“出”與保姆小菊的“進”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使“家”的意味無限綿延。“家”對于小菊來說具有深刻意義,它寄托著農村女孩對于大城市的憧憬,小菊渴望有一個“家”的空間來撫慰在大城市艱辛生活的自己。所以,她自在地生活在這個“家”中,重復著裘落的日常慣例——喂貓、洗熱水澡、看電影等等。當然,小菊也看伍爾夫,尤其對《一間自己的屋子》印象深刻:“里面說,女人必須有一間自己的屋子,小菊讀著覺得很觸動。”[4]187“出/進”與“伍爾夫”使兩位女性萌生了藕斷絲連的鏡像關系,裘落的逃離也引發了小菊對于自身婚姻與人生的思考。至此,嚴肅的性別話題顯得更加明朗,而這間屬于“自己的屋子”儼然成為了女性的心理空間。“娜拉出走后怎樣”在裘落身上得以重映,雖然她們面對的問題不同,但卻共同分享了一種實質,張悅然展現了新的歷史語境下女性解放的經典主題。作為小資產階級女性的裘落在覺察兩性關系失衡之后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出”,那么保姆小菊的“進”又將演繹出怎樣的女性之舞呢?
作為后經典敘事學的分支,女性主義敘事學是女性主義文評與經典結構主義敘事學相結合的產物,自20世紀80年代起,逐漸成為一個發展勢頭強勁的跨學科流派。女性主義敘事學不僅關注隱含的作者的創作目的以及作者與讀者的交流,更聚焦于敘事結構和敘述技巧的性別政治。其代表人物蘇珊·瑟在《虛構的權威》一書中指出,女作家采用“公開的作者型敘述”可以建構并公開表述女性主體性和重新定義女子氣質,而女作家采用的“個人型敘述”則可以建構某種以女性身體為形式的女性主體的權威。“每一種權威敘事形式都編制出自己的權威虛構話語,明確表達出某些意義而讓其他意義保持沉默。”[6]短篇小說《家》便兼顧了這兩種敘述方式:上半部“裘落”中的敘述者與作者的聲音相一致,可看作是張悅然的“公開的作者型敘述”;但是在小菊部分,敘述者與作者截然分開。小說下半部以農村保姆小菊為視點,在閱讀信件時小菊更是成為了掌握話語空間的敘述者,顛覆了信件原始的敘述者男性井宇與受述者女性裘落。小說中男女主人公誰是敘述者,誰是受述者,誰是敘述對象成為一種權力之爭,這種人物敘述權之爭也是男女社會斗爭的體現[7]。小菊成為敘述者遂象征著女性不再處于“他者”的地位,而是掌握了主動的話語權。《家》中敘述者的“全知敘述”與小菊的“個人型敘述”,都不約而同地為我們發出了女性主義的吶喊。張悅然筆下的女性角色在此發生了蛻變,裘落與小菊都不再是“青春小說”中的懵懂少女,她們生發出了女性意識的特質,理性地思考人生的困境,進而求證自我的存在。“娜拉”的出走,女性的解放又為《家》增添了一重闡釋的能指。
最后,由于裘落與小菊的特殊身份,不得不對小菊這一女性角色予以重新觀照。這一人物的魅力如同撲閃著雙翅的精靈,使文本散發出別樣的光芒。來自農村的底層人物與城市小資產階級互不相融,小菊進城當保姆也自然無法輕易獲得主人家的青睞。在裘落眼中,小菊無疑是缺乏素質的一類人:“小菊初來的時候,她簡直有些受不了,是一種草的味道,是干硬的糧食的味道,是因為吃得不好、缺乏油水而散發出的窮困的味道。”[4]173城鄉空間的遙相對立以及城市人與農村人的敵視在現代性飛速發展的今天已然成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都市現代性文化帶來的沖擊,以及以旁觀姿態經歷過的城市資產階級的困境,使小菊對傳統的鄉村文明產生了懷疑。她想掙脫這支戴著鐐銬的隊伍,獲得一點自由,于是,她提出了離婚。她想要擺脫來自家庭的牽絆,然而,一場地震又頃刻熄滅了初生的火苗。同時,她對城市“家”的感受也有所改變。“看著眼前的光景,覺得有些恍惚”,“墻上那個沒有秒針和刻度的表,總讓人以為它停住了”[4]190。此刻,“家”帶給小菊的是一種安靜與冰冷。從人物視角對空間的描寫,不僅反映了空間的形態,也反映了人物的心理空間,與之前小菊的渴望形成對比的是她的卻步,城市——“家”成為既想靠近又頗有距離的空間,由此也反映了城市對于農村人的可望而不可即。最終,她讓丈夫也來到了北京,其中有這樣一段描寫令人回味:“小菊好像也看得見,他正從一片破墻爛瓦中走出來,走著走著,他回過頭去,留戀地看了一眼。”[4]193這最后一眼不僅是她丈夫也是小菊向農村空間所作的最后的告別,地震后的“農村”一片殘垣斷壁,“農村”的日漸衰敗堅定了他們進城的決心。小菊更換了臥室的床單,帶著對新生活的憧憬,占據了主人公的“家”。一代代的農村人懷著熱切的向往,飛蛾撲火般地來到城市。身為小資產階級的主人公覺醒了,而還未成為小資產階級的小菊迷失了。張悅然告訴我們,農村人或許只能游走在城市的邊緣,他們于城市來說終究是“局外人”,城鄉之間矛盾的緩和還有一場馬拉松式的長跑,這又是作者提供給我們的另一層思考。
三、“曇花一現”——從《家》看張悅然創作的一種嘗試
短篇小說《家》的多重闡釋空間正如怒放的曇花,于讀者不經意間安靜地層層展開,綻出迷人的笑靨。然而,“曇花”似乎并未以一個完美的收尾來結束難得一遇的盛開。張悅然讓逃離的男性、出走的女性雙雙來到了地震災區,這又顯現出作者依附歷史來重塑主體性的意圖。
四川綿陽災區構成了一個承載意義的空間,它的表意是歷史的想象,內核卻是非恒定的——這個空間是偶然產生的,它包含著太多的不穩定性。倘若地震并未來臨,它也就不會成為災區,自然也不會需要救援,那么,主人公也無法實現重塑主體的企圖。張悅然創造了一個隨時發生變化的空間試圖解決問題,是不具有說服力的。但是我們也可以做出如下理解:小資產階級用何種方式來反抗不滿的現狀不得而知,但正是這種“不知”又使文本呈現出開放式的空間,作者指出了這一代人的困境,而將“知”留給讀者思索,由此也營造了文本“多知”的意境。同樣地,對小菊的處理,讀者的反應也是“多知”的。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信件的敘述者是小菊,此時的話語空間便是“家”這一空間。通過農村姑娘小菊這一特定視角,敘述主人公對家的逃離,如此便成為一個悖論:一面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對“家”的逃離,一面是農村姑娘對“家”的渴望,作者一邊在消解“家”的意義,一邊又在建構“家”。然而結局還是留給了讀者:或許農村人小菊進入城市,會成為一個不同于小資產階級的新人?又或許會重蹈主人公的覆轍,成為裘落一樣的女性,面對同樣的困境?抑或會繼續追逐著伍爾夫,走出困住女性的牢籠?《家》的結尾既像是在解結又同時在打結,J.希利斯·米勒曾說:“真正具有結束功能的結尾必須同時具有兩種面目:一方面,它看起來是一個齊整的結,將所有的線條都收攏在一起,所有的人物都得到了交代;同時,它看起來又是解結,將纏結在一起的敘事線條梳理整齊,使它們清晰可辨,根根閃亮,一切神秘難解之事均真相大白。”[8]從后經典敘事學的角度而言,《家》不僅內含多重的闡釋空間,在很大程度上也實現了與讀者的互動,讀者成為了文本的一部分,與作者一起分享著故事的秘密,“難以解釋的符號”成為優秀藝術的圖騰。
“80后”作家自“新概念作文大賽”進入大眾視野,其“作文”并非“文學”決定了他們只能暫時悠游于市場。隨著時間的推移,“80后”文學隱約出現分化的趨勢,張悅然成為這一代由市場叩擊文壇進程中備受矚目的作家。她在2006年末推出的“歷史記憶”小說《誓鳥》入選“中國小說排行榜”,可謂是主流文壇對張悅然創作的一種肯定。而她自身也逐漸步入純文學的軌道,試圖抽離“偶像派”的光圈。她飽含著對“文學”的熱淚,執著于對“文學”的探索,甘愿接受“純文學”的檢驗。從這一角度而言,“青春寫作”似乎是其向“文學”靠攏的一條路徑,遺憾的是這條路的指向與她的終極目標背道而馳。張悅然正如筆下的“葵花”一般走向了迷失,既然此路不通,那便重揚風帆邁出新的征程。短篇小說《家》即是這次征程中的瑰寶,初讀——沾染塵土暗淡無光,再讀——洗凈灰霾熠熠生輝。《家》雖然也演繹了一場場生活敘事,但不同于以往,這一次現實不再被“懸置”,而是貼近讀者內心最柔軟的地方。通過“家”所建構的日常現實,將小資產階級一代與農村一代以及男性與女性的生存困惑展現得淋漓盡致。文學作為人學,必須要反映作家對現實獨特而深刻的感受,并給讀者提供形而上的思考,文學對社會道德訓誡、對人的心靈與精神的指引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而使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正是其自身的“文學性”,《家》的多重闡釋空間以及“難以解釋的符號”正是張悅然小說“文學性”的顯現。
困境—轉型—成熟是很多作家寫作生涯中的必經階段,但張悅然的寫作卻更為復雜。許多作家的天平向歷史和記憶傾斜,以此表明個人思想和寫作上的逐漸成熟,張悅然同樣如此,雖然《誓鳥》與《繭》兩部長篇作品稍有瑕疵,但這種打破牢籠、企求新生的意識是值得肯定的。同時這也折射出寫作者的困境,是否轉型必須依托于長篇小說?是否長篇小說的容納量才足以使作品冠以轉型力作之名?張悅然2010年的短篇舊作便可視作“曇花一現”的回應。這部短篇舊作相較于張悅然的長篇力作較少受到批評家們的關注,自然也無法成為他們筆下的言談對象,然而其中小資產階級一代人的困境、女性解放以及進城的主題都不同程度地向嚴肅文學靠近。或許因為作家對短篇的把握相較于長篇更加容易,而長篇巨大的篇幅容量往往更難以駕馭,但這足以說明作家的重生完全可以從短篇小說著手。短篇雖容量有限,但其可蘊含無限的意味,也可拓展出一片新的天地。張悅然是頗具生長性的作家,其成長與轉變并非一帆風順,稍以回望會發現作家的創作并非易事,背后牽涉到多種復雜的因素——作者自身的主觀愿望、寫作資源、客觀的歷史環境、讀者的接受度等等。創作與批評的攜手共進才能使作家的創作臻于完善。以理性的目光觀照張悅然的短篇小說《家》,我們有理由認為:《家》是張悅然創作的另一種嘗試,是其創作生涯中的“一現”曇花。
四、結語
“80后”作家初登歷史舞臺,以“青春寫作”進入市場,繼而抽離浮躁,以嶄新的面貌叩開文學大門。十多載后,最初的“少年”成長為“青年”,進而步入中年,“校園文學”“青春文學”早已不是“80后”寫作的標簽。每一個有理想的作家都在尋求創作上的開拓與突破,兼具“偶像派”與“實力派”兩者之長的張悅然,無疑以自覺的文學追求在純文學的道路上走得最遠。縱觀其跨越青年步入中年的創作生涯,《家》是其中最出彩的一篇小說。具有多重闡釋空間且頗具現實意義的短篇小說《家》正如一朵曇花,安靜地等待花期,當時辰一到,它便層層綻開幽香的花瓣。“曇花”之于張悅然的創作終究是剎那的“一現”,但是這種考驗能使她洞悉生命更深層的意義。對于文學而言,抵達生命更深的層面依靠永恒的探索,而磨難和考驗是必經之路。正如她自己所言,“我們早慧而晚熟,出發雖遲終會抵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