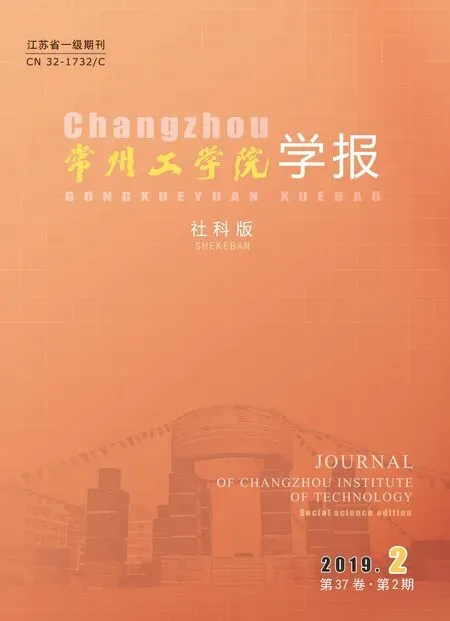《呼蘭河傳》中的“人間”
賈艷霞,劉濤
(河南大學(xué)文學(xué)院,河南 開(kāi)封 475001)
“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前期,整個(gè)中國(guó)社會(huì)都處于一種狂飆突進(jìn)的狀態(tài),各種各樣的文學(xué)思潮紛紛涌入中國(guó)文學(xué)界,人們?cè)噲D尋找到救國(guó)救民的良方來(lái)挽救大廈將傾的中國(guó)。在這各種思想觀念碰撞交匯的時(shí)代,周作人作為文壇的領(lǐng)袖,也在不斷地探索著適合中國(guó)并且能改造中國(guó)的新思想新理論,他最終找到了一種能夠構(gòu)建理想人間社會(huì)的理論——現(xiàn)代人道主義的“人間觀”。周作人的“人間觀”對(duì)當(dāng)時(shí)及以后的文學(xué)界都有著深刻的影響。蕭紅作為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的左翼作家,也很明顯地受到了周作人“人間觀”的影響,這表現(xiàn)在她的《呼蘭河傳》中。蕭紅的《呼蘭河傳》描寫(xiě)了一個(gè)互相隔膜使人們深受其害的世界,但是在這慘痛的世界中還有明亮的理想的精神之光——超越階級(jí)的“大人類主義”的祖父形象,這正是周作人想要構(gòu)建的理想世界的代表人物。
一、“五四”時(shí)期的“人間觀”及其對(duì)新文學(xué)的影響
“‘五四’前期,周作人在世界現(xiàn)代人道主義社會(huì)思潮的影響下,對(duì)現(xiàn)代人道主義的理論觀念在諸多方面做出了創(chuàng)造性的理論貢獻(xiàn),其中在‘人間觀’方面創(chuàng)獲頗多,他的‘人間觀’著重對(duì)‘大人類主義’的理論構(gòu)建、理想人間生活的實(shí)現(xiàn)等問(wèn)題進(jìn)行了深入思考。”①河南大學(xué)文學(xué)院張先飛教授曾在他的《“人”的發(fā)現(xiàn)——“五四”文學(xué)現(xiàn)代人道主義思潮源流》一書(shū)中對(duì)“五四”時(shí)期現(xiàn)代人道主義的“人間觀”進(jìn)行了研究,認(rèn)為現(xiàn)代人道主義“人間觀”是周作人先生的一個(gè)重要觀點(diǎn)。
周作人認(rèn)為,這“人間觀”首先是一種“大人類主義”,“人類是個(gè)總體,個(gè)人是這總體的單位”②。作為這總體中的一員,個(gè)人只是人類中同等的一員,每個(gè)“自我”彼此間沒(méi)有任何本質(zhì)上的差異,也不是對(duì)立的,但這“我”又是具有個(gè)體意識(shí)的“唯一者”,每個(gè)個(gè)體都有個(gè)性、個(gè)體意識(shí)高度發(fā)展的可能性,所以,“我即是人類”,“我”要講人道,愛(ài)人類,自愛(ài)而愛(ài)人。在周作人的“人間觀”中,理想人間生活的實(shí)現(xiàn),本質(zhì)上就是人間和諧關(guān)系的實(shí)現(xiàn)。如何實(shí)現(xiàn)這種理想的人間生活?周作人對(duì)現(xiàn)實(shí)人間作出的判斷是:人類精神的隔絕。“國(guó)家、種族間的對(duì)立、仇視,階級(jí)間的不平、對(duì)立,各種狹隘集團(tuán)間的沖突,普通人之間難以化解的敵意等。”③“人間”的不和,其本質(zhì)在于每個(gè)“自我”,由于人們的錯(cuò)誤觀念,“認(rèn)為彼此之間利害相對(duì),‘非損人不能利己’”④。那么,要打破這種精神隔膜,其核心便在于改變?nèi)说木瘢茏魅颂岢龈淖兙窀裟ぞ褪菍?shí)現(xiàn)理想人間的途徑,“在理性上完全接受人道主義的真理,并在感情上發(fā)生轉(zhuǎn)變,而且還要徹底改變?nèi)藗兟槟镜木駹顟B(tài),培養(yǎng)出‘愛(ài)與理解’以及對(duì)其他個(gè)體精神的‘感受性’等精神能力”⑤。
“周作人的這種思考,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的思想界、文學(xué)界都有著深刻影響。”⑥這種影響力首先表現(xiàn)在他對(duì)京派作家如廢名、沈從文等寫(xiě)作的影響,他們的作品沖淡、平和,表現(xiàn)了理想人間的和諧美,如沈從文的作品給我們描繪了一個(gè)淳樸優(yōu)美的湘西世界,汪曾祺則書(shū)寫(xiě)出了中國(guó)傳統(tǒng)美德和中國(guó)人的靈性。甚至我們還可以從戰(zhàn)斗作家的作品中看到周作人“人間觀”的痕跡:“不能否認(rèn)孫犁受到過(guò)周作人的深刻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周作人和孫犁的創(chuàng)作都有淡遠(yuǎn)明靜的藝術(shù)特征。孫犁易受周作人影響的深層原因在于二人性格、氣質(zhì)及讀書(shū)路徑的相似。”⑦周作人的“人間觀”可以用很多文學(xué)作品來(lái)印證分析,本文擬對(duì)蕭紅的《呼蘭河傳》中的“人間觀”作一分析。
二、《呼蘭河傳》中的“人間”的精神隔膜
蕭紅的《呼蘭河傳》以一個(gè)孩子的視角刻畫(huà)了一個(gè)小城“呼蘭河”的地理風(fēng)物、眾生眾相。文章一開(kāi)頭就描寫(xiě)一個(gè)大泥坑,這個(gè)泥坑下雨時(shí)蓄滿了水,大家沒(méi)有辦法過(guò)去,只能沿著墻根一點(diǎn)一點(diǎn)挪;晴天時(shí)就成了一個(gè)大泥潭,總是會(huì)淹死牲畜,有時(shí)還會(huì)淹死人。可以說(shuō)這個(gè)泥坑對(duì)整個(gè)縣城的人都危害不小,但是“說(shuō)拆墻的有,說(shuō)種樹(shù)的有,若說(shuō)用土把泥坑來(lái)填平的,一個(gè)人也沒(méi)有”⑧,人們都是得過(guò)且過(guò),麻木度日,這正是周作人所說(shuō)的“精神隔膜”,缺少“愛(ài)與理解”。
文中,最讓人觸目驚心的就是小團(tuán)圓媳婦的遭遇。小團(tuán)圓媳婦才到婆家的時(shí)候,“她的頭發(fā)又黑又長(zhǎng),梳著很大的辮子,普通姑娘們的辮子都是到腰間那么長(zhǎng),而她的辮子竟快到膝間了。她臉長(zhǎng)得黑乎乎的,笑呵呵的”⑨,一個(gè)活潑可愛(ài)的小姑娘形象躍然紙上。但是婆婆呢,要給小團(tuán)圓媳婦一個(gè)下馬威,于是就打她,“打了她一個(gè)多月”,“把她吊在大梁上”抽她,“用燒紅過(guò)的烙鐵烙過(guò)她的腳心”⑩,平時(shí),“做婆婆的打了一只飯碗,也抓過(guò)來(lái)把小團(tuán)圓媳婦打一頓。她丟了一根針也抓過(guò)來(lái)把小團(tuán)圓媳婦打一頓。她跌了一個(gè)筋斗,把單褲膝蓋的地方跌了一個(gè)洞,她也抓過(guò)來(lái)把小團(tuán)圓媳婦打一頓。總是,她一不順心,她就覺(jué)得她的手就想要打人。她打誰(shuí)呢?誰(shuí)能夠讓她打呢?于是就輪到小團(tuán)圓媳婦了”。等到把小姑娘打怕了,白天也哭,夢(mèng)里也叫時(shí),又說(shuō)她生病了,開(kāi)始給她治病,“偏方、野藥、大神、趕鬼、看香、扶乩”,直到最后用熱水燙她,還連燙三次,所謂“洗澡”,最后終于把這樣一個(gè)機(jī)靈孩子活生生折磨死了,這死對(duì)小團(tuán)圓媳婦來(lái)說(shuō),反而是一種解脫。這種愚昧,正是周作人所說(shuō)的“非損人不能利己”,但是這個(gè)婆婆乃至整個(gè)老胡家并沒(méi)有得到任何好處,只能說(shuō)是“損人不利己”,或者他們自己覺(jué)得能夠“利己”,也就是得到一種精神上的優(yōu)越感。
而在整個(gè)小團(tuán)圓媳婦被管教被治病(被毆打被折磨)的過(guò)程中周圍鄰人的表現(xiàn),就更加體現(xiàn)了周作人所說(shuō)的“精神的隔膜”了。“于是一些善人們,就覺(jué)得這小女孩子也實(shí)在讓鬼給捉弄得可憐了。哪個(gè)孩兒是沒(méi)有娘的,哪個(gè)人不是肉生肉長(zhǎng)的。誰(shuí)家不都是養(yǎng)老育小……于是大動(dòng)惻隱之心。東家二姨,西家三姑,她說(shuō)她有奇方,她說(shuō)她有妙法。”其實(shí)呢,這哪里是真正的治病救人,這是什么藥方?“吃全毛的雞,連毛帶腿地吃下去”,這分明就是在折騰人。于是,老胡家就“又跳神趕鬼、看香、扶乩,老胡家鬧得非常熱鬧。傳為一時(shí)之盛。若有不去看跳神趕鬼的,竟被指為落伍”,“大家都想去開(kāi)開(kāi)眼界,就是那些患了半身不遂的,患了癱病的人,人們覺(jué)得他們癱了倒沒(méi)有什么,只是不能夠前來(lái)看老胡家團(tuán)圓媳婦大規(guī)模地洗澡,真是一生的不幸”。這些描寫(xiě)把民眾們看他人不幸為獵奇的心理刻畫(huà)得惟妙惟肖,讓人膽戰(zhàn)心驚,人與人之間的精神隔膜至斯,真是讓人不得不反思。看小團(tuán)圓媳婦洗澡的場(chǎng)景,蕭紅的描寫(xiě)如神來(lái)之筆:“看熱鬧的人,你望望他,他望望你。雖然不知道下文如何,這小團(tuán)圓媳婦到底是死是活。但卻沒(méi)有白看一場(chǎng)熱鬧,到底是開(kāi)了眼界,見(jiàn)了世面,總算是不無(wú)所得的。”看他人受苦是看熱鬧,開(kāi)眼界。而大神為了吸引人,要她連洗三次澡,“于是人心大為振奮,困的也不困了,要回家睡覺(jué)的也精神了。這來(lái)看熱鬧的,不下三十人,個(gè)個(gè)眼睛發(fā)亮,人人精神百倍。看吧,洗一次就昏過(guò)去了,洗兩次又該怎樣呢?洗上三次,那可就不堪想象了。所以看熱鬧的人的心里,都滿懷奧秘”。以“損人”來(lái)滿足自己的獵奇心理,借以忘卻自己悲慘的毫無(wú)光明和未來(lái)的生存境況,正像周作人先生所說(shuō)的,“我們平常專講自利,又抱著謬見(jiàn),以為非損人不能利己……所以彼此都‘劍拔弩張’,互相疾視”,“我們能不妨害別人的生存而生存,不妨害別人的幸福而幸福么?當(dāng)然是不能的。現(xiàn)在人的生存與幸福的基礎(chǔ),便全筑在別人的滅亡與禍患上。這是錯(cuò)的,是不正當(dāng)?shù)摹薄?/p>
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已經(jīng)成為一個(gè)我們不得不正視的問(wèn)題,也是所有中國(guó)人必須想辦法解決的問(wèn)題。蕭紅完滿地詮釋了周作人先生的“人間觀”的精神隔膜問(wèn)題。
三、愛(ài)與理解的理想“人間”
其實(shí)在蕭紅的《呼蘭河傳》中,也有一抹亮色,這就是“我”的祖父,以及“我”和祖父在后花園中幸福的玩鬧時(shí)光。
在《呼蘭河傳》中,“我”是一個(gè)爸爸不疼,媽媽不愛(ài),祖母也嫌棄的一個(gè)很可憐的小家伙。祖母拿針扎“我”,罵“我”;父親呢,則是,“一腳把我踢翻了,差點(diǎn)沒(méi)把我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去”,而母親在文中很少出現(xiàn),好像她在“我”的童年中本就是一個(gè)無(wú)足輕重的小角色。只有祖父,一直在,一直愛(ài)。
“我生的時(shí)候,祖父已經(jīng)六十多歲了,我長(zhǎng)到四五歲,祖父就快七十了。”就是這樣一個(gè)老人,卻給了童年的“我”無(wú)限的關(guān)愛(ài)和樂(lè)趣。“祖父一天都在后園里邊,我也跟著祖父在后園里邊。祖父戴一個(gè)大草帽,我戴一個(gè)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鏟地,我也鏟地”,“我”就是祖父的小跟屁蟲(chóng),調(diào)皮而且可愛(ài)。“我”總是跟著祖父,是因?yàn)樽娓笇?duì)“我”好,“我”把韭菜割掉,把狗尾草留著,祖父不生氣,只是大笑,笑完細(xì)細(xì)給“我”講谷子和狗尾草的區(qū)別。“我”把祖父的玫瑰花都摘了在他的草帽上插一圈,祖父知道了,也不像一般的大人一樣惱羞成怒,而只是笑,“他笑了十多分鐘還停不住,過(guò)一會(huì)兒一想起來(lái),又笑了”,“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祖父愛(ài)“我”,也愛(ài)所有的孩子,所以他常常和孩子們開(kāi)玩笑,“每當(dāng)祖父這樣做一次的時(shí)候,祖父和孩子們都一齊地笑得不得了”。這是一個(gè)慈祥善良的好老頭。祖父天天教“我”念詩(shī),“早晨念詩(shī),晚上念詩(shī),半夜醒了也是念詩(shī)”。又給“我”做好吃的,烤豬肉,烤鴨子。一幅天倫之樂(lè)的和諧圖景。
“就這樣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園,我,這三樣是一樣也不可缺少的了。”祖父和“我”在后花園中其樂(lè)融融的樣子,不正是周作人所提倡的理想人間嗎?在這個(gè)理想人間中,人和人相愛(ài),互相理解。“我”愛(ài)祖父,有什么好玩的都想叫上祖父,讓祖父看;祖父愛(ài)“我”,寵著“我”,慣著“我”。這是幸福的人間。
但是,祖父的愛(ài)并不僅僅是針對(duì)“我”一個(gè)人的,他是一個(gè)具有悲天憫人大情懷的人。在小團(tuán)圓媳婦的悲劇中,他是唯一對(duì)小團(tuán)圓媳婦持深切同情的人。剛見(jiàn)到小團(tuán)圓媳婦時(shí),只有祖父說(shuō)她“怪好的”;在他們不斷地打罵折磨小團(tuán)圓媳婦時(shí),祖父則不斷地說(shuō),“明年二月讓他們搬家”,又說(shuō)“好好的孩子快讓他們捉弄死了”,“二月讓他搬家。把人家的孩子快捉弄死了,又不要了”。這是整個(gè)鬧劇中唯一清醒的人,他悲憫同情著小團(tuán)圓媳婦,他理解她的處境,卻無(wú)可奈何,因?yàn)檎麄€(gè)大環(huán)境麻木愚昧。當(dāng)租戶馮歪嘴子遭難時(shí),又是祖父給他提供了一席之地,還注意照顧到他的自尊心,“你沒(méi)看馮歪嘴子的眼淚都要掉下來(lái)了嗎?馮歪嘴子難為情了”。大家都在議論馮歪嘴子和王大姐的事情,熱鬧非凡,只有祖父,“是什么也不問(wèn),什么也不聽(tīng)的樣子”。馮歪嘴子來(lái)“我”家吃飯,飯后祖父一定會(huì)溫和地讓他帶上幾個(gè)饅頭回去,好喂他的孩子。祖父對(duì)世人的愛(ài)是超越階級(jí)的,是符合“大人類主義”的愛(ài)。
蕭紅在《呼蘭河傳》中描寫(xiě)了一群人相互隔膜、彼此傷害的人間悲劇,又刻畫(huà)了一個(gè)充滿愛(ài)與理解的理想人間的大人類典范祖父,正是通過(guò)這種對(duì)比,把“我”家的后花園塑造成了一個(gè)理想的人間樂(lè)園,使讀者能夠看到精神隔膜的毒害,充滿愛(ài)與理解的理想世界的美好,從而最完美地詮釋了周作人的“人間觀”。
周作人先生在“五四”時(shí)期呼吁的消除精神隔膜,彼此用愛(ài)和理解來(lái)塑造理想世界的“人間觀”,在今天看來(lái),仍然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從錢(qián)鍾書(shū)《圍城》中的愛(ài)人和朋友之間的隔膜,到王安憶作品中的人情洞察背后的隔膜的悲涼,從余華筆下的《活著》《第七日》到莫言作品對(duì)整個(gè)社會(huì)整個(gè)人間的思考,作家無(wú)不是在思考著這個(gè)社會(huì)的種種病痛,用筆來(lái)剖析、刺破人間的種種毒瘤,以建造一個(gè)充滿愛(ài)與理解的理想人間。從這個(gè)角度來(lái)看,周作人的“人間觀”有著十分重大和深遠(yuǎn)的意義,應(yīng)該并值得進(jìn)行深入的研究。
注釋:
①③⑤⑥張先飛:《“人”的發(fā)現(xiàn)——“五四”文學(xué)現(xiàn)代人道主義思潮源流》,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9年,第151頁(yè),第184頁(yè),第195頁(yè),第195頁(yè)。
④周作人:《新文學(xué)的要求》,《晨報(bào)》,1920年1月8日。
⑦李中華:《談周作人對(duì)孫犁的影響》,《鄭州航空工業(yè)管理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6年第1期,第34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