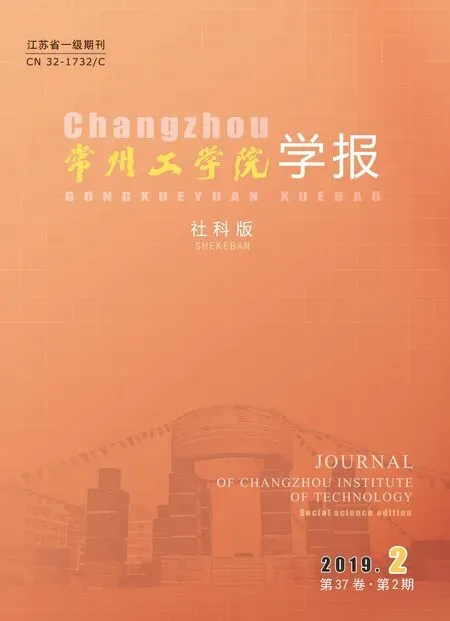離散書寫與離散譯介的互生關(guān)系
——以張錯(cuò)為例
馬明蓉,張向陽(yáng)
(1.廣東外語(yǔ)外貿(mào)大學(xué)高級(jí)翻譯學(xué)院,廣東 廣州 510420;2.常州工學(xué)院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江蘇 常州 213022;3.長(zhǎng)沙理工大學(xué)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湖南 長(zhǎng)沙 410114)
在我國(guó)學(xué)界,較早關(guān)注離散書寫的是簡(jiǎn)文志①,而較早關(guān)注離散譯介的是孫藝風(fēng)②。此后,離散書寫和離散譯介逐漸成為學(xué)界的關(guān)注熱點(diǎn),是當(dāng)下比較文學(xué)、文化研究、世界華文文學(xué)等領(lǐng)域的重點(diǎn)話題。
就離散書寫而言,理論研究層面上,離散書寫與作者的文化身份、中華文化的全球傳播、后殖民語(yǔ)境下的身份認(rèn)同、離散作品與世界文學(xué)和比較文學(xué)的關(guān)系等話題得到較多關(guān)注;研究?jī)?nèi)容上,研究者從作家或作家群入手,分析離散書寫的特征,特定作品的文學(xué)、社會(huì)學(xué)意義。關(guān)注度較高的離散作家有林語(yǔ)堂、張愛(ài)玲、白先勇、嚴(yán)歌苓、聶華苓、余光中、林幸謙、葉維廉等。離散作家群基本按離散居留地劃分,如東南亞離散作家、北美離散作家、歐洲離散作家、澳新離散作家、東北亞離散作家等。離散書寫研究的文類以小說(shuō)、詩(shī)歌、散文為主。
就離散譯介而言,國(guó)內(nèi)學(xué)界既有關(guān)于離散譯介作品、離散譯者的個(gè)案研究,如林太乙《鏡花緣》的英譯、華人離散族群的文化翻譯研究,也有宏觀理論層面的探索。例如,王曉鶯指出當(dāng)代翻譯研究中的離散命題可從離散作品研究、離散譯者研究和翻譯的離散屬性研究展開[1]12-16;孫藝風(fēng)則深入探討了離散譯者的文化使命[2]。
離散書寫和離散譯介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方面,相關(guān)術(shù)語(yǔ)的含義未得到深入闡發(fā),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研究的深入和細(xì)化。無(wú)論是“離散書寫”還是“離散譯介”,無(wú)論是“離散作家”還是“離散譯者”,學(xué)界目前尚缺乏認(rèn)可度較高的社會(huì)學(xué)意義界定。例如,“離散作家”的相近術(shù)語(yǔ)紛繁復(fù)雜,具體含義既有重疊,也有不同指涉,如“海外華人作家”“北美新移民作家”“華裔美國(guó)作家”等。另一方面,離散主體除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行為之外,還自覺(jué)或不自覺(jué)地具有離散譯介與傳播意識(shí),衍生出獨(dú)特的離散譯介行為。
離散主體有何社會(huì)、文化特質(zhì)?如何界定“離散書寫”與“離散譯介”?離散主體在離散書寫和離散譯介行為中的文化自覺(jué)意識(shí)如何發(fā)展?在離散書寫和離散譯介中,離散主體為構(gòu)建文化身份經(jīng)歷了什么?離散主體的離散書寫和離散譯介之間的關(guān)系如何?這些話題都有待進(jìn)行深入的系統(tǒng)性探究。
一、離散主體的界定
離散書寫和離散譯介均離不開從事創(chuàng)作和譯介的行為者,即離散主體。離散書寫是離散主體的詩(shī)文創(chuàng)作行為,而離散譯介是離散主體的譯介傳播行為。兩種行為都是離散主體在特定社會(huì)、歷史情境下的文化翻譯行為。從事離散書寫的離散主體是離散作家,而從事離散譯介的離散主體是離散譯者。
林幸謙考察了當(dāng)代作家的離散書寫,認(rèn)為不少當(dāng)代作家“都曾在海外烙下漂流異鄉(xiāng)居留的印記,從而構(gòu)成臺(tái)灣漂泊世代的主要群體”[3]103,他們雖然曾長(zhǎng)期在海外生活,但大部分都心系大陸,“書寫過(guò)某種程度的離散與流放主題”[3]104,可納入離散作家群體來(lái)研究。“身在異鄉(xiāng)心懷故土的海外作家大量書寫家鄉(xiāng)情愁”[4]114,“大部分作品亦往往在海外完成”[4]114,更重要的是,離散作家的創(chuàng)作往往體現(xiàn)“懷鄉(xiāng)/離散主題和作家在精神上的放逐形態(tài)”[4]114。離散作家首先經(jīng)歷地理位置的外在離散,離開父輩的故鄉(xiāng)或文化原鄉(xiāng)(第一居留地),由于戰(zhàn)爭(zhēng)、經(jīng)濟(jì)、政治等原因漸次漂流到第二甚至第三居留地。他們?cè)诘乩砜臻g的漂泊離散中,不可避免地體驗(yàn)精神空間的離散與流亡。然而,饒芃子指出,移居海外的華文作家,其“文化意識(shí)、思維方式、心理素質(zhì)仍然是中國(guó)式的”[5]195,作品中的“中華文化更多的是一種對(duì)故土的緬懷,一種超越時(shí)空的記憶,一種對(duì)于‘文化中國(guó)’的渴求與向往”[5]195。
從地理空間看,離散主體在海外居留較長(zhǎng)時(shí)間,遠(yuǎn)離文化原鄉(xiāng),是外在流放;從精神空間看,離散主體心系中華文化,是內(nèi)在回歸。在創(chuàng)作語(yǔ)言上,離散主體大多堅(jiān)持以母語(yǔ)——漢語(yǔ)進(jìn)行創(chuàng)作,以彰顯華人身份。離散主體的離散書寫多具有回望與追溯母語(yǔ)文化的特點(diǎn),他們往往通過(guò)離散書寫追憶、想象和重構(gòu)母語(yǔ)文化。離散主體長(zhǎng)期居留在中華故土之外,經(jīng)歷地理空間的“橫向移植”,但在精神空間上卻努力與中華文化保持強(qiáng)韌的“縱向承繼”,自覺(jué)或不自覺(jué)地在詩(shī)文創(chuàng)作、文化譯介中浸染家國(guó)想象、鄉(xiāng)土追尋等,是創(chuàng)造第三文化空間的行為者。離散主體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行為即離散書寫,此時(shí)離散主體的具體身份是離散作家;離散主體的譯介行為,包括自譯、編纂譯集、翻譯和出版等,此時(shí)離散主體的具體身份是離散譯者。
二、張錯(cuò)的離散書寫:雙重邊緣的母語(yǔ)文化尋根之旅
張錯(cuò),原名張振翱,生于1943年,廣東惠陽(yáng)人。他曾在廣州、香港、澳門讀中小學(xué),后赴臺(tái)就讀于政治大學(xué)西語(yǔ)系,創(chuàng)辦星座詩(shī)社。1967年赴美求學(xué),獲得華盛頓大學(xué)比較文學(xué)博士學(xué)位,1974年起任教于洛杉磯南加州大學(xué)。1965年至今,共發(fā)表16部詩(shī)集、11部散文集和多篇學(xué)術(shù)論文。張錯(cuò)在海內(nèi)外漢語(yǔ)詩(shī)歌界,尤其是現(xiàn)代詩(shī)壇影響較大,曾獲《中國(guó)時(shí)報(bào)》敘事詩(shī)首獎(jiǎng)、中興文藝獎(jiǎng)等。張錯(cuò)是“精神上扎根在中華文化、有著兩岸三地成長(zhǎng)經(jīng)歷”的華裔作家[6]78。
在離散書寫中,張錯(cuò)濃厚的文化自覺(jué)意識(shí)主要體現(xiàn)在離散書寫的鄉(xiāng)情歸依、母語(yǔ)文化堅(jiān)守、創(chuàng)作語(yǔ)言選擇3個(gè)方面。
正如美籍學(xué)者劉若愚所述,“中國(guó)人不樂(lè)于背井離鄉(xiāng)、遠(yuǎn)游他鄉(xiāng)”[7]65,“懷鄉(xiāng)之作自然成了一個(gè)不絕如縷的主題”[7]66。張錯(cuò)經(jīng)歷了多重離散,離散書寫體現(xiàn)了濃濃的鄉(xiāng)情歸依。第一重離散是從第一居留地(即文化原鄉(xiāng))往第二居留地漂移,是非自愿行為。第一重離散具有宏大的家國(guó)歷史背景,是戰(zhàn)爭(zhēng)性、政治性的放逐與離散。第二重離散是從第二居留地向第三居留地漂移,是自主性選擇。
在離散書寫中,張錯(cuò)一直堅(jiān)守母語(yǔ)文化。他強(qiáng)烈的民族主義精神在《雙玉環(huán)怨》序中得以體現(xiàn):中國(guó)是他“一生的婚配”[8]157。張錯(cuò)“不論離家多遠(yuǎn),永遠(yuǎn)不變的是對(duì)華族身份的堅(jiān)守”[6]81。在受訪時(shí),他說(shuō):“我非常強(qiáng)調(diào)我的中國(guó)性。”[9]53他認(rèn)為自己的離散書寫“何嘗離開過(guò)中國(guó)本土?”[9]59。張錯(cuò)有自覺(jué)繼承中文文學(xué)傳統(tǒng)的意識(shí)。雖然主修西方文學(xué),他和同時(shí)代的年輕人能“很開放地接受西方的東西,但在思維里面迫切感覺(jué)到一種傳統(tǒng)的需要,認(rèn)為中國(guó)傳統(tǒng)是不能丟掉的”[9]58。他主動(dòng)旁聽中文系的課,“詩(shī)選、詞選、曲選與中國(guó)文學(xué)史,什么都有”[9]50。張錯(cuò)以詩(shī)文創(chuàng)作進(jìn)行離散書寫,其本質(zhì)是以離散書寫實(shí)現(xiàn)文化意義上的自我精神救亡和自我文化補(bǔ)給,從而在放逐語(yǔ)言中回歸精神文化原鄉(xiāng),獲得母語(yǔ)文化歸屬感。
張錯(cuò)在離散書寫中自覺(jué)思考創(chuàng)作語(yǔ)言的選擇。張錯(cuò)在大學(xué)期間,出版了第一部漢語(yǔ)詩(shī)集《過(guò)渡》。隨后,他前往第三居留地——美國(guó)深造。在英語(yǔ)自譯選集Drifting的序言中,他對(duì)離散書寫的語(yǔ)言選擇歷程作了回顧:
“I first came to America in 1967 as a graduate student in English.At the age of 23,I had already published two volumes of poetry and a volume of prose in Chinese before coming to the States.Writing poems in English had imbued with me a spirit of the cosmopolitan,an American dream that I could be part of the melting pot process.But I soon discovered that the precision of language,and the insistence of such,as an expression in poetry,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ersistence of my ethnic identity.Wasting no time,I wrote mainly in Chinese again.”③[10]9-10
張錯(cuò)曾經(jīng)嘗試以英語(yǔ)進(jìn)行離散書寫,期望自己能順利地融入美國(guó)的文化“大熔爐”,但短暫的嘗試后,仍回歸以母語(yǔ)進(jìn)行離散書寫的模式。詩(shī)人認(rèn)為選擇特定語(yǔ)言創(chuàng)作,就是選擇特定的民族文化身份發(fā)聲。“張錯(cuò)坦言是中國(guó)人,用華文為中國(guó)人而書寫。”[11]21張錯(cuò)最終決定以漢語(yǔ)進(jìn)行離散書寫,這是凸顯民族性和中國(guó)性的文化自覺(jué)行為。
海外華文書寫者“通過(guò)記憶、回望、想象、傳說(shuō)等方式致力于用母語(yǔ)的表達(dá)沖破固有的牢籠,自覺(jué)地保持自身的尊嚴(yán)和母性的聲音的努力,以抗衡西方世界中存在的種族偏見(jiàn)和文化誤解乃至歧視”[12]50。張錯(cuò)堅(jiān)持中國(guó)性,在離散詩(shī)歌中流露出“飄零的痛苦,身份的挫敗,還鄉(xiāng)的憧憬”[13]85,離散書寫的語(yǔ)言選擇,反映了他以離散書寫構(gòu)筑文化身份的努力和文化自覺(jué)意識(shí)的覺(jué)醒。在西方主流文學(xué)大潮中,他嘗試用處于邊緣位置的“他者”語(yǔ)言創(chuàng)作,這既是解構(gòu)西方文學(xué)與文化的嘗試,也是凸顯離散主體母語(yǔ)文化的努力,對(duì)于豐富兩者的文學(xué)形式具有積極的意義。
三、張錯(cuò)的離散譯介:全球化語(yǔ)境下重塑母語(yǔ)文化之舉
在構(gòu)建文化身份過(guò)程中,張錯(cuò)的離散譯介行為包括編纂譯集、詩(shī)歌自譯和譯介出版等。
張錯(cuò)編纂譯集時(shí)曾說(shuō):“選集里面你就要產(chǎn)生出你對(duì)文學(xué)整理的觀念。”[14]96同時(shí),他質(zhì)疑年度詩(shī)選和十年一期的年代詩(shī)選,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選集的重要性。在《結(jié)網(wǎng)與羨魚》中,張錯(cuò)認(rèn)為“目前大多數(shù)的現(xiàn)代翻譯詩(shī)選多以‘詩(shī)選集’為主”,“最缺乏的仍是個(gè)人詩(shī)集翻譯”,“詩(shī)人作品作精品選譯,目前以數(shù)量及代表性而言,仍未足夠,徒足誤導(dǎo)世界讀者對(duì)臺(tái)灣現(xiàn)代詩(shī)作的判斷與整體透視”[15]62-63。于是,張錯(cuò)主張“個(gè)別詩(shī)人的作品以單本方式來(lái)翻譯出版”[15]63,以此促進(jìn)世界文學(xué)對(duì)現(xiàn)代詩(shī)歌的認(rèn)可與接受。
為促進(jìn)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人在世界范圍發(fā)聲,張錯(cuò)遴選詩(shī)人和作品,組織翻譯了5位現(xiàn)代詩(shī)人(焦桐、席慕蓉、張錯(cuò)、陳義芝和許悔之)的詩(shī)歌選集。他在譯集序中談到:
“The above list represents two generations of poets wh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in Taiwan in the past two decades.”④[10]5-6
張錯(cuò)之所以選擇這5位詩(shī)人,是因?yàn)樗麄冊(cè)?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對(duì)現(xiàn)代中文詩(shī)壇的形成發(fā)揮了積極作用,能代表兩代詩(shī)人的成就。5位詩(shī)人的個(gè)人選集于2000年前后在美國(guó)Sun & Moon Press(日月出版社)以Green Integer(《綠的合集》)系列出版。詩(shī)作均由張錯(cuò)遴選,譯者也由張錯(cuò)尋找最合適的人選擔(dān)任,譯稿最終由張錯(cuò)親自審定。可以說(shuō),在這5位詩(shī)人的英譯選集譯介中,張錯(cuò)先后扮演了翻譯任務(wù)發(fā)起者、編選者、翻譯代理/中介和審稿者等角色。角色綜合了離散譯者的文化身份和多重社會(huì)角色,因而其離散譯介是理性的、社會(huì)性的譯者行為,體現(xiàn)了離散主體語(yǔ)言性身份和社會(huì)性身份的有機(jī)融合。譯者的多種角色和諧統(tǒng)一于行為主體,離散譯者的文化譯介目標(biāo)起到了統(tǒng)攝作用。張錯(cuò)的譯介出版行為彰顯其宏大的世界文學(xué)構(gòu)建目標(biāo):
“把詩(shī)翻成另一國(guó)文字,以讓更多人分享與了解,甚至是把詩(shī)利用翻譯文字而與其他國(guó)家文學(xué)并列,從而進(jìn)入世界文學(xué)的殿堂,更是詩(shī)人與學(xué)者的抱負(fù)與努力目標(biāo)。”[15]56
以譯詩(shī)構(gòu)建世界文學(xué)的目標(biāo)既反映了他作為離散譯者的語(yǔ)言性身份(“把詩(shī)翻成另一國(guó)文字”),也顯示了他作為文化中介的社會(huì)性身份(極力促進(jìn)漢詩(shī)“進(jìn)入世界文學(xué)的殿堂”)。張錯(cuò)對(duì)文學(xué)作品譯介出版的理解,超越了語(yǔ)言層面的技術(shù)性探討,將譯詩(shī)置于世界文學(xué)交流對(duì)話的層面來(lái)看待,不能不說(shuō)具有前瞻性。張錯(cuò)前瞻性的世界文學(xué)視野得益于其離散書寫和離散譯介的跨文化體認(rèn)。張錯(cuò)的離散文學(xué)譯介理念是在雙重邊緣之上,重構(gòu)一個(gè)全新“中心”——地理空間。華語(yǔ)離散文學(xué)譯介反映其發(fā)展的獨(dú)特社會(huì)歷史文化背景。而在精神空間上,離散文學(xué)譯介是母語(yǔ)文化與其他居留地(主要是北美)文化的混融物,是離散主體重構(gòu)的第三文化空間。
通過(guò)譯介出版5位現(xiàn)代詩(shī)人的詩(shī)歌選集,張錯(cuò)以實(shí)際的離散譯介行為詮釋了自己的文學(xué)譯介理念:翻譯出版詩(shī)人個(gè)人詩(shī)集,與世界文學(xué)匯通交流。5位現(xiàn)代詩(shī)人譯集均入選了美國(guó)日月出版社知名詩(shī)文叢書Green Integer(《綠的合集》)⑤。《綠的合集》收錄5位現(xiàn)代詩(shī)人譯集,意味著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人在世界詩(shī)壇上集體發(fā)聲。譯集照顧目的語(yǔ)讀者的閱讀習(xí)慣,以詩(shī)人黑白照片為封面,裝幀風(fēng)格類似20世紀(jì)六七十年代在北美風(fēng)行的《新導(dǎo)向叢書》,因而能和諧融入《綠的合集》叢書,順利與世界文學(xué)接軌,是“可以成功而引起世界巨大反應(yīng)的”[15]63。
張錯(cuò)的自譯行為強(qiáng)調(diào)自身的離散經(jīng)驗(yàn)。張錯(cuò)將《漂泊者》中大部分詩(shī)作及少量早年詩(shī)作自譯為英語(yǔ),結(jié)集成詩(shī)集Drifting出版。張錯(cuò)坦言,選擇這些詩(shī)作的原因是:“Nevertheless,these poems represent a journey of my drifting,and someone else perhaps,physically and mentally.” “For many years have I longed for a home and a nation,and after many years,I find myself still searching.” “I yearn for a dwelling of the body and mind where the spirit burgeons.”⑥[10]11-12
早年詩(shī)作和《漂泊者》展現(xiàn)離散的人生旅程,呈現(xiàn)身體和精神的離散狀態(tài)。多年來(lái)的家國(guó)追尋、身心安定之所的找尋,無(wú)疑為張錯(cuò)的離散書寫和離散譯介打上了“漂泊”的印記。
四、離散書寫與離散譯介:相融互生、一枝二花
連接離散書寫和離散譯介的紐帶是什么??jī)烧哧P(guān)系如何?饒芃子在探討離散作家的文化混融性時(shí)認(rèn)為:“華族文化的‘根性’,并非凝固、靜止的,而常常會(huì)形成文化認(rèn)同的‘變異體’。”[5]195離散主體不是被動(dòng)接受多元文化的影響,離散書寫、離散譯介和文化認(rèn)同是在混融的多元文化環(huán)境中創(chuàng)造、再生的結(jié)果。“一個(gè)人只有首先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或通過(guò)自我建構(gòu),方能在文學(xué)世界中發(fā)出屬于自己的聲音。”[11]20離散書寫是如此,離散譯介更是如此,兩種行為的核心要素是離散主體的文化身份構(gòu)建。
塞繆爾·亨廷頓區(qū)分了身份來(lái)源的六大因素,即歸屬性、文化性、疆域性、政治性、經(jīng)濟(jì)性和社會(huì)性[16]21。文化身份中的自然屬性,如地域、血緣、性別、年齡等是相對(duì)穩(wěn)定的因素;而社會(huì)文化性因素,如民族、部落、語(yǔ)言、國(guó)籍、宗教、生活方式等是動(dòng)態(tài)性因素。離散書寫和離散譯介是離散主體的敘述認(rèn)同行為。離散主體的文化身份是母語(yǔ)文化與居留地文化的矛盾融合體,兩者相互滲透,處于動(dòng)態(tài)平衡構(gòu)建中。離散主體的文化身份構(gòu)建具有雜糅性、復(fù)雜性和動(dòng)態(tài)性特征。面對(duì)母國(guó)文化與居留地文化兩個(gè)既定中心時(shí),離散主體的文化邊緣性是雙重的,而雙重邊緣性(或雙重彼岸)正是離散書寫(或文化翻譯)的產(chǎn)生緣由,產(chǎn)生文化對(duì)話的第三文化空間,甚至在第三文化空間重構(gòu)一個(gè)全新的“中心”。離散主體“居住于一個(gè)‘文化之間的’世界中,于矛盾、沖突的傳統(tǒng)中創(chuàng)造、協(xié)商著自己的文化認(rèn)同,他們同時(shí)‘既是此又是彼’,或者‘既非此又非彼’”[17]51。文化對(duì)話意義上,離散主體的他鄉(xiāng)即故鄉(xiāng),邊緣即中心。以張錯(cuò)為例,離散書寫是離散主體化解身份焦慮的方式,亦是構(gòu)建家國(guó)想象、滿足文化尋根精神需求的行為;而離散譯介是離散書寫水到渠成的行為,是文化翻譯的必然結(jié)果。張錯(cuò)多年的詩(shī)文創(chuàng)作、學(xué)術(shù)鉆研、文化對(duì)話行為無(wú)疑為離散譯介奠定了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他多年堅(jiān)持在海外以母語(yǔ)創(chuàng)作,這是其母語(yǔ)文化自覺(jué)意識(shí)的表現(xiàn),而其離散譯介,是文化對(duì)話深化的必然結(jié)果。
張錯(cuò)的文化身份既包括語(yǔ)言性身份,也包括社會(huì)性身份。就語(yǔ)言性身份而言,首先,張錯(cuò)是華語(yǔ)詩(shī)人。張錯(cuò)認(rèn)為自己最重要的語(yǔ)言性身份是詩(shī)人:“創(chuàng)作使我超越了自己的學(xué)者身份,其實(shí)在研究里我也有很自豪的一面,可是我更愿意做一個(gè)詩(shī)人”,“ 我一直在堅(jiān)持,在這個(gè)創(chuàng)作的世界里從沒(méi)有停止過(guò)”[9]55。在面對(duì)學(xué)者型詩(shī)人和詩(shī)人型學(xué)者的身份選擇時(shí),張錯(cuò)坦言會(huì)選擇詩(shī)人:“這是我一生的抉擇,也是我一生的志業(yè),這個(gè)東西是不可磨滅的,隱隱之中我感覺(jué)到它是一種召喚。”[9]56其次,張錯(cuò)也是文學(xué)批評(píng)和比較文學(xué)學(xué)者。在《批評(píng)的約會(huì)》中,張錯(cuò)關(guān)于詩(shī)歌批評(píng)的文章是全集的重要組成部分。他還編著了現(xiàn)代詩(shī)選集《千曲之島》,對(duì)眷村文學(xué)和新小說(shuō)與五四運(yùn)動(dòng)有獨(dú)到見(jiàn)解。張錯(cuò)的離散經(jīng)驗(yàn)是他文學(xué)批評(píng)研究的亮點(diǎn)。他將詩(shī)歌創(chuàng)作、翻譯、批評(píng)融為一體,同時(shí)進(jìn)行離散書寫與離散譯介,是現(xiàn)代文學(xué)界不可多得的學(xué)者型詩(shī)人。
經(jīng)歷多年的離散體驗(yàn)后,張錯(cuò)的社會(huì)性身份從外在被動(dòng)的政治離散者漸漸轉(zhuǎn)變?yōu)閮?nèi)在主動(dòng)的文化放逐者。20世紀(jì)中期,張錯(cuò)與家人不得不先后在廣州、香港、澳門等地經(jīng)歷放逐,成為華族離散者。20世紀(jì)80年代后,地理空間上的回歸已不是難題,但詩(shī)人仍在精神空間尋找身心最適切的文化居留地。他理想中的文化居留地也許是大陸,也許是臺(tái)灣,也許是北美,也許三者均不是,也許三者都是。社會(huì)性身份的模糊性和動(dòng)態(tài)性是離散主體離散書寫和離散譯介的創(chuàng)作之源,更是離散書寫和離散譯介的主要內(nèi)容。張錯(cuò)對(duì)自我文化身份認(rèn)知有濃厚的追問(wèn)意識(shí)。在自譯選集Drifting的序言中,他談到:
“Many years later,I realized that I had become an American writing in Chinese.I live in America but I have published more than thirty books in Taiwan,Hong Kong,and China.Sometimes I ponder on whether am I a Chinese poet,an Asian American writer,both,or none of the above?”⑦[10]10
正是對(duì)自我文化身份的追問(wèn),對(duì)家國(guó)文化的追尋,對(duì)身心合一安定之所的尋覓,促使張錯(cuò)不斷地以離散書寫和離散譯介重構(gòu)家國(guó)形象,不斷構(gòu)建文化身份,在中文或英文的字里行間找尋精神空間。與其他離散主體的“葉落歸根”式文化訴求不同的是,張錯(cuò)的離散書寫和離散譯介均呈現(xiàn)出“落地生根”的文化取向。
張錯(cuò)在離散書寫中以漂泊為母題,以漢語(yǔ)為創(chuàng)作語(yǔ)言,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文化自覺(jué)意識(shí);在離散譯介中,張錯(cuò)堅(jiān)持為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壇發(fā)聲,努力向世界推介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壇的優(yōu)秀作品,為現(xiàn)代中國(guó)詩(shī)歌被世界文學(xué)認(rèn)可、接受做出貢獻(xiàn)。離散主體的文化身份作為離散主體行為的根源性因素,在建構(gòu)中統(tǒng)攝了離散書寫和離散譯介的行為模式和文化取向。離散書寫和離散譯介是離散主體文化身份一致下的創(chuàng)作與譯介行為,兩種行為一枝二花,同根同源,呈現(xiàn)出相融互生的面貌。
五、結(jié)語(yǔ)
考察離散主體的離散書寫和離散譯介,不難發(fā)現(xiàn),離散主體的離散書寫和離散譯介行為是一枝二花,同根同源,呈現(xiàn)出互生互動(dòng)、相融相濟(jì)的面貌。在離散書寫和離散譯介中,離散主體擺脫了離散族群的“雙重邊緣”,進(jìn)行文化交流新“中心”的嘗試。作為離散作家和離散譯者的典型代表,張錯(cuò)的離散書寫和離散譯介具有同源相融關(guān)系。張錯(cuò)的個(gè)案研究,對(duì)比較文學(xué)、海外華裔文學(xué)跨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jià)值,同時(shí)也對(duì)中國(guó)文化“走出去”的傳播與譯介模式具有借鑒意義。
注釋:
①簡(jiǎn)文志:《存在形式的荒謬性——痖弦詩(shī)歌探析》,《詩(shī)探索》,2004年Z2期,第134-154頁(yè)。
②孫藝?guó)P:《離散譯者的文化使命》,《中國(guó)翻譯》,2006年第1期,第3-10頁(yè)。
③英文引文的中譯文為筆者所譯,下同。“1967年,作為英語(yǔ)專業(yè)研究生,我第一次來(lái)到美國(guó)。到美國(guó)之前,23歲的我,已出版了兩卷中文詩(shī)集和一本散文集。用英文寫詩(shī)一直讓我沉醉于世界精神,這是我的美國(guó)夢(mèng),好成為大熔爐中的一分子。但我很快發(fā)現(xiàn),語(yǔ)言的精準(zhǔn)、詩(shī)歌表達(dá)的主張,比固守民族身份更重要。很快,我又以中文為主要?jiǎng)?chuàng)作語(yǔ)言了。”
④“上述名單中的詩(shī)人代表了過(guò)去20年中,在臺(tái)灣為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歌的構(gòu)成發(fā)揮積極作用的兩代詩(shī)人。”
⑤《綠的合集》是日月出版社最負(fù)盛名的叢書之一。目前該叢書已出版詩(shī)文集100余冊(cè),包括馬克吐溫、喬伊斯、王爾德等大家作品,在美國(guó)知名度較高。
⑥“然而,這些詩(shī),代表著我的漂泊旅程,或許還有其他,身體的或精神的。”“多年來(lái),我一直渴望一個(gè)家,一個(gè)國(guó),但多年后,發(fā)覺(jué)自己仍然在尋找。”“我盼望有個(gè)身心的居所,那里,可容精神萌發(fā)。”
⑦“多年后,我意識(shí)到自己成為用中文寫作的美國(guó)人。我住在美國(guó),但在臺(tái)灣、香港和大陸出版了30多本書。有時(shí),我也思量,我到底是中國(guó)詩(shī)人、亞裔美國(guó)作家,還是兩者都是,還是三者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