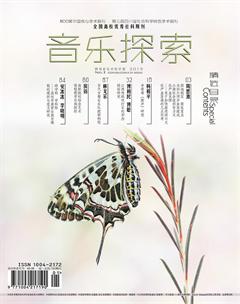基于《經典詠流傳》的古詩詞流行歌曲傳承研究
摘 要:《經典詠流傳》立足中國傳統文化,和詩以歌,運用大眾媒體語言對古詩詞、流行音樂等進行“編碼”和創新詮釋,講述文化知識、闡釋人文價值、解讀思想觀念,具有鮮明獨特的審美特征。該節目為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提供了新路徑,有助于對現代文明追本溯源,樹立文化自信。
關鍵詞: 《經典詠流傳》;古詩詞歌曲;文化傳承
中圖分類號:J6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 - 2172(2019)01 - 0072 - 04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19.01.009
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挖掘中華傳統文化要結合時代理念讓其流傳下去。“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詩韻。”詩詞伴隨著中華歷史文明的發展,從早期的民間歌謠到漢代樂府詩,再到唐詩宋詞,至近代以來的白話詩、現代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詩言志,歌詠言”,詩詞本入樂,古人和詩以歌,與詠(吟)唱相得益彰,那么今人應如何創新“音樂文學”模式,讓詩詞在當代散發魅力引領青年受眾傳承文化經典?
一
在古代,《詩經》 《楚辭》、漢魏六朝樂府詩、唐詩、宋詞都是合樂之詩。詩詞以樂傳詞、以文化樂,兼具音樂與文學特性。《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楚辭》收錄戰國時期楚地流行的音樂。漢樂府的職責是采集、改編民間歌謠。《文心雕龍·樂府》載:“故知詩為樂心,聲為樂體。”唐詩入樂,如《陽關三疊》《送元二使安西》《菩薩蠻》等。宋代更是有姜夔自度曲傳世。在中國古代音樂史上,詞樂是一種藝術歌曲體裁,由“曲”(音樂上的音聲)與“詞”(文學上的文詞)兩方面構成。音樂創作方式主要有倚聲填詞和依曲填詞。從音樂角度論,詞樂是“詞調音樂”,或按古代稱謂“曲子詞” “歌曲” “曲子”;從文學視野說,詞樂是合樂的歌詞,或謂“詞”。后世有詞無樂的“詞”不再具有原來“樂”的意義,早已“蛻變”為一種純粹的文學創作形式。
近代以來,古詩詞歌曲是“向西方學習”的產物。中國傳統音樂與西方音樂創作技法相互吸收、互相參照,創造性地發展了自身,代表作品有青主的《大江東去》、黃自的《花非花》《南鄉子》、江文也的《春曉》、譚小麟的《正氣歌》《江夜》、冼星海的《古詩十首》等。1949年以后,李劫夫、田豐、羅斌等將毛澤東詩詞進行譜曲,如《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卜算子·詠梅》等。改革開放以后,古詩詞歌曲有了創作和傳播的新途徑——影視音樂作品,如歷史題材電視劇《三國演義》的《滾滾長江東逝水》、《紅樓夢》的《枉凝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流行音樂領域,最早對古詩詞進行譜曲演唱的是鄧麗君,如《獨上西樓》《但愿人長久》等。另外,瓊瑤在其電視劇主題曲或插曲中,采取移花接木等手法對詩詞作了局部調整,如《在水一方》《幾度夕陽紅》等。
近年來,國家不斷強調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中共中央國務院辦公廳在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中指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點任務之一是滋養文藝創作,要善于從中華文化資源寶庫中提煉題材、獲取靈感、汲取養分,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益思想、藝術價值與時代特點和要求相結合,運用豐富多樣的藝術形式進行當代表達,推出一大批底蘊深厚、涵育人心的優秀文藝作品。”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新時代文化建設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要把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提煉出來、展示出來,把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文化精髓提煉出來、展示出來。” ① 這些精神為文藝工作者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也對從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兩年,《朗讀者》《見字如面》《國家寶藏》《中國詩詞大會》等節目在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具有較好的引領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經典詠流傳》節目以“歌詠”方式,將古詩詞與現代流行音樂相結合,用現代音樂“激活”傳統文化,聯動大眾主流媒體力量推動了古詩詞的當代傳播。
二
《經典詠流傳》節目共11期,前后有57首不同音樂形式的古詩詞歌曲呈現在舞臺上。該節目音樂形式豐富,有原創音樂作品如《定風波》《聲律啟蒙》等,有經典影視歌曲《枉凝眉》《滾滾長江東逝水》等老歌新唱,有《三字經》等說唱歌曲,有《將進酒》等搖滾樂。歌者各具特色, 有“90后”王俊凱演唱《明日歌》,有中國第一代鋼琴演奏家巫漪麗彈奏《梁祝》,有臺灣原住民歌手胡德夫根據古歌謠改編的《來甦·秋思》,還有香港演員汪明荃、羅家英的《鵲橋仙》等。節目將朗誦、傳唱與解讀結合,以現代人喜聞樂見的方式推廣優秀中華文化。內容上,節目中詩詞大范圍引用中小學課本中的古詩詞;音樂創作上,以尊重詩詞韻律為前提,融入現代音樂形式。如《將進酒》結合搖滾樂展現李白的豪邁之氣;《關雎》以仄聲結尾,采用印尼民歌《哎呦,媽媽》進行配樂;《別君嘆》融入20世紀初學堂樂歌時期《送別》與多民族樂器。同時,也有傳統樂器的加入,如在曹軒賓演唱的《別君嘆》中,趙家珍用南宋古琴現場彈奏琴曲《流水》;龔琳娜演唱的《上下求索》中展示了編鐘;趙照演唱的《聲律啟蒙》旋律采用五聲調式,并加入古人吟詩作對的語氣腔調,配合吉他彈唱所演奏的傳統樂器有琵琶、笛子、古琴、木魚、尺八等。
從傳播學的視角看,媒介具有傳承文化、教育民眾的功能。《經典詠流傳》切合時代背景,把握媒介社會功能,依托音樂、文學、歷史等學科的文化資源,以版塊化的傳播形式構建價值體系,以“詩”“歌”講述現代“中國故事”,為傳統文化賦予時代內涵,體現出“以詩傳情”“文化傳承”“文化新詮釋”等主題。詩為歌創作,歌為詩傳播,彰顯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實現文化化人之作用。另外,有些歌曲在創作過程中融入了戲曲元素。如譚維維演唱的《墨梅》融入了戲歌,也加入了琵琶、古箏等傳統樂器,在唱腔上采用了藏族哭腔、苗族水腔、陜西的秦腔和老腔的唱法;在現場,還有中國鼓與古風古意的舞蹈助陣。因此,在傳統音樂傳承人青黃不接的當下,《經典詠流傳》節目對于推廣傳統音樂文化、傳唱戲曲經典唱段方面具有引領性作用。
在藝術結構方面,中國藝術結構的特質體現在布局與韻律方面;從構思到具化,主要以動態的布局完成構制運營,在語言結構中以隱含情思內容為旨歸。以優美、柔韌而具時空綿延的張力,情與文統一立意,意象(隱性的)與言象(顯性的)交融整合,內外兼涉構思辯證,審美愉悅與生命意趣結合驅動機制,從而形成空靈婉曲的美學風貌。主導風格空靈飄逸以形而上內涵呈現,結構上給予立體化處理,審美韻律體現于作品情感、主體、意趣、意蘊、格調、情味等內在追求,即由意象到言象的動態整合過程。由言象進入到意象,透過可感、可把捉的音樂節奏、聲響等存在,從而把握住它的存在規律。從這個意義上說,《經典詠流傳》節目中“主持人朗誦詩詞——詩詞歌曲演唱——傳唱人及嘉賓講述歌曲創作背景、時代意義——鑒賞嘉賓團鑒賞時刻”模式不單是詩歌、音樂、舞蹈、戲劇、戲曲的融合,還積極調動了聲光電整體設計的造型藝術、舞臺屏幕中的影像藝術,高科技的虛擬歌手(智能機器人)也登上舞臺。節目所呈現的表演形式既是外在媒介對運作格局的示現,又是物質媒介對布局機制的協合與歸依,也是內在思維運動的呈現,更是審美主體創造智慧的積極顯現,呈現空靈絕妙之境。
從美學的視閾論,首先,在審美感知方面,《經典詠流傳》在同一時空中呈現出詩、樂、舞、光、戲、色等的完美結合,對觀者產生強烈的審美沖擊,使其形成對古詩詞的全新審美感知。其次,受眾通過視聽結合的方式,在直面具體可感的對象時,激發審美想象,深入到作品的背后去探尋古詩詞作品蘊涵的哲理。如受眾在《明日歌》中理解惜時如金的深刻道理,激發對未來的憧憬與思考,傳遞好好學習、珍惜時光的價值觀;在《墨梅》中感受梅花的高潔傲骨;在《苔》中領悟新時代鄉村教師的堅韌、守望與無私奉獻……進而產生感性與理性相互融合的精神道德體驗。最后,在審美體驗方面,受眾對音樂形象產生想象、聯覺。如在《離騷·上下求索》古老編鐘聲中宛見春秋時代禮樂之高雅,在《定風波》紛飛的竹葉背景中猶有穿林打葉聲之感,在《鵲橋仙》《秋思》等情感故事的訴說中產生心靈共鳴。節目內容選擇和創意表達頗具匠心,是對繁衍生息、生存蛻變、和諧相處的藝術總結;將情感與哲理相互交融,使觀者感受現場演繹的熱辣滾燙情感,感知隱匿的理性思考的生存哲學,從而產生強大的審美效應(磁場)。節目所應承擔的主要社會責任及其所應遵循的由自然人向社會人過渡的基本法則,在情理呼應和激蕩中升華出人生況味與美感,彰顯出人之為人的基本道德倫理規范,有一種蕩氣回腸與回味無窮的審美效應,為優質文化的正道而行、弘揚正氣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探索和模式,發揮出藝術養心和澡雪精神的作用。
“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文化是一條河流,唯有創新才能柳暗花明、枯木逢春。就今天而言,文化創新當為全球化背景下個體的文化迷失、焦慮及失根提供答案,為匡正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服務,為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貢獻,為解決文化發展中的不平衡尋求良方。從這個意義上說,《經典詠流傳》節目最大的成功便是敢于創新。“經典演繹——背后的故事挖掘——現代審美價值闡述” “三位一體”的結合方式創造性地實現了形式與內容的有機統一。可以說,這種創新打開了文化傳承與創新的想象空間,是“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① 的探路先鋒,開拓了新時代民族文化復興的新路徑。
三
在中國傳統美學中,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無言之美是非知識的生命體驗,更是無功利的生命境界。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經典詠流傳》的美是一種無言的大美。它更加契合中國古典藝術理論“可以心契,不可言宣”的原則,盡量避免語言的使用。點評嘉賓的評語精練簡潔,對經典傳唱人沒有過多介紹,有時甚至一段典故、一段人生經歷便取代了詩詞的評點。將舞臺和時間都給了音樂與詩詞,讓觀眾得以細品慢嚼,開啟一段對美的朝圣之旅。
詩詞的審美之路是一條純粹體驗的道路,這是一種內在的冥合。詩詞中所蘊含的詩人對生命的覺解需要受眾用審美的眼光去觀照,用音樂和畫面營造意境,激發審美情感,在作品意境中體會傳統文化之美。詩詞之美在意境,即人在認識世界萬物之前早已沉浸在他所活動的世界萬物之中,早已與世界萬物融合在一起。人們在塵世尋求“登高”式的超越,以超越自身,達到“萬物一體”的境界。詩人與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達到“天人合一”境界。登高懷遠,“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就是“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或無意或有意,首期《經典詠流傳》節目推出極富體現“萬物一體”境界的哲學內涵與美學韻味的詩詞《登鸛雀樓》,可謂是絕妙的安排。聆聽來自祖國各地7所中小學的學生吟唱《登鸛雀樓》時,歷史在剎那間生動起來,仿佛進入一種超越于現實之外的“靈境”,時間如滴水成冰般凝結,生命綿綿不絕;可聽見古人之“曲水流觴,橫槊賦詩”,亦可聽見今人飽含深情的吟唱。人追求神圣,精神是人類生活的意義所在。東方的神圣性源于“美”。美是對主客二分的超越,是對“物”的實體性的超越,更是對自我有限性的超越,“因而照亮了一個本然的生活世界回到萬物一體的境域,這是對人生家園的復歸,是對自由的復歸” ②。因此,美對個體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文化便以這樣的方式延續,傳承久遠,是與生命的偉力相伴相生的創造力,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從這個意義上論,《經典詠流傳》以古詩詞“和詩以歌”開始,挖掘中國古詩詞背后的精神內涵。總結其在文化傳承過程中所體現的獨具中國特色的審美特征,闡釋凝聚于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人文價值,促進現代社會的融合發展,探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創新性轉化發展過程中的基本路徑,對于追溯現代文明的東方淵源,傳遞中國好聲音、弘揚民族精神,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詩詞創新,古來有之。南北朝徐陵有詩“江陵有舊曲,洛下作新聲”,王昌齡則說“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唐代張嵩寫道“新聲巧妙今古傳”。文以載道,歌以詠志,“詩詞唱經典,中國正流行”,以歌動人、以情感人、以事引人,共享盛世文化的洗禮。《經典詠流傳》讓經典具有時代感,讓中華瑰寶“活”起來,通過現代人的事跡閃耀新時代的光輝,產生新的先鋒文化,煥發出蓬勃的生命力。
◎ 本篇責任編輯 錢芳
收稿日期: 2018-07-13
作者簡介:王滔(1976— ),男,碩士,浙江音樂學院流行音樂系講師(浙江杭州 31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