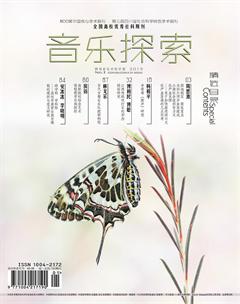當代古蜀樂樂隊建制構想
摘 要: 四川歷來為我國西南地區音樂文化重鎮,從古代不同時期的音樂圖像、考古出土的樂器遺物中,都展現出古蜀音樂文化豐富多樣的面貌。作為當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構成部分,古蜀之樂一直就為學界所重視。從傳承保護與創新發展的角度出發,從古蜀樂賴以生存的樂器入手,梳理古蜀樂器,并參考大量民族管弦樂隊建制方案,提出當代古蜀樂隊的基本建制規劃,可為古蜀樂從理論研究邁向表演實踐提供必要而可行的方案。
關鍵詞:樂器學;古蜀樂隊;樂隊建制;民樂創新
中圖分類號: J628? ? ? ? ?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 - 2172(2019)01 - 0067 - 05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19.01.008
引言
“? ? ?之為國,造于人皇”。蜀,是古代先民對四川盆地為核心的廣大地域的總稱,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從地理位置上看,其東鄰重慶市,南接貴州、云南,西毗西藏,北達青海,自古以來就是西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核心區域。歷史上,先后有多個獨立政權在這一地區建立,而蜀的名稱就來自于先秦時期在該地區建立的獨立政權蜀國。北宋時期該地區設置四路,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以及夔州路,簡稱“四川路”,元代合并四路,設四川省,并沿用至今。
蜀地歷史悠久,特殊的地理環境孕育出多彩燦爛的文化。除漢族之外,在該區域生活的主要還有藏族、羌族、彝族與回族,并在地理分布上形成川西甘孜藏族聚居區,川西北阿壩藏羌聚居區以及川南涼山彝族聚居區。而上述三個少數民族聚居區則與藏東、滇西北地區一起,以橫斷山脈的特殊高山峽谷地理特征構成了一條自北向南的“歷史—民族”地理文化通道——藏彝走廊。 ① 從出土的歷代文物看,蜀地兼具中原漢族文化圈與西南、西北少數民族文化圈的特點。以距今2800多年前的著名古蜀文化遺址三星堆為代表,其出土的大量器物已表明古蜀地區是我國長江文明的發源地,亦是華夏禮儀制度在上古西南地區的傳承再現。② 而正是在這樣一種特殊地理自然環境與人文傳統的基礎上,蜀地的先民創造了鮮活動人、多姿多彩的音樂文化。從先秦的金石之樂,到兩漢的琴歌合鳴;從隋唐盛世的大型器樂合奏,再到明清以來的川劇高腔,古蜀地區有著一以貫之的漢族音樂文化傳統。除此之外尚有康巴藏族、羌族以及涼山彝族民間音樂傳統,四個不同族群的音樂傳統共同構成蜀地多樣性的音樂文化景觀。
音樂的重要載體是樂器,人類通過演奏不同的樂器來抒發、表達、交流感情,每一種音樂文化都有較為固定與特殊的樂器種類構成完整的操作系統。而今天,對古蜀音樂的發掘整理,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當代發展都迫切地需要建立這樣一套樂隊體系,這一體系不僅能夠為傳統古蜀音樂的完美呈現奠定物質基礎,同時也能夠容納當代古蜀音樂的創新發展。可以說,當代古蜀樂樂隊體系的建制應體現出傳承性與開放性的特征。傳承性即是需要深入了解古蜀音樂以往的樂器構成體系,開放性即是需要主動與當代世界音樂潮流接軌,借鑒其它音樂文化中優秀的一面為我所用。
一、當代古蜀樂隊之樂器來源
總地說來,無論從傳世樂器還是出土樂器文物,或是出土音樂圖像來看,古蜀樂器類型都非常豐富,時間跨度從先秦時期直到晚清年間,吹、拉、彈、打四類樂器齊備,制作樂器的材料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
以中國先秦時期定型的樂器“八音分類法” ① 來看,古蜀地區的“金”類樂器包括大量先秦時期的青銅樂器,如鐘、鎛、鉦、鐸以及錞于。這些青銅樂器構成了先秦時期古蜀“金石之樂”樂隊建制的主體部分。大多數“金”類樂器則一直流傳至今,如各種形制的銅鼓、鐃鈸、鑼,以及代表蜀地特色的川鑼,各種形制的嗩吶等。另外,“金”類樂器還有藏傳佛教密宗的金剛薩埵鈴、銅質低音樂器筒欽,羌族骨柄鈴、彝族畢摩鈴等。“絲”類樂器包括大量傳世的彈撥樂器,如箜篌、箏、琴、琵琶、阮、三弦等,同時還有瑟、筑等古代彈撥樂器;而川劇高腔中使用的主奏樂器板胡以及其他胡琴類家族在古蜀音樂中亦是常見的拉弦樂器。另外還有康巴藏族的牛角胡、札木聶;涼山彝族的月琴、三弦等。“竹”類樂器包括各種形制的笛、排簫、洞簫以及篳篥(今管子)、胡笳等古代樂器,涼山彝族特色樂器口弦亦是由竹篾制作。“土”類樂器有陶塤、陶鈴,以沙錘為代表的各種搖響器。“匏”類樂器主要以笙、竽為代表,除漢族傳統笙外,涼山彝族還有葫蘆笙。“革”類樂器主要為各種形制的鼓,包括漢族傳統的大鼓、堂鼓、排鼓、腰鼓、手鼓、建鼓、答臘鼓、羯鼓;康巴藏族的鼗(táo)鼓(達瑪如、撥浪鼓)、熱巴鼓;羌族羊皮鼓;彝族八角鼓等。“木”類樂器包括敔(yú)、拍板、板鼓、木葉、木魚,以及涼山彝族打擊樂器煙盒等。
由此看來,古蜀樂樂器類型多樣,樂器種類豐富,并共同構成了一個龐大的樂器寶庫。這些來自于不同族群,有著不同音響效果的樂器為今天復興古蜀樂,構建其樂隊體系提供了重要物質保證。面對古蜀樂復興、古蜀樂樂隊體系的建構不僅需要深入把握這一樂器寶庫,還需要充分掌握古蜀樂傳統的樂器展現與組合形式。
從古蜀地區出土或留存的大量音樂圖像資料來看,依據樂器的多寡可分為三種不同類型的樂器展現與組合形式。首先是樂器獨奏,獨奏是我國傳統民間音樂的常見形式。早在東漢時期巴蜀地區就出現了大量樂器獨奏的音樂圖像,如成都吹竽畫像磚、雅安高頤闕師曠鼓琴畫像石。在東漢時期的郫縣百戲畫像石《東海黃公》中可見,樂器獨奏為瑟,而同時還存在大量舞蹈、雜技、戲劇表演演員做著千姿百態的肢體動作。
其次是小型器樂合奏,大多為2~5件樂器的組合演奏。如彭山神獸奏樂畫像磚形象地描繪了吹奏樂器笙與彈撥樂器琴相互組合的形式;在成都羊子山鼓吹畫像磚中則出現了東漢時期代表性的鼓吹樂——騎吹,四位軍人騎于戰馬之上演奏著鐃、建鼓、排簫、琵琶四件樂器,由此構成了打擊樂器、吹奏樂器與彈撥樂器組合的形式;而在彭縣樂舞畫像磚中,在笛子、琵琶的合奏下中間的舞者揮舞著長袖翩翩起舞。
最后是大型器樂合奏,古蜀樂中的大型器樂合奏最早出現在先秦戰國時期成都宴樂武舞圖銅壺的紋飾中,在這一紋飾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編鐘、編磬、建鼓、丁寧、笙、排簫6件樂器的組合,這是先秦大型樂舞的典型樂隊建制形式;而在前蜀王建墓樂舞石刻中,則出現了更為龐大、組合完備的古蜀樂隊,這支樂隊共由21件樂器構成,包括打擊樂器和鼓、毛員鼓、正鼓、齊鼓、羯鼓、答臘鼓、雞簍鼓、鞉牢、銅鈸、拍板;吹奏樂器箎(chí)、排簫(2件)、篳篥、笛、笙、貝、木葉,以及彈撥樂器琵琶、箜篌、箏,其代表了古蜀地區隋唐時期歌舞伎樂的典型樂隊建制。
與此相類似的還有五代時期樂至報國寺伎樂摩崖石刻其兩組樂隊共計17件樂器。第一組樂隊樂器為手鼓、羯鼓、拍板、箜篌、琵琶、箏、篳篥、排簫;第二組樂隊樂器為杖鼓、羯鼓、拍板、箜篌、琵琶、箏、笙、排簫、篳篥。
二、當代古蜀樂隊的基本建制
總地看來,古蜀樂樂器傳統組合形式豐富多彩,其中吹奏樂器笛、管子;彈撥樂器琵琶、箜篌;打擊樂器鼓、鐃鈸等占據了重要的地位。當代古蜀樂樂隊體系的建制,正是在充分了解上述古蜀樂傳統樂器組合形式的基礎上,以我國民族管弦樂隊體系為基礎來進一步建立與完善。近幾十年來,我國廣泛使用的民族樂隊建制以演奏方式為標準分為“吹、拉、彈、打”四個部分,即吹奏樂器、拉弦樂器、彈撥樂器與打擊樂器。吹奏樂器主要包括笛子、簫、笙、嗩吶四類樂器,其中每一類樂器又因音域的差異而細分。拉弦樂器主要以胡琴家族為主,而為了填補中國民族拉弦樂器中缺少低音的空白,還改良加入了大提琴、低音大提琴等西方樂器。彈撥樂器包括箏、箜篌、琵琶、揚琴、月琴、古琴等。而打擊樂器分為有音高打擊樂器,如云鑼、排鼓、編鐘、編磬、改良定音鼓等,以及無音高打擊樂器,包括各種形制的鼓、鈸、鑼、鈴、梆子、拍板等。① 當代古蜀樂樂隊建制的基本分類依舊按上述四種基本演奏法進行分類。
在此基礎上,根據古蜀地區的樂器組合特色增減各組中的樂器,由此突出古蜀地區不同歷史時期的樂器組合形式,并兼顧到古蜀樂多族群同榮的音響文化內涵。首先,打擊樂器是古蜀樂樂隊建制中的主體。古蜀樂樂隊的打擊樂器可以具體分為三組,即固定音高的打擊樂器、相對音高的打擊樂器、無音高的打擊樂器。固定音高的打擊樂器包括編鐘、編磬、云鑼、民族定音鼓、排鼓等;相對音高的打擊樂器包括方響、木魚;無音高的打擊樂器包括了各種形制的鼓、鐃鈸以及鈴、梆子。其中還包括川劇鑼,藏族打擊樂器達瑪如、金剛薩埵鈴,彝族打擊樂器煙盒、畢摩鈴等。其次,吹奏樂器除了我國民族樂隊中固定常用的笛、笙、嗩吶三類樂器外,古蜀樂樂隊中的吹奏樂器還應包括排簫、管子、筒欽、貝號、木葉等,其中排簫、管子可以說是古蜀樂樂隊吹奏樂器中必不可少的樂器。再次,彈撥樂器應包括琵琶、大阮、中阮、三弦、揚琴、箏、古琴、箜篌、月琴、柳琴等。最后,拉弦樂器應包括京胡、高胡、二胡、板胡、中胡、大胡、牛角胡(弦子)等胡琴類樂器以及民族大提琴、民族低音大提琴等改良西方樂器。
上述每一組樂器都完整囊括了現代民族管弦樂隊的常用音域,而其中各個組別中都有不同于一般的民族管弦樂隊的特殊音色,在打擊樂器中,川鑼、達瑪如、煙盒、畢摩鈴等樂器都有著異于一般打擊樂器的特殊音效;而在吹奏樂器中,排簫悠遠的音色特點是古蜀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而藏族低音樂器筒欽為特殊音樂形象的描繪提供了特殊的音效。同樣,在拉弦樂器中康巴藏族的牛角胡特有的顫音演奏技法亦是古蜀樂的代表性音色;而在彈撥樂器中,箜篌、琵琶、古琴則有著重要的地位。盡管在我國一般的民族管弦樂隊中也有這三件樂器的存在,但在演奏技巧與音色控制上卻凸顯出古蜀樂特有的音色變化特點。
進一步,在“吹、拉、彈、打”四大組別的樂器分類基礎上,古蜀樂樂隊有三種基本編制形式,即小型古蜀樂隊、中型古蜀樂隊、大型古蜀樂隊。每一種編制都有一些固定的樂器組合,同時也有一些樂器可依據音樂表現內容來增添。
具體看來,小型古蜀樂隊,是古蜀樂的基本樂隊建制形式,也可以說是古蜀樂室內樂化的具體形式。一般由2~9件不同固定音高的古蜀樂器與1~3位古蜀打擊樂器操作者構成。在這一建制的古蜀樂樂隊中,其強調的是每一件樂器獨特的音色魅力、以及多件不同樂器之間的組合。其中雖然打擊樂器并不限定其具體的件數,但需將其可操作性控制在3位演奏者之內。因此,小型古蜀樂隊最大編制為12位演奏者,全編制的小型古蜀樂隊樂器組合為吹奏樂器笛、排簫、笙(或嗩吶);彈撥樂器箜篌、琵琶、三弦(或大阮);拉弦樂器高胡、二胡(或板胡)、低音大提琴(或大胡);固定音高打擊樂器云鑼;非固定音高打擊樂器鼓、鐃鈸等。所有固定音高樂器,在演奏者可操作的前提下,可更換同類樂器家族中不同音域的變種樂器。如笛子演奏者可根據需要選擇演奏曲笛、梆笛、羌笛等不同笛類家族變種樂器。非全編制的小型古蜀樂隊可根據需要取舍其中的各件樂器組成。
如果說,小型古蜀樂隊更多表現出現代室內樂樂隊建制的特征,那么中型古蜀樂隊與大型古蜀樂隊則更多體現出古蜀樂樂隊建制現代“交響化”的特色。兩種樂隊在樂器使用上并無太大差別。主要差別體現在人員編制與樂器數量上。中型古蜀樂隊大致為40~60人左右,而大型古蜀樂隊則為80~100人左右,其具體編制范例如表1所示。一個完整的古蜀樂交響樂隊,不僅“吹、拉、彈、打”四類樂器齊備,同時每一類樂器都構成完整的高、中、底三個音區,在吹奏樂器中,笙、嗩吶樂器家族亦構成三個音區的樂器劃分。而依照上述編制范例,古蜀樂的總譜編寫亦呈現出相同式樣。
古蜀樂隊的舞臺空間具體呈現為,舞臺左側前1~5排為高胡、板胡、二胡、京胡(弦子);舞臺右側前1~5排為中胡、大胡(大提琴)、低胡(低音大提琴)。舞臺中間1~5排,古琴、揚琴、古箏、柳琴、琵琶、中阮、大阮、三弦;舞臺第六排為笛、笙、簫三類樂器,舞臺第七排為嗩吶、管子及其他吹奏樂器;舞臺第八排為打擊樂器。舞臺斜左側第五、第六排排尾位置為彈撥樂器箜篌。另外,屬于“金石之樂”的編鐘、編磬則應放置在正對指揮的樂隊最后方。
結 語
總地來看,古蜀樂樂隊體系的建構與不斷完善為古蜀樂在今天世界多元音樂大發展的潮流中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在上述古蜀樂隊的建制設想中,古蜀樂的傳承性體現在對古蜀彈撥樂器箜篌、琵琶,吹奏樂器排簫、管子以及拉弦樂器板胡的重視;而古蜀樂的發展性體現在對古蜀樂建制體系從歷史上的“吹、彈、打”的樂隊組合形式擴展為“吹、拉、彈、打”四種樂器組合的完整形式。同時對四川省境內藏、羌、彝等少數民族族群代表性樂器的使用也彰顯出當代古蜀樂樂隊體系開放、包容的特點。在當代古蜀樂樂隊構建中,只有依循尊重傳統而不因循傳統,追求現代而不濫用現代的原則,古蜀樂才能在今天多元發展、快速轉變的世界音樂潮流中脫穎而出,實現持續性發展。
◎ 本篇責任編輯 李姝
收稿日期:2018-10-08
基金項目:2015年四川省哲學社會學科重點研究基地(西南音樂研究中心)重點項目(xnyy201
5006)。
作者簡介:林戈爾(1957— ),男,國家一級作曲家,二級教授,四川音樂學院原院長(四川成都? 61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