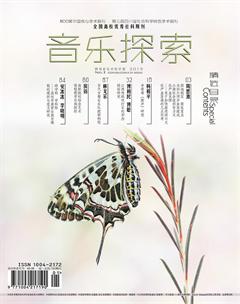淺析《史記》記載的幾首慷慨悲歌
摘 要: 司馬遷在《史記》中使用了以音樂展現人物性格的手法。荊軻“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英雄赴難之歌,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英雄末路之歌,劉邦“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勝利者惆悵之歌深化了對英雄人物的形象刻畫。
關鍵詞:《史記》;《荊軻歌》;《垓下歌》;《大風歌》
中圖分類號: J65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 - 2172(2019)01 - 0076 - 04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19.01.010
馬遷所撰寫的《史記》被稱為“二十四史”之首,被魯迅先生高度贊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一是它恪守“信史”的原則,不拔高不溢美;二是它以文學的筆調書寫歷史;三是它在對人物的描寫中穿插使用了音樂作品,增強了人物事件的真實感。眾所周知,在所有的社會活動中,音樂是最為純粹的一種文化藝術形式,能直截了當地表現人們的心理情感和精神世界。晉代嵇康曾云:“夫心動于中,而聲出于心。”意思是歌聲是來自心靈的吶喊,是個人情感最直接的張揚。《史記》中音樂作品的使用極大地深化了作者對英雄人物形象的刻畫。下文具體分析《史記》中記載的幾首著名慷慨悲歌。
一、英雄赴難的《荊軻歌》
《史記·卷八十六·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詳細記載了戰國時期荊軻刺秦王這一悲壯的歷史事件:“……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發盡上指冠。于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①
荊軻刺秦王發生在戰國時期末年,當時中原各國戰亂頻繁、諸侯爭霸。秦國在秦王嬴政的統治下日漸繁榮富強,大有一統天下之勢,“戰國七雄”中的韓已被秦滅,楚、魏、趙也名存實亡,燕、齊亦危在旦夕。到燕王喜時期,燕國的國力已經大大衰弱,軍事力量薄弱。雖然預感到秦王滅燕是遲早的事情,但太子丹不愿坐以待斃,便想到以刺殺秦王來阻止秦國進攻燕國的計劃。他派出無畏勇士荊軻趕赴秦國刺殺秦王,希望秦王遇刺后秦國陷入內亂,為其他諸國贏得一線生機。
荊軻明知刺殺秦王兇多吉少,此番前去必然是有去無回,但既已答應太子丹,就一定要履行諾言。公元前227年,他攜帶燕國督亢地圖與大將樊於期首級前往秦國伺機刺殺秦王嬴政。臨走之時,燕國百姓在易水邊為荊軻送行,氣氛濃重而悲壯。太子丹與眾賓客頭戴白帽身著白衣,表情肅穆凝重,氣氛濃烈緊張。拜祭祖先之后,荊軻準備上路,這時高漸離為眾人擊筑,荊軻相和而歌,音調是“變徵”音,呈現出悲涼之感,眾人聽聞不由得低頭掩面而泣。之后荊軻前行,高聲唱著“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其所屬音調變為慷慨的“羽”音,聲調激憤,眾人皆怒目圓睜,頭發豎立于帽子之下。荊軻隨車離去了,再也沒有回頭。
荊軻抵達秦國后不久便被秦王召見于咸陽宮,在給秦王嬴政進獻燕督亢地圖時圖窮匕見,但行刺終告失敗,荊軻也被秦王侍衛所擊殺。“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唱詞一語成讖。
將《荊軻歌》歌詞譯為現代語即是:“風蕭蕭地吹呵,易水亦寒氣逼人,壯士在此遠去呵,不完成使命誓不歸還!” 整首歌曲僅兩句歌詞,短小精悍。第一句寫出了出行離別前的自然環境:秋風蕭瑟,冰冷的易水緩緩流淌,蒼涼的自然景象烘托出荊軻刺秦的悲壯氛圍。第二句描寫了荊軻勇入秦國,誓死完成任務的堅定決心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情懷。
這種借景抒情的表現手法使全篇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是我國古代詩歌之典范,體現出了藝術的永恒性,超越了時空的限制,訴求于超自然的情懷。荊軻因刺秦而留名,《荊軻歌》也流傳于世,以通俗易懂的語言表現出了最高層次的愛國情懷和義士之勇,令人肅然起敬。
二、英雄末路的《垓下歌》
項羽是著名的軍事家,一代英雄豪杰,被稱為西楚霸王,在中國歷史上書寫了屬于自己的宏偉篇章。項羽在垓下之戰中被困,兵盡糧絕,在對敵軍伎倆的憤恨和對戰況的無奈中最終吟唱出《垓下歌》,驚天地,泣鬼神,影響深遠。司馬遷在《史記》中以“本紀”給予項羽帝王般的地位。
在《史記》中,項羽既是一位蓋世英雄,又是一個性情暴戾、優柔寡斷、不善謀略的匹夫。司馬遷在對項羽的記載中將其身上的諸多矛盾融為一體,不但有深重的討伐之意,同時也充滿了深切的同情和發自肺腑的惋惜之情。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第七》載:“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于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①
文中的《垓下歌》雖然篇幅短小,但卻深刻地表現了人生的無奈,譯為現代語即是:“力量之大,可將大山全然拔起;豪氣萬丈,無人能夠匹敵。然而時局危難對我而言相當不利,烏騅馬早已精疲力竭,跑不動了,已不能夠更加快速地前進啊,之后我該如何是好呢?虞姬啊!虞姬啊!我又怎能將你安置妥當呢?”
這是項羽抱著必死之心在戰斗前夜所吟唱的絕命之歌。簡短的4句歌詞不但展現出項羽的萬丈豪氣和滿懷深情,又隱含著他對時局的無奈嘆息。
第1句 “力拔山兮氣蓋世”寫出了項羽的超凡能力。項羽是將門之后,年少時氣盛胸懷廣,志向遠大,不畏懼秦始皇,曾喊出“取而代之”的雄心壯語。項羽23歲時隨同叔父項梁對秦國起兵,率領8000戰士涌入起義的戰潮中,在眾多起義首領中脫穎而出。在巨鹿之戰中,項羽帶兵浴血奮戰,面對多于自己幾倍的秦軍破釜沉舟,最終取得勝利,成為歷史傳奇。因此,他被諸侯們稱為“上將軍”。項羽久經沙場,戰無不勝,最終進軍咸陽,自封為 “西楚霸王”。他是頂天立地的英雄,但是對個人力量的過分夸大最終導致了他在垓下敗于對手。
第2句 “時不利兮騅不逝”表明時機不利于他啊,就連心愛的戰馬“烏騅”也不肯前進了。在長達4年之久的楚漢之爭中,項羽雖然戰績赫赫,但他不善用人,也不會審時度勢,失敗只是遲早的事。
末句“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秦朝滅亡之后,項羽與劉邦展開了爭奪天下的戰爭。項羽殘暴,不但使“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馀萬人新安城南” ① ,且“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 ② 。當他撤至垓下(今安徽靈璧縣南沱河北岸)之時,已是損兵折將、糧草殆盡、眾叛親離。
四面楚歌之下,項羽知曉自己的末日已然到來,痛苦與絕望充斥著他的頭腦。因自己的原因使天下得而復失,最后只落得個自刎而死的悲涼結局。《垓下歌》是英雄末路的慷慨悲歌,令人倍感蒼涼。
三、勝者亦憂的《大風歌》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垓下歌》描述了項羽的窮途末路,而《大風歌》則表現了劉邦作為勝利者的惆悵與擔憂。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第八》載:“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③
《大風歌》內容簡短,卻飽含慷慨激昂之氣,有著多層含義,每句歌詞都代表漢高祖不同的場景與心情。
“大風起兮云飛揚”。劉邦用風、云做喻,看似描述天氣變化,實則暗喻秦末時群雄爭奪天下,社會動亂的畫面。“威加海內兮歸故鄉”。首字“威”字顯示了劉邦的王者霸氣,描述了自己天下臣服的豪氣。此時劉邦戰勝項羽和其他割據者,統一天下,榮歸故里,邀請父老鄉親飲酒、擊筑、唱歌,是何等的榮耀與威風!
在這兩句歌詞中,劉邦總結了自己奪得天下、威加海內的原因。天時是首要條件。當時天下大亂,群雄紛爭,誰能夠最終奪得天下是上天的安排,并不是人力能夠左右的。現在雖然自己奪得了天下,但不過是運氣好,時勢造英雄而已。若不是碰上了這個時代,自己的才能又能被何人賞識呢?出身如此低微的自己又能夠有多大成就呢?因此,自己能夠爭得天下,奪得帝位,不過是上蒼的安排罷了。
最后一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劉邦對自身政治理想的有感而發,同時也反映了他對于國家剛脫離戰亂之苦、尚不安定的擔憂及惆悵。他深知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要守護天下,保天下太平,需要“猛士”來駐守四方。但是當今天下是否有這樣的勇士呢?劉邦并不確定,就算是有,他們是否愿意來守護天下,為自己效力呢?這也不是劉邦能夠確定的。這最后一句表現了劉邦的復雜心境,他深知以后的道路會更加艱難,壓力會更大,也清楚地看到了更加艱巨的責任;因此,這句歌詞隱含著前途未卜時的焦灼和恐懼。
《史記》一書全面記載了我國從黃帝時代至西漢時期的歷史文明,跨度約3000年,內容涉獵廣泛,包含了天文、地理、音樂、人物等多方面。本文簡單探討了《史記》中的幾首悲壯之歌,不論是荊軻刺秦的“風蕭蕭兮易水寒”,還是末路英雄項羽的“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或是奪得天下劉邦的“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都是以寥寥數語勾勒出鮮明的人物形象。正因為這幾句歌詞都是出于內心的吶喊,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能夠深刻感受到處于當時的歷史環境下,荊軻的離別的悲涼、項羽英雄末路的無奈與痛苦、劉邦對未來的彷徨與困惑。
◎ 本篇責任編輯 錢芳
收稿日期: 2018-05-25
作者簡介:謝丹(1979— ),女,碩士,四川音樂學院繼續教育學院講師 (四川成都 61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