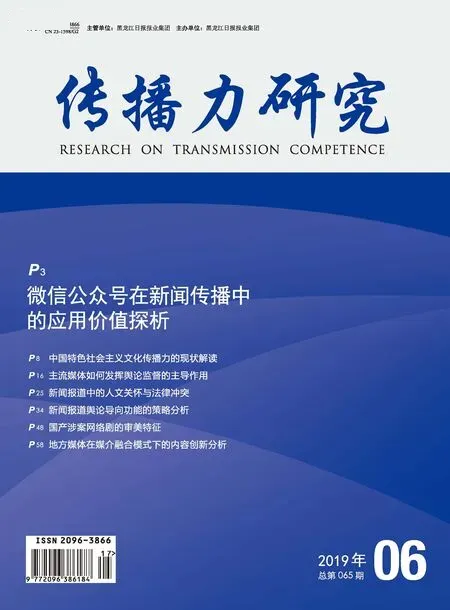央視《等著我》電視節目傳播策略分析
——基于霍爾編碼/解碼理論視角
單曉萍 山東師范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
2014年4月5日,大型公益尋人節目《等著我》在中央電視臺綜合頻道開播。不同于其他綜藝節目,《等著我》聚焦公益尋人,在泛娛樂化的風氣中脫穎而出。它用真人物、真事件、真情感關注個體生命歷程,真實呈現時代樣本,體現了人間大愛,它的成功契合了當下人們的情感和精神需求。本文從斯圖亞特·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出發,試圖分析《等著我》的編碼策略以及受眾的解碼策略,提煉其借鑒意義,并以此助力國內電視節目的良性運轉。
一、《等著我》節目制作者編碼分析
(一)選題符碼分析
《等著我》植根于現實,深度挖掘中國老百姓的真人真事,讓觀眾得以從一個個救助者身上窺探那些鮮為人知的記憶,以及從中體現出來的對于情感和主流價值觀的追求。《等著我》在編碼過程中,既設置了血濃于水的“親情”符碼,也有情比金堅的“愛情”符碼,有超越血緣的“恩情”符碼,也有患難與共的“戰友情”符碼,它用普通人身上不普通的故事進行編碼,串聯起人類最真實的情感鏈條,讓受眾在解碼時能夠更大程度地引起共鳴。
(二)主體符碼分析
《等著我》節目臺前的主體符碼由主持人、嘉賓、尋人當事人以及觀眾組成。主持人在節目中處于引導地位,由著名主持人倪萍和舒冬擔任;《等著我》的嘉賓設定也呈現多元化,有知名文藝工作者、有代表權威的政界人士、有資深的媒體人等等;此外,構成尋人事件的當事人是整個節目的核心,尋人者帶著各自的故事走上舞臺,將塵封已久的往事展現給觀眾;除了臺前的參與者,還有幕后的尋人力量,如公安干警、志愿者們和節目的制作組等等,他們與前臺一起共同構成了整個編碼主體,力求為觀眾呈現完整的節目形態。
(三)節目流程符碼
為了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節目組在進行編碼時要充分考慮受眾的解碼能力,設置更為人性化的節目環節。《等著我》一期節目一般呈現兩個尋人故事,節目開始先由尋人者講述其尋人故事,這其中穿插了主持人的提問,幫助觀眾更好的解碼;講述完之后,由尋人團展現其尋人的過程,以視頻的方式呈現;接下來便是節目的高潮部分——打開“希望之門”,揭露尋人結果,這樣的編碼設計能最大程度地引起觀眾的懸念,提升節目的張力;最后便是結果的解釋和補充。自此,由各個環節符碼構成了完整的編碼過程,為受眾高效的解碼作了鋪墊。
(四)表達元素符碼
在節目的編碼過程中,適當的表達元素也是必不可少的。由于《等著我》的主旨設定,其舞臺設置簡約化,一張白色的沙發、一個通道和一扇大門便構成了節目舞臺的全部元素符碼;同時,《等著我》舍棄絢麗的燈光,采用暖色系的符碼設計,營造溫馨的場景氛圍;最后,背景音樂也采用抒情類的,并以現場鋼琴彈奏的方式,依據節目的流程和講述人的情感表達,在適當的時刻切入,引起觀眾的共鳴。
二、《等著我》受眾解碼分析
(一)優先式解讀
受眾的“優先式解讀”是指按照編碼者賦予的意義來理解節目傳達的訊息。從《等著我》的觀眾反饋中來看,大部分人對于節目所傳達的價值觀采取的是認同的態度。《等著我》所呈現的一個個鮮活真實的故事,卷入了強大的情感能量,這些人這些事看似遙遠,但其中蘊含的感恩、孝道、人倫,都是人類無時無刻不在觸及的人生命題。同時,通過親歷者的講述和權威人士的解讀,能夠增強人們的法律意識,更好地保護自我、保護家人。除此之外,《等著我》作為一檔公益尋人類的節目,更大的意義是使得更多的人參與到公益事業當中來,讓更多失散的親友通過科學的方法早日團聚。以上便是編碼者通過節目想要傳達的意義,受眾能夠根據其意圖認同節目中蘊含的信息和價值觀,是一檔電視節目能夠長久存在的重要手段。
(二)妥協式解讀
受眾的“妥協式解讀”是指受眾在觀看電視節目時,不完全按照編碼者所提供的話語訊息來解讀,有部分抗拒的心態。對于《等著我》來說,該節目最大的爭議便是“太過煽情化”,甚至被觀眾戲稱為“催淚彈”,曾一度被認為是拿親歷者的悲慘故事來消費大眾的悲傷。同時,嘉賓和主持人的“道德綁架”,也引起了部分觀眾的不滿。每個人的生活經歷以及價值觀都各不相同,所以也根本無法做到對于親歷者的“感同身受”,這種矛盾是必然存在的,編碼者在處理此類情況時要采取相應的策略將這種沖突降到最低。
受眾的第三種解讀方式是對抗式解讀,即受眾對編碼者所提示的訊息意義做出完全相反的理解。[1]在《等著我》節目中,這部分受眾占很小的一部分,但節目組也應提高重視,采取相應的策略,規避這種情況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