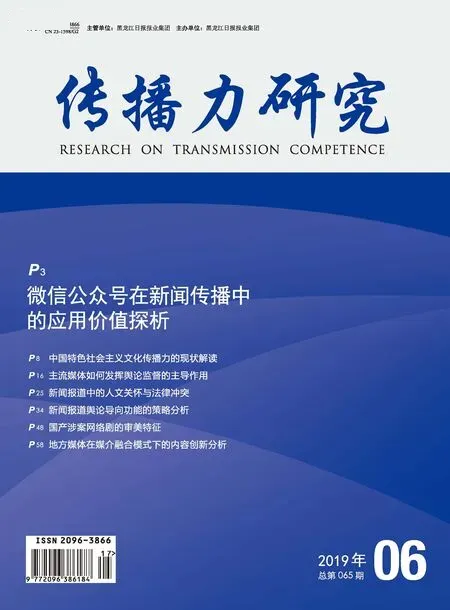朗誦意境中的層次對應
鄧鑫 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院
一、緒論
朗誦主體進行有聲語言轉化過的作品,至少要有三個方面的層次。這三個層次能否被受眾感知是客體論需要討論的,但不能孤立的論述這個傳播過程。在主體意境角度,筆者借鑒明畫家李日華在《紫桃軒雜綴》對畫的三境界說。朗誦者應當有意識的表現出這三個層次,即環境內容、文本情緒以及代觀眾感受的‘本我’。也就是宗白華所歸納的“寫實”、“傳神”、“妙悟”。
二、身之所容,直觀感受的渲染
張頌老師說:“意境其實是一種時空氛圍。”[3],這句話其實說明了欣賞一個朗誦作品,首先得進入這個‘場’。在浩如煙海的文學作品中,每一個時代都有其時代特征,其作品自然也沾染了這種氣息。如何能在這萬古長空見這一朝風月,是朗誦主體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播音創作基礎第3 版的教材這樣描述時代感:“古代和近代,現代和當代,都能夠顯現出變化的印記。如解放戰爭中的慷慨激昂、‘文革’時期的虛張聲勢、改革開放后的沉穩亢奮、新世紀以來的務實創新。”[4]在現當代歷史中,都有細小微妙的差別,朗誦主體更應做好充足準備面對自文明出現以來的龐大時空背景。為了使作品本身及聽眾感知有直觀感受的渲染,朗誦者首先應當做到身之所容。但個人經歷有限,既要在生活中積累素材,包括情緒的感受、知識儲備,也要根據具體文本具體分析。播音創作基礎中謂之廣義與狹義備稿。而‘容’,不僅僅是指創作者應構造的時空氛圍,同時也包括創作者自身應該進入的情境。它同時容納了詩文本意、意象、象外象,以及創作主體、受眾、創作場。
三、目之所矚,活躍生命的表達
劉潤說:“堅持適度原則,情取其真。”[5]感受一個作品,常常以它是否能打動你作為判斷好壞的依據。這要求朗誦者要有共情的能力,這種共情的能力體現為雙向的,表現在朗誦者是否能心領神會文本的情與意,受眾能否感受到朗誦者所構建的意境場;這種雙向能力其實表現了朗誦者自身的審美與能力,在創作基礎中謂之情景再現,由此可見具體創作技巧能表現出具體意境特征從而形成層次。而在這個共情體會的過程中,不管從價值取向層面而言,還是從意境的層次而言,播講目的都是尤為重要的。
它主要表現在控制、移情與整體觀上。朗誦者為了更好的共情,讓觀眾體會情緒,無節制地夸大情景再現的形式、過程,雜亂無章;而沒有生活的體驗便只局限于詞語表面,模糊膚淺;如果過于注重細節,而忽視整體感受,停滯于此,便會讓受眾覺得‘不知所云’,難以接受。目之所矚,是受眾被帶入到意境場后,能直觀看到情感的動容與活躍。
四、意之所游,最高靈境的啟示
意之所游,是整個傳播過程的目的。也是宗白華所言的‘妙悟’。在美學與詮釋美學有關整體關系的循環過程中,朗誦主體以及鑒賞者都對作品文本有著不同的領悟或啟示。而對于作品的領悟,取決于自身的閱讀基礎、領悟能力、理解能力等多方面的因素。張頌言:“面對文字作品,不應浮光掠影、淺嘗輒止。”所謂‘意之所游’建立在理解力和判斷力的基礎上。是主體經歷了思考之后的領悟,也是其竭盡所能追求與文本共鳴的探索。
這種啟示類似于散文中的‘神散’,它由文本生發,卻又不僅僅只是文本。它非常主觀,故它是‘悟’,更是由于其表現形式稱為‘妙悟’。這是‘意’卻還要‘游’。如果只是‘意’,這種啟示可以不被表達,或者如果只是單一的‘意’,這種意境是孤立且不被共情的。要給人以最高靈境層面的啟示,就還要將其‘意’運動起來,所謂‘意之所游’。它不僅僅可以調動受眾隨之運動,更是讓其更直觀的看到文本意及文本意境。而客體意境又是怎樣一番景象,又有很多因素了。文學作品講究把道理蘊含在故事之中,朗誦美學更是追求將文本藏于構建在‘悟’之后的聲音及聲音構造出的意境場中。
五、結語
將主體意境區別于客體與文本意境進行研究,也是播音學科應當承擔的責任。意境美的探討屬于播音美學范疇,但卻是播音創作領域中不可忽視、難以略過的重要環節。將播音創作基礎的具體技巧與意境綜合運用產生的基本手法結合是經驗之談,但也是大膽構想。播音學的技巧與美學的手法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它們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在綜合運用之后是否能有一個好的呈現,就需要用傳統意境的層次進行判斷,這是最后的‘把關’。把研究的概念細分化,將學科內的技巧綜合運用使之傳播,并始終存在著一個較為共識的標準去判斷是否合理。這是美學從上層建筑層面幫助播音學科解決的意義所在。